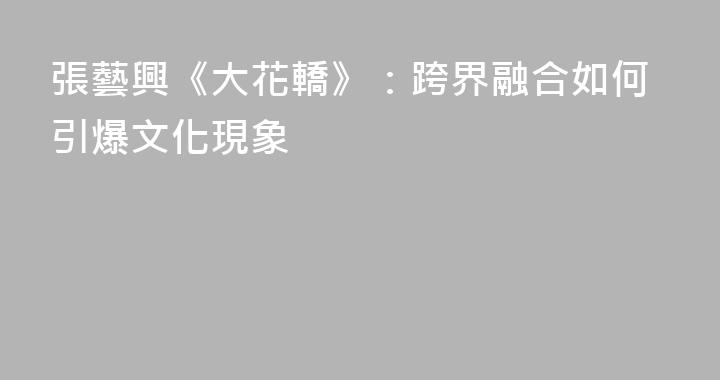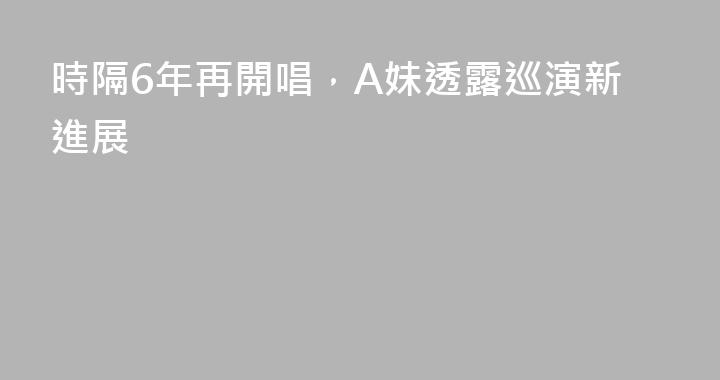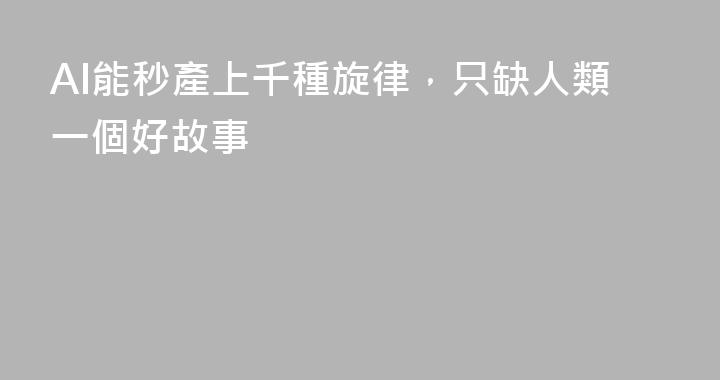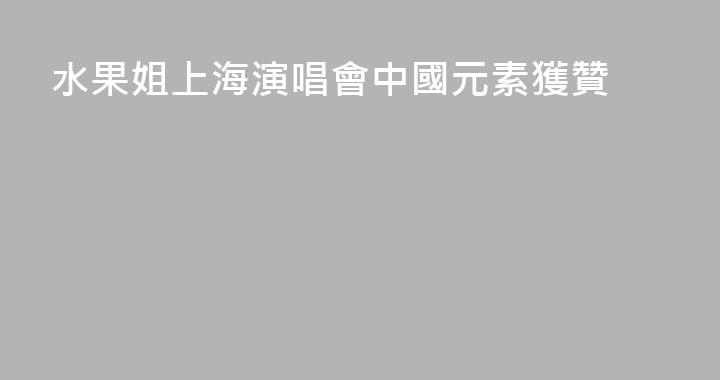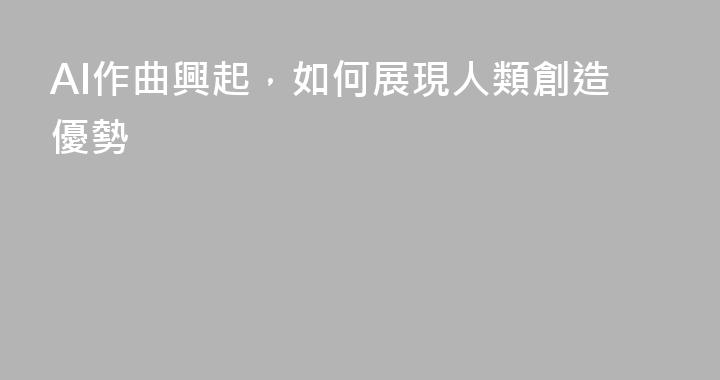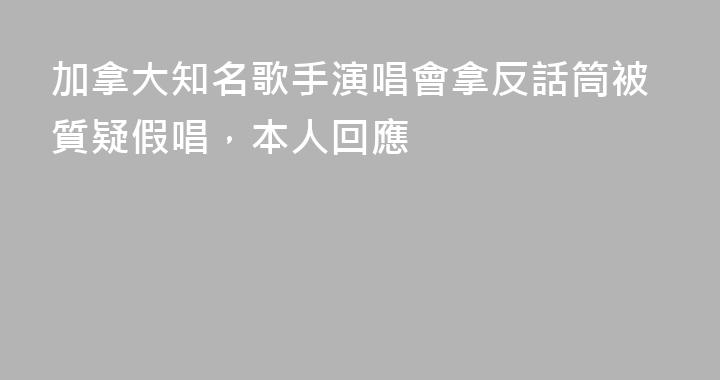《大河安瀾》是一部講述黃河與人的故事、富於生活氣息的戲,也是一部講述共和國曆史、富於時代精神的戲。將普通人與時代之間的關聯,做一種生動、有力的舞臺表現,推動國家政策與社會人心之間的對話,正是豫劇三團自《朝陽溝》以來開拓、成就的現代戲傳統之一。《大河安瀾》在這一傳統的滋養與各方人才的傾力合作中,創造了“大河”這樣一個動人的、嶄新的藝術形象,帶領觀衆進入黃河岸邊平凡又偉大的生活世界,極爲精彩地回答了:一個普通的守河人何以安瀾?何以承載黃河孕育的土地上的厚重文化?何以成爲護持百姓、激勵後人的“河神”?何以成爲承繼了“大禹”精神、也凝聚了共和國精神的平民英雄?
《大河安瀾》開場時,一面幕牆奔騰着黃河水,說書人一樣的支書靠河一吼,唱出這黃河岸邊流傳的故事與精神:“大黃河,看得見五帝三皇,大禹王要治水,得罪了龍王,大禹王鎮守中原禹門口,他要與龍王爺血戰一場。”隨後,身穿志願軍服、打着揹包的劉大河跑上黃河岸邊的大堤,孩子般把一捧沙拋起來,又瞪眼吹去拂面而來的沙塵,憨態可掬,喜從中來,這是他熟悉的家鄉,他熟悉的土和沙。他熟練地從大堤上滑下,遇到他熟悉的鄉親們的鑼鼓秧歌歡迎陣仗……大河的這一開場亮相,把一種黃河岸邊長大的孩子的憨厚,和一種經過部隊培養、戰爭磨礪的戰士的堅毅、明亮、擔當,做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賦形。這是中原厚土和得之不易的共和國曆史賦予的氣質,一種在大河此後幾十年生活風雨中毫不褪色、消磨的精氣神,讓他在任何困難面前都會挺身而出,“我是軍人,我來守河”,“我是軍人,我來保護你”,“這是我的陣地,我絕不會放棄”,也讓他在每一次涉及個人幸福與安危的抉擇中,都先顧着他人,而放下自己。
豫劇演員賈文龍把這一角色塑造得令人感動而信服,這來自他對角色的理解和把握、能很好表現性格的唱詞唱腔、融合豫劇傳統戲與現代戲的精湛技藝和傾情投入。這還與編劇王宏對1950年代部隊經驗、精神的深刻把握和傳達有關。大河面對鄉親們對他“英雄回來了、快給我們講講你殺了多少鬼子”的期待,雖有點羞澀自己並沒有這樣的戰績,卻同時大方地說自己是炊事兵,當有人發噓聲,他更“驕傲地”說,老班長說了,“一個炊事員,半個指導員”。大河,這一個“驕傲”的炊事兵身上,同樣蘊含了四五十年代中國軍隊諸多了不起的創造性經驗和革命傳統。
編劇把普通士兵大河的淳樸心性和軍隊磨礪的能力品格,視爲寶藏,以一種知心而謙虛的方式,針腳細密地編織進劇情,這實則是文眼,是戲眼:大河是黃河的赤子,也是共和國的“赤子”。
如果說,大河代表了經過部隊熔爐鍛造,高強度的、純粹的赤子,黃河岸邊壩頭村的村民們,則鋪設了一種更爲寬廣、深厚、生長這樣的赤子的土壤。有胸懷、有頭腦的支書,熱心腸、不怕事的二嬸子,即使在動亂時代,也能讓躁動起來的村莊平靜下來,讓七寶這樣有點“渾”、有可能被狂瀾帶着跑的野小子清醒過來,守護住人性人心善良的根底。像守河人曾經收留了黃河漂來的孤兒大河一樣,他們收留了父母是資本家、落難的師範學院畢業生安瀾;這樣的大河安瀾故事,在這樣的黃河風土與生活世界裏,生生不息。
安瀾和大河在堤上的廟裏安了家。新婚之夜,安瀾說:聽二嬸兒說,這是大王廟,這裏面供的都是老輩子治河的大英雄,村裏人都把他們尊爲河神。
大河說:俺爹說了,守河人也是河神!一輩子都要守好這條河。
安瀾說:大河,你也是河神?
大河沒有回答,只是引着她來看河,告訴她黃河是母親,卻有不受管束的脾氣,“她平安就是我一生追求。老年後我也要跟着她走,跟着她去看大海,去看源頭……”當年,大河復員回家鄉,在衆人都不願意守河、黃河誰來守成了難題之時,毅然接下養父守河人的職責。守河守河,守的是蒼生。
大河爲護河而死,葬在了河邊。多年後,爲“數字黃河”工程攻堅的兒子大堤,陷入母親和妻子要自己“離開黃河”的矛盾和痛苦中,來到父親墳頭。此前,在老龍灣的水文測量中他差點喪命,母親安瀾堅決要他辭職,因爲,“你和恁爹太像了”。這個戲劇衝突其實頗不容易設計。大堤來到了墳前,使他下了決心的,不只是心上烙印的父親的堅忍和奉獻,更是對埋在黃河岸邊的父親的“心疼”。這心疼也就自然地通過動人的唱段,和母親安瀾的心連接起來。在世代的情感與責任的傳遞中,矛盾不是被解決,而是被昇華了。黃河岸邊埋骨的大河,是守護土地與後代的人,也是永遠被後代感念的人。
赤子其人,河神其魂。正如安瀾轉述二嬸兒的話,在中國的鄉土上,自古以來如此,老百姓以尊爲神的方式記住一些爲老百姓做了好事的人,這是一種屬於百姓的感謝機制。這樣的《大河安瀾》,正如幾年前豫劇三團的另一部大戲《焦裕祿》:老百姓把焦裕祿這個人記住了,而藝術以這樣一種細膩而恢宏的方式把老百姓的感謝記錄下來。這樣的藝術,是時代的藝術,也是屬於人民的藝術。
(作者:李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