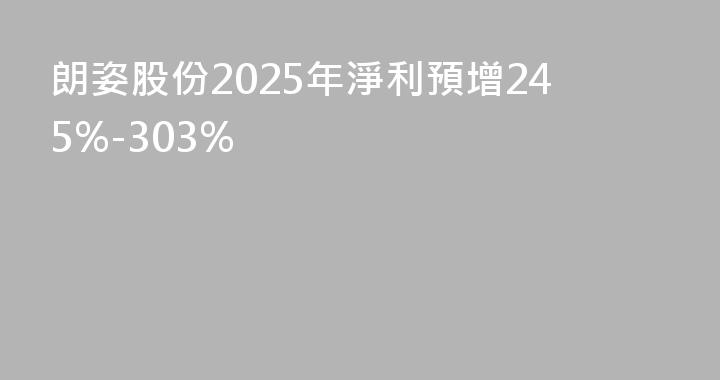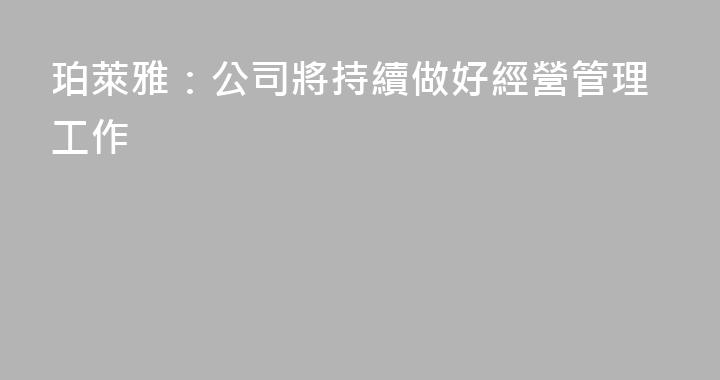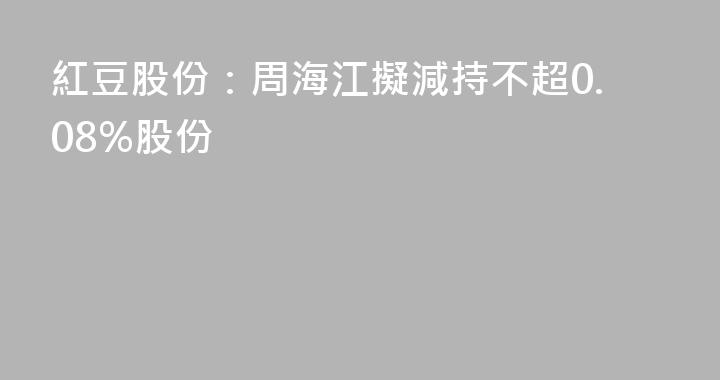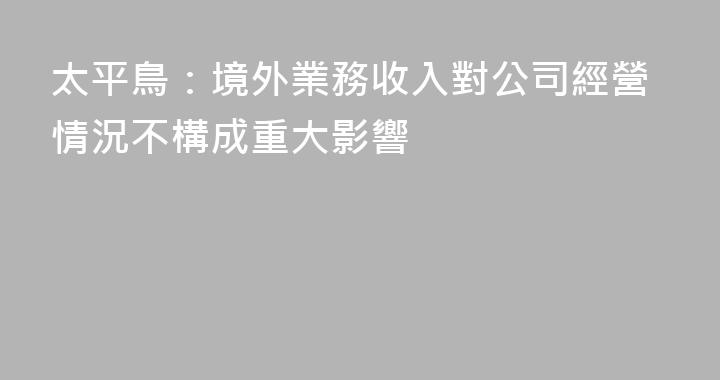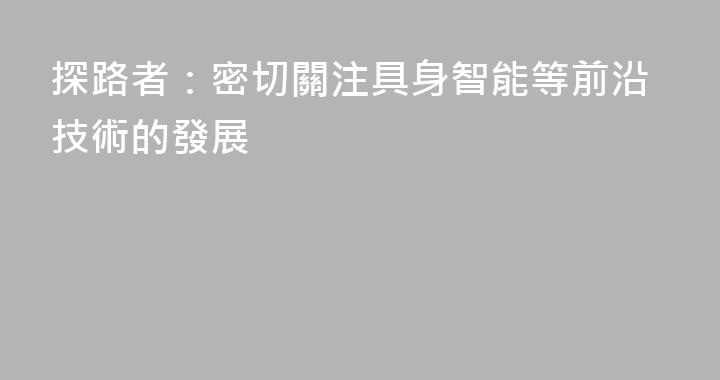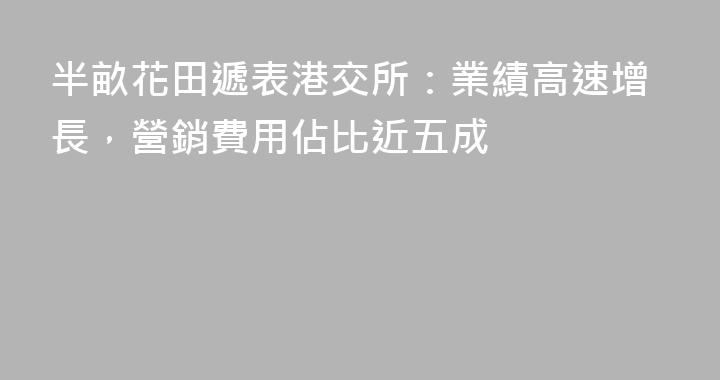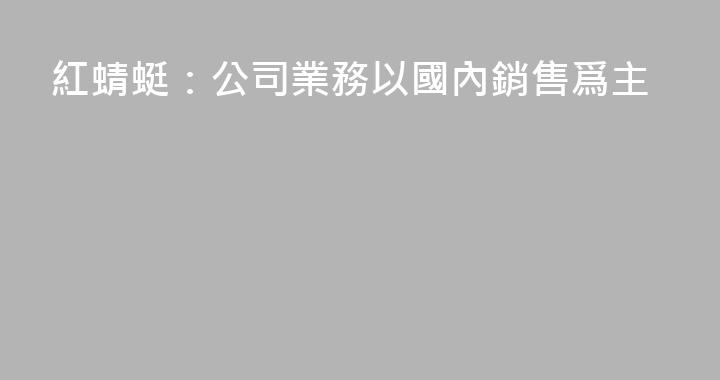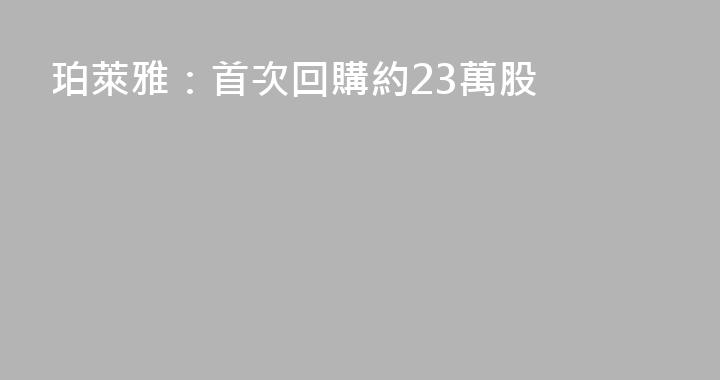《人生之路》裏,那些青年男女面臨的困境都有了多元的選擇,無論是男主角們意外的交錯人生,還是女主角們註定的生命軌跡,皆有去向與歸處,而與原著不曾背離的,是他們在逆境中向陽而生的精神,一如既往地蕩氣迴腸;而對劇中人命運沉浮的思索,也一如既往地耐人尋味。
許久未有這種感覺了,追劇之路並不全然只是愉悅或憤慨,而是幾度夢迴劇中情境,依然情難自禁地爲劇中人命運的參差,感到唏噓。以至於也曾像劇中人那樣不斷在迷茫時刻生出對人生、命運的叩問!或許,不同人的人生本就是如此千差萬別,但高加林的悲劇源於何處?劉巧珍對感情的執着,又值不值得?
由閻建鋼執導,陳曉、李沁領銜主演的現實題材劇《人生之路》正在央視和愛奇藝熱播,開播即引發廣泛熱議,從服化道的年代感到演員們的演技,從敘事方式再到與原著之差別等都成了熱門話題。《人生之路》的故事部分取材自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此番將經典重現不只是對原著的煥新,還在保留其內核的基礎上進行了時代性的續寫——
《人生之路》以20世紀80年代陝北黃土高原的生活爲背景,講述了高加林、高雙星、劉巧珍、黃亞萍等青年人走出黃土高原來到上海,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斷奮鬥拼搏而改變人生命運的故事。
相比原著,擁有複雜性格的男主角高加林,其多舛命運又增添了一分悲劇色彩:他渴望以知識改變命運,一心想離開那片貧瘠的黃土地,但不幸的是,他考上大學卻被好友高雙星冒名頂替,而自己與錦繡前程失之交臂。失去開啓光明人生的希望,他曾清澈明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采。而接二連三的打擊,將他幾乎“錘”入谷底。當民辦教師,卻因意外事故痛失轉正機會丟了工作;進城當通訊幹事,又因被舉報錄用不合規而重歸農民身份……如此起伏不平的人生,當失意成爲日常,他頹廢、彷徨、消沉、氣餒……但他又總能在每一次生活重新露出一絲曙光時,振作、蓬勃、奮起、進取……
儘管對陳曉飾演的高加林,人們評價並不一致,但對於像我這樣不曾讀過原著和看過電影《人生》的初見者,從他塑造的高加林形象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不同狀態,已然看到了40年前的陝北高原,有爲青年的種種特質——他有一定的才華,因此有文人傲骨,心懷鴻鵠之志;他有改變不了的家庭背景,因此敏感脆弱,有強烈的自卑感……優缺點並存,有幾分自負亦有幾分虛榮的高加林,在陳曉的演繹下,是血肉豐滿的,也是可悲亦可愛的。
幾番起起落落,和被束縛在高家村的高加林不同,“偷”走他人生的高雙星卻在上海的校園裏,從初期與周遭的格格不入,漸漸通過自己的努力開始“如魚得水”,不僅與上海姑娘戀愛,發表《農民工生存困境的調查報告》找到自己的價值,還因申領身份證的契機,如願改回自己的真實姓名。本是不光彩的“竊”他人命運者,卻坦然自若、順風順水地完成階層轉換,這是何等諷刺?而這種雙線對照形成的鮮明對比,更凸顯了高加林命運的悲愴,渺小的他猶如一葉扁舟在浪花裏漂流,難敵波濤洶湧!
當這種對比越發強烈時,讓人很容易代入高加林的視角,去體會那種不甘於平凡的人生,體會那種現實的殘酷與時代的脈搏交織下,小人物的命運難與大時代的力量抗衡的痛苦,當然,也因此順理成章理解了高加林在逆境時的無奈、妥協,以及被動地接納現實,與宿命和解;理解了高加林在順境時的意氣風發、神采飛揚,以及主動地爲了飛得更高更遠而作出的抉擇。
顯然,《人生之路》對高加林這一角色性格、境遇的一些改動,除了反映當時因信息差導致的社會真實現狀、反映當時的陝北農村的真實生活狀態,並沒有改變高加林自身的精神面貌,反而,更能帶給人們對人生最深刻的思考:面對突如其來的人生挫折,有多少人可以從容不迫?又有多少人可以將苦難化爲原動力,在每一個艱難時刻,都有向前走的勇氣?無疑,勤勞樸實的高加林是具備向命運挑戰的品質的,更擁有那個時代背景下知識青年開闊的眼界,以及渴望突破自我的雄心。
和多面性的高加林相比,劇中的女主角,堪稱那個時代具有自我意識的新女性代表人物,無論是在山溝溝裏土生土長的劉巧珍,還是在大都市出生的黃亞萍——
劉巧珍是黃土高原生命力的代名詞,雖然她文化程度並不高,但她具有勞動女性特有的善良、單純、率真、坦蕩、勤勞,也有超脫於普通鄉村女性的視野,所以,她理解高加林的鬱郁不得志,鼓勵他走向城市;她支持妹妹劉巧玲攻讀學業,對抗父親的狹隘認知;她懂得生活的真諦,寬慰高考落榜的馬栓“自己的路自己走”……她勇於追求愛情,也敢於直面生活。“我的婚姻我做主,我的愛情我說了算”,在閉塞的鄉村成長,劉巧珍並未被禁錮在當時、當地以男性爲主的話語體系裏,也並非如刻板印象中的鄉村女性那般怯懦,她活潑開朗,風風火火,對生活有着屬於自己的想法與見解,對高加林的愛情,更是來自靈魂深處沒有半點雜念的愛,且熱烈如火。對父親試圖包辦自己婚姻的想法,她據理力爭;對村子裏每天對她指指點點的人們,她大大方方地與高加林牽手面對。同時,她也是腳踏實地生活着的女性,努力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展現了堅韌的女性力量。
如果劉巧珍質樸無華的美好,帶給人們的是單純、原始的感動與共情,黃亞萍則是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體,代表的是接受知識薰陶的自立自強的新時代女性,她的思維方式更貼近如今的現代人。她熱愛讀書,熱愛文學,熱愛詩歌,熱愛跳舞,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對事業和感情,都有自己的執着追求。熱愛理想的同時,也熱愛生活,因父生病錯過高考她不曾抱怨,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在做播音員時,她沒有荒廢愛好,時常利用閒暇時間跳舞。可以說,她是一個在任何方面,都忠於自我且忠於自我選擇的女性。
不同身份和家庭生活背景下的劉巧珍與黃亞萍,都具有相似的先鋒性和共通的閃光點,她們都勇於主動去選擇自己夢想的生活,且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步履不息地行走着、耕耘着,她們共同呈現了20世紀80年代黃土高原上生活着的女性,自我意識與女性力量的覺醒。
不同於原著,《人生之路》在他們走出陝北高原後譜寫的上海奮鬥史,還將讓人們看到他們每個人更多的成長與蛻變,在書中似乎曾經屬於高加林一個人的“獨角戲”,也將變成一部全新的時代青年羣像的成長史詩。《人生之路》的前半部分,聚焦的是幾位年輕人在特定時代的生活現狀,而後半部分,則是他們走出時代、地域和社會環境侷限的奮鬥歷程。但不管是在陝北的黃土地,還是在大上海的鋼鐵叢林,人們都能看得見,他們在人世間跌跌撞撞,不甘於被命運捉弄的奮力掙扎;也看得見,他們對理想人生與自我價值的不斷追逐。
立足時代的迭變,《人生之路》試圖以更貼近現代人價值觀的敘事方式來演繹經典,讓原著《人生》迸發出新的時代價值,儘管有時間、空間的差異,但不變的是與原著一脈相承的精神內核。就像導演閻建鋼在接受採訪時曾經說的,“《人生》的內核沒變,都是在時代變遷中如何守住自己的堅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也一如編劇的初衷:“《人生之路》讓每個人都有了奮鬥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將理想和現實生活這個關鍵命題具象化了。”這並非是一句虛言——劇中,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着,例如高加林,始終希冀走出山村實現理想抱負;例如高雙星,在“竊”取別人勞動成果的陰影下回歸初心,積極向上地以一篇報道證明自己也非“池中之物”;例如劉巧珍,時常流露出對自己沒有文化的遺憾但從未一蹶不振;例如黃亞萍,無論何時都不曾放棄對鍾愛的舞蹈的堅持……
路遙所著逾15萬字的《人生》,結局停留在高加林被舉報後返回高家村的一幕,高加林未完待續的人生故事,在37集的《人生之路》裏有了延伸,不僅是他自己,書中那些青年男女面臨的困境都有了多元的選擇,無論是男主角們意外的交錯人生,還是女主角們註定的生命軌跡,皆有去向與歸處,而與原著不曾背離的,是他們在逆境中向陽而生的精神,一如既往地蕩氣迴腸;而對劇中人命運沉浮的思索,也一如既往地耐人尋味。
或許,忘卻《人生》裏諸人命運的“戛然而止”,能在《人生之路》尋找到未來也算是圓滿了期待,畢竟,那是我們或是愛着或是厭着的他們和她們,對個人命運的絢麗書寫有了終章。而這些從經典作品中走出來的角色,也因此有了新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