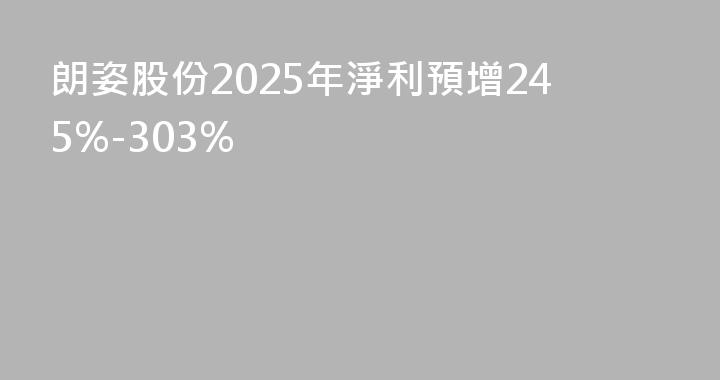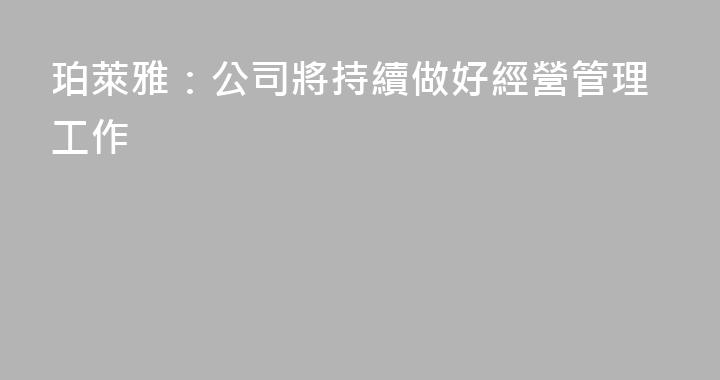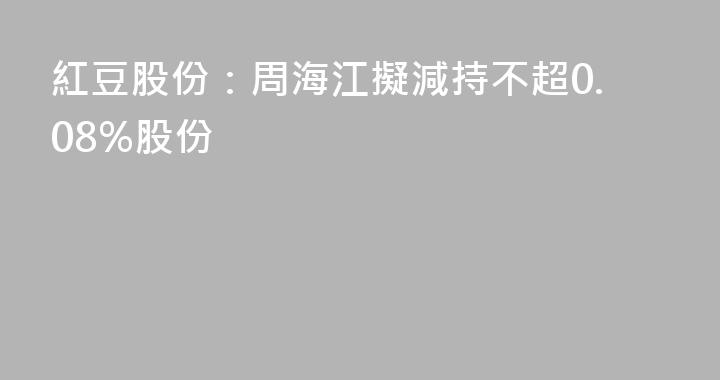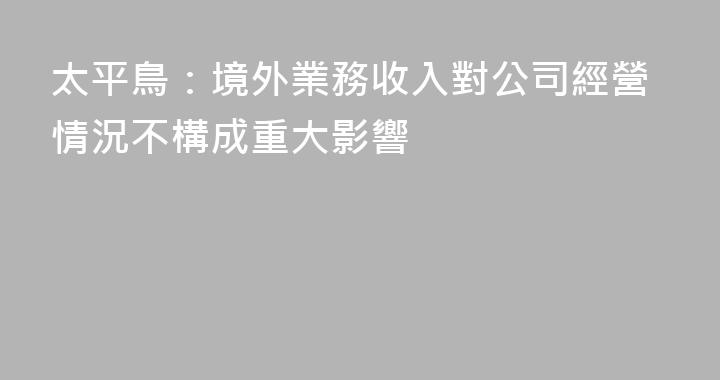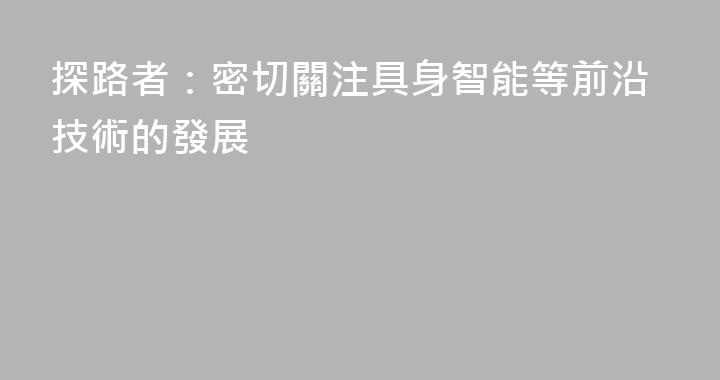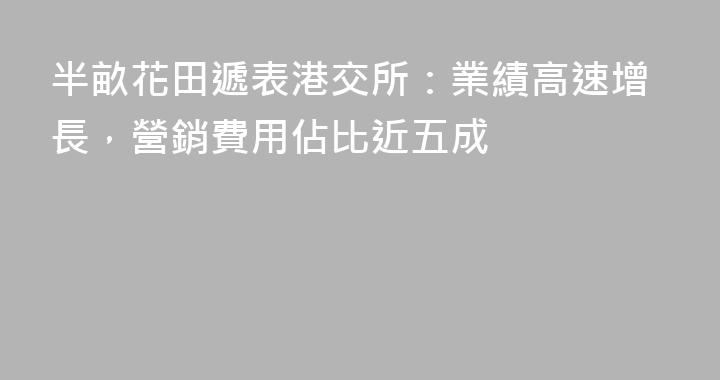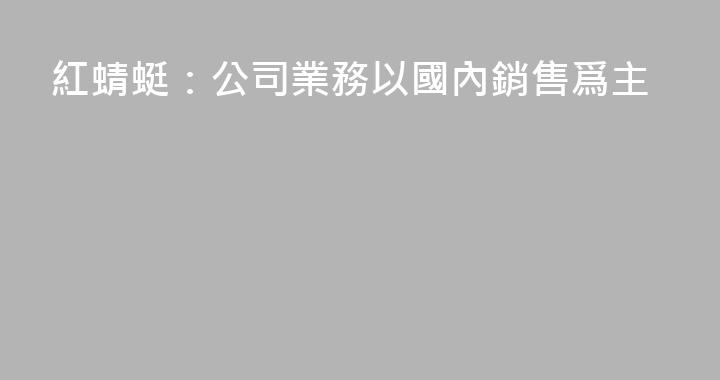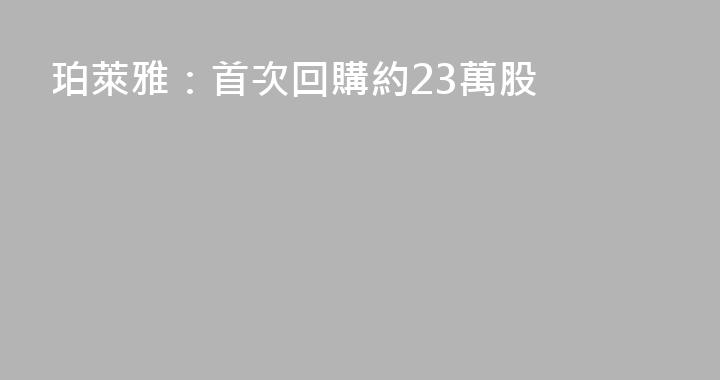4月15日,凌源影調戲《昭君叱賊》現場錄製已順利殺青,至此,凌源已在3年內創排6部影調戲,完成演出80餘場,受到觀衆熱烈歡迎。作爲遼寧地方戲曲之一,脫胎於皮影戲的凌源影調戲已有百年發展歷史,但在發展過程中,與國內很多地方戲曲一樣,凌源影調戲也陷入了傳承發展困境。2021年以來,隨着凌源採取多種舉措,這個充滿濃郁地方特色的戲種迎來發展春天。相關專家高度讚賞其示範性,表示地方戲曲傳承發展需多措並舉、政府與社會持續給予支持。
1、深具遼寧特色的地方戲種凌源影調戲近年重新煥發新活力
即使身着普通衣服,52歲的海兆鳳站在人羣裏也會顯得與衆不同,她自帶的藝術氣質讓旁觀者輕易就將她與其他人區別開來。對此,海兆鳳粲然一笑,“這可能是因爲我唱了幾十年戲的緣故。”
海兆鳳的戲劇生涯要從她14歲加入凌源市評劇團那年算起。不過,在唱了大半輩子評劇後,海兆鳳幾年前在自己的藝術道路上突然遇到二次“轉崗”。2021年,凌源市計劃創排影調戲《香槐嶺的笑聲》,海兆鳳因具舞臺表現張力和紮實的基本功被選中,在劇中出演重要角色。對這次演藝生涯的挑戰,海兆鳳欣然接受並刻苦練習。這一年,《香槐嶺的笑聲》在遼寧省第十一屆藝術節戲劇(小戲小品)展演中榮獲一等獎。
對海兆鳳來說,從評劇到影調戲,是她藝術生涯的悄然轉身;而對凌源影調戲來說,2021年則是遼寧這個地方戲種煥發新活力的重要年份。
若追根溯源,凌源影調戲——這個獨具遼寧特色的地方戲曲劇種是在凌源皮影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凌源位於遼寧西部,因大淩河發源地而得名。地處遼冀蒙三省區交匯地帶的凌源,幾千年來多元文化在這裏不斷撞擊與交融,使得這片土地禮樂興盛,文化積澱深厚,凌源皮影戲以及後來的凌源影調戲均植根於此。
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凌源皮影戲具有典型的遼西特色,僅就唱腔而言,演員大多掐嗓演唱,聲音高亢圓潤。因受東北地域文化影響,唱腔具有短促直平、大氣豪放的特質。脫胎於此的凌源影調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這一特點。不過與皮影戲演員躲在幕布後面表演不同,影調戲的演員則站在了舞臺中央,直接面向觀衆表演。
舞臺佈景與演員動作保留了皮影戲特點,再加之影調戲發展之初演出的小曲、小段多直接取自皮影戲,凌源影調戲一經問世,廣泛的皮影戲觀衆迅速轉化成了影調戲觀衆,使這個遼寧特色地方戲種廣受歡迎。
1945年,凌源三道河子組建了號稱“活人影”的影調戲班,其代表劇目有《姚憲殺妻》《牛順投案》等,這些彰顯着中國傳統社會價值判斷的戲曲被觀衆津津樂道。
新中國成立後,1959年凌源縣成立影調戲實驗劇團,這標誌着凌源影調戲走上了正規發展之路。劇團成立後,創排了《七仙女下凡》等多個劇目,同樣受到觀衆熱捧。1980年創排的凌源影調戲《寡婦門前》仍廣受好評,在同年遼寧省地方戲展演中獲一等獎。
然而,因多種因素綜合使然,凌源影調戲與國內很多地方戲種一樣,此後陷入傳承與發展困境,一時舉步維艱。
2
開展影調戲調研普查及劇種搶救工程,將戲曲表演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強對地方戲曲的學術研究等,多措並舉促影調戲傳承發展
“研一縷月光/落墨紙上/淚水抑或笑容/在寂寥中飛揚/夜色未央/有夢爲裳”。2022年,凌源市設立首屆市政府文藝獎,在廣播影視類特別獎的獲獎名單中,專注凌源影調戲劇本創作十餘年的王宇石的名字赫然在列。以上是活動組委會寫給他的頒獎詞,既充滿了浪漫詩意,又對他近年來的突出貢獻給予了凝練式的總結。
對凌源市文旅廣電局劇目創作室主任王宇石來說,“有夢爲裳”裏的“夢”,就是盡己之力,重振凌源影調戲昔日風采。2021年,王宇石進入了劇目創作高峯期,這一年,凌源影調戲也同步迎來發展曙光,逐漸呈現蒸蒸日上的發展態勢。
2021年,凌源影調戲《香槐嶺的笑聲》在遼寧省第十一屆藝術節戲劇(小戲小品)展演中榮獲一等獎;2021年《婆婆還鄉》在遼寧省第一屆農村戲曲小戲展演中獲得專家評委和現場觀衆的一致好評,並獲得遼寧省第十七屆羣星獎。
2022年,凌源創排並演出了大型影調戲《百合芬芳》,讓長久以來只能觀看十幾分鍾“小戲”的觀衆,有機會看到一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凌源影調“大戲”。這樣一部劇情跌宕起伏並充滿了濃郁地域特色的影調大戲,並代表遼寧省參加了“菊苑流芳——第七屆遼吉黑蒙四省區地方戲曲優秀劇目線上展演”。沉寂已久的凌源影調戲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對短短几年內取得的豐碩成果,凌源市文旅廣電局局長李宗傑既感欣慰,又覺任務緊迫。李宗傑早就意識到,對地處遼西地區的凌源而言,影調戲絕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戲種,它還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傳承傳統文化與主流價值觀的有效方式,更是百餘年來已與當地羣衆生活融爲一體的精神文化食糧。
秉持這一理念,李宗傑上任伊始就狠抓影調戲發展,在看到流散各處的影調戲創演人才因影調戲又重新聚攏時,開始實行“要在創排中發展,要在總結中提高,要在演出中活態傳承”的舉措。
由此,凌源市近些年力推影調戲的傳承與發展。一方面深入開展影調戲調研普查及劇種搶救工程,建立健全凌源影調戲保護傳承體系,詳細收集記錄劇目文本、影音圖譜、藝術人才等基礎資料,不斷填充完善藝術檔案或資源數據庫,實施拯救性整理和保存。另一方面積極探索凌源影調戲藝術傳承發展的新思路、新渠道和新模式,並將地方戲曲表演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同時加強對凌源影調戲等地方戲曲藝術的學術研究,爲其傳承和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對於人才,在加強培養的同時,暢通引進優秀戲曲專業人員通道,讓凌源影調戲後繼有人。
日前,又一部由王宇石創作的凌源影調戲《昭君叱賊》正式開始排演,這部戲將參加今年7月在大連舉辦的遼寧省第二屆地方戲曲小戲展演。屆時,唱腔嘹亮高亢、表演質樸大氣的凌源影調戲將再一次在全省觀衆面前亮相。與此同時,更令人充滿期待的潛藏戲迷內心多年、成立影調戲專業劇團的夙願也正一步步清晰起來。
3
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發展地方戲曲要樹立“在地化保護意識”
對凌源影調戲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長期致力於地方戲曲研究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學會會長王馗十分熟悉,“遼寧地方戲曲的起伏原因,與全國整體情況類似。”
王馗表示,如果將時間軸線拉長,我國地方戲曲所遭遇的挑戰其實始於百年前。在百餘年間不斷的社會轉型中,包括京劇、越劇、黃梅戲等在內的中國戲曲普遍受到衝擊,加之多元文化的發展和衝擊,更是擠壓了我國戲曲原有的生存空間。
“現在好像戲曲藝術只要放到劇場裏演出就行了,實際上,我們忘掉了戲曲曾經是中國人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婚喪嫁娶、節日慶典等緊密聯繫在一起,共同構築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態。但是,我們在大踏步前行的過程中,已經遺忘了這種曾經的生活方式。”王馗說。
中國地方戲曲遭遇挑戰的另外一個原因與戲劇院團相關。急速轉型的社會打破了戲曲院團原本的生存土壤,導致本應弘揚與傳承中國戲曲的專業團體缺位。
還有就是我國戲曲人才培養方式的特殊性,也決定了地方戲曲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傳統戲曲培養講究的是‘童子功’,也就是從小就要開始培養,不僅有口耳相傳,還要有師徒傳承,再輔以專業化的學校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優秀的戲曲演員,而這種人才培養模式本身還存在着高淘汰率。”
爲了讓中國戲曲重新煥發生機,自2015年起,國家從加強戲曲保護與傳承、支持戲曲劇本創作、支持戲曲演出、改善戲曲生產條件、支持戲曲藝術表演團體發展、完善戲曲人才培養和保障機制、加大戲曲普及和宣傳等多個方面明確支持戲曲傳承發展。
我省有評劇、遼劇、阜新蒙古劇、海城喇叭戲、凌源影調戲、鐵嶺秧歌戲和二人轉7個地方戲種。對遼寧地方戲曲的現狀,王馗如數家珍,並鼎力支持包括阜新蒙古劇等在內的多個遼寧地方戲種的發展。
“發展地方戲曲一定要樹立‘在地化保護意識’,不僅要保護本鄉本土的地方戲曲,還要包括跨地區的戲種,凡是本地區生存的劇種和戲劇形態,都應有所保護。比如說京劇、評劇等這些跨地域戲曲劇種,都要本着‘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原則大力予以保護。”王馗說,所謂的“政府主導”,具體來說,就是政府要爲戲曲發展建立良好的發展機制,並建立健全相關的制度體系。近些年來,國內戲曲藝術發展較好的地區,比如江蘇的崑曲、廣東的粵曲之所以取得長足發展,與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社會參與”則強調的是讓戲曲真正回到社會空間裏去,修復並維護好戲曲原有生態。比如,要將戲曲的種子根植在少年兒童心中,讓孩子們從小就培養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戲曲的意識,培養他們對傳統戲曲的喜愛。同時,還要大力營造戲曲文化生態空間,在重大的節日慶典和文化活動中,爲戲曲騰挪出充分的展示空間。
在王馗看來,戲曲並不只是一門表演藝術,它能在一個地域紮下根來,實際上在漫長歲月的演進中,已與這片土地上的各種要素深度交融。比如說皮影戲,它不單單是一個戲曲,它的演出儀式和展現內容,已與地域人羣的人生禮儀、文化習俗等緊密聯繫在一起。隨着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戲曲進入劇場演出,實際上,劇場劇院並不是一個孤零零的藝術展示舞臺,它更是城市社區的組成部分,而在這裏演出的地方戲曲,也應該是社區文化的重要部分。
王馗表示,發展地方戲曲,還要高度注重戲劇院團的建設。傳統戲曲的傳承與發展,離不開專業劇院團。劇團內的演職人員都經過專業化訓練,他們是傳承發展戲曲的主力軍,將地方戲曲的藝術之美對外呈現,主要依靠的還是專業院團。
在對劇團的保護髮展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劇團內部專業化問題。業內常說,“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在一個劇團內,經常會同時存在多個流派,只有保留並保持住不同流派的特色,保持劇院團的藝術風格和創作者的藝術理想,才能將地方戲曲更好地傳承發展下去。
儘管唱了大半輩子的戲,但站在影調戲的舞臺上,海兆鳳仍覺自己內心激情澎湃得像一名年輕人,“影調戲是我們凌源的瑰寶,我願意永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