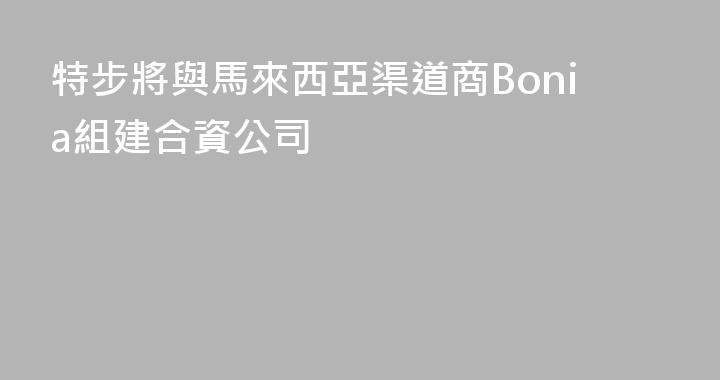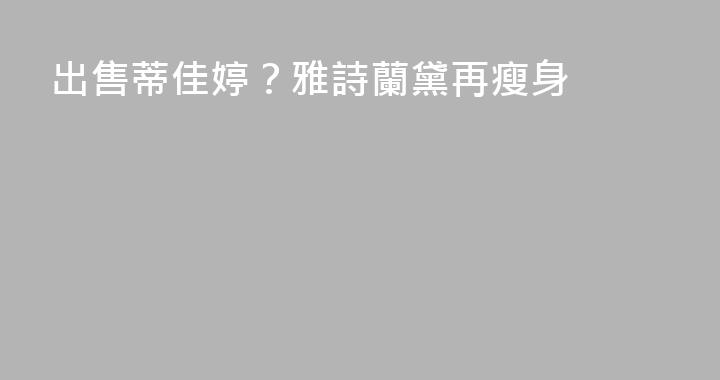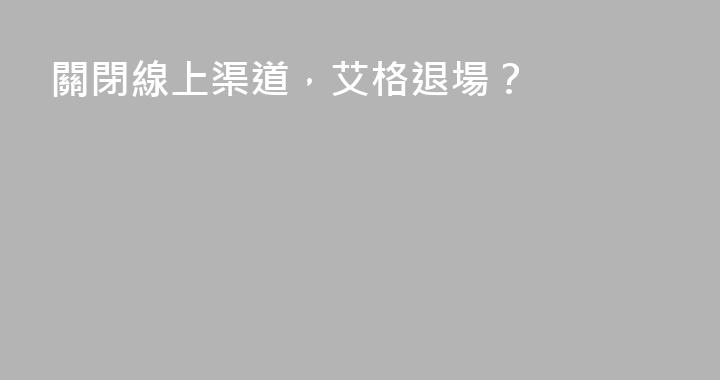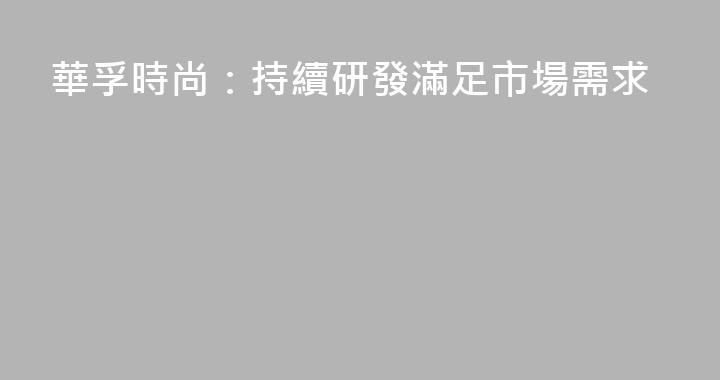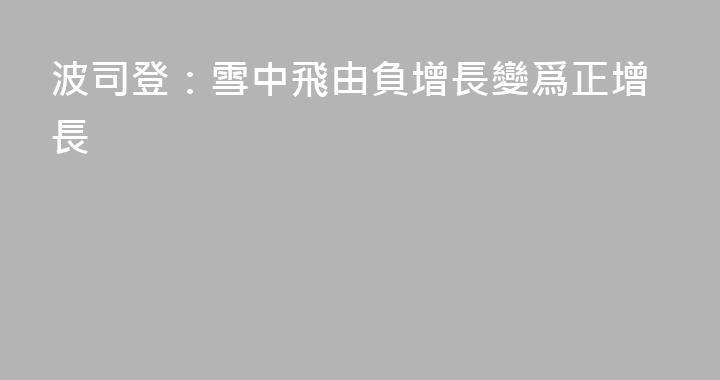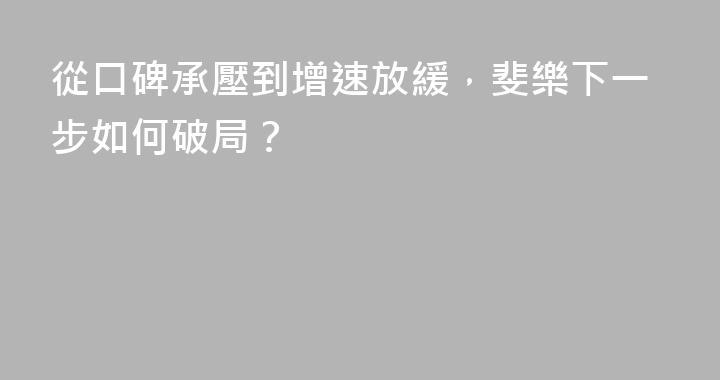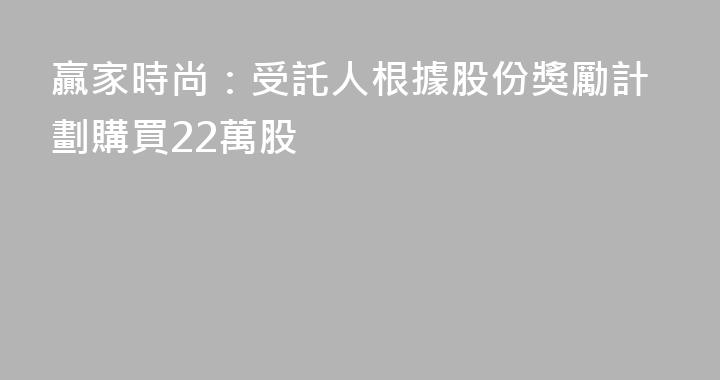“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這是《不虛此行》電影導演劉伽茵很喜歡的一句話。在這個故事裏,曹保平作爲監製,胡歌和吳磊再次聚首,他們和齊溪、白客共同去詮釋這個關於普通人生活的故事,去詮釋普通人生活中的“傾聽”。想作爲人活着,想作爲人死去,就像這部電影所表達的:每個普通人都應該得到尊重,每個普通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

看到胡歌的臉時,劉伽茵覺得,她終於見到了聞善。

黑色襯衫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聞善是個三十五歲的獨身男人,生活在北京。以前他是個失敗的編劇,後來以爲逝者寫悼詞爲生。他也是劉伽茵執導的電影《不虛此行》的男主角。這個人物,在劉伽茵的思想中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但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輪廓和一些姿態,看不見他的臉——直到電影開拍的那一天。

暗紋西裝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抵達它則是個漫長的過程,起點在1995年。那年是世界電影百年誕辰,央視做了一套專題片,那還是用摳像的時代,後景是電影畫面,孫道臨老師站在前景,按時間順序,從誕生,到各種流派、代表作、名導演……講了一遍簡明的世界電影史。那年劉伽茵還在上初中,每天午休時回家,就看這套專題片。她第一次看到了新現實主義、新浪潮,看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因爲爸爸媽媽喜歡看電影,劉伽茵從小也喜歡。《搖滾青年》《頑主》《第一滴血》……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好電影都是爸媽帶她去電影院看的。電影對她而言,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看專題片的時候,她被那些突然出現的電影片段和所探討的東西強烈地吸引了。
那是90年代中期,錄像帶的時代。專題片中出現的那些電影是不可能接觸到的。爸媽發現了劉伽茵的興趣,買了一些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書給她。就這樣,從文字而非影像,她開始接近電影。

白色短袖、亞麻長褲Brunello Cucinelli
劉伽茵還記得當時讀到的那套《世界電影鑑賞辭典》。一套三本,紅色硬皮戴着護封,鄭雪來主編,撰稿人水準非常高。那是劉伽茵的啓蒙讀物之一。後來,她將它放到了《不虛此行》中,聞善也讀過它。
從初中到高中,電影抵擋住青春期的善變,逐漸成爲一件認真的事情。那時候,在圈外人的眼中,電影行業很神祕,從業人員很神祕,電影學院也很神祕,因爲神祕,所以很難考。但是要學電影,就只有這麼一個大學可以考。劉伽茵的學習很好,性格內向,本來老師建議她學歷史,但父母都還很支持她去考北電。於是就考。當時電影學院的文學系和導演系都是隔年招生,1999年輪到文學系招,劉伽茵在那一年考入了文學系電影劇作專業,學習寫劇本,主任教員是曹保平。
劉伽茵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長,但是,她不像大部分北京人那樣,有鮮明的方向感。上大學之前,北京對她而言是灰突突的一片,她是其中更小的一個深灰色的小點,只在家附近的一個極小的範圍內活動。考上電影學院,爸爸跟她說了一句:“電影學院在薊門橋的北邊。”——上大學,離開家,對她而言就是離開從小到大生活的區域跑到了薊門橋北。這離開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一秒鐘,這一秒鐘後,她瞬間獲得方向感,自此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辨別出東南西北。
在電影學院,劉伽茵一待就是十幾年。本科畢業讀碩士,然後留校任教。2005年,她自編自導自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作品《牛皮》,片子裏只有三個角色,父母和他們的女兒。實際上就是劉伽茵自己和爸媽的家庭生活。那是一部很極端的電影,具象又抽象,壓抑,焦慮。她說:“我對完美一類的事情不感興趣……我們無非是在表演我們的生活。”幾年後,她又拍了《牛皮2》,之後,是長久的沉寂。

白色短袖、亞麻長褲Brunello Cucinelli
長袖襯衫 Icicle
幾年前,劉伽茵搬到了北京的郊區。這裏什麼都是新的,很寬的馬路,嶄新的小區,綠化很好,基礎設施還沒跟上,有大片的空地,沒什麼人,很安靜,完全不像北京。她喜歡這裏不像北京。她是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從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記得,而且還有細節和溫度。但是對於北京,她沒有歸屬感。她覺得自己只是作爲一個成年人,選擇在這個城市待着、活着。偶爾,有一些稍縱即逝的瞬間,比如從學校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從北騎到南三十多公里,到長安街的某一段,有那麼五分鐘,不用看導航,路在輪下自己展開,帶來大量的安全感,她會短暫地感到自己是個北京人。“那幾分鐘裏,特別自在,感到我和這個城市之間很親密的關係。”但,也只是那短短的五分鐘而已。
她像是存在於城市的一個懸浮的人。聞善也是。他只是在這兒上學和留在這兒生活,他活在這兒,和這個故事裏面的很多人一樣。
聞善的故事浮現在2015年左右。當時不只有聞善,還有其他生活、工作在這座城市的人,但它沒有最終完成,以雛形的形式存在電腦硬盤中,也存在腦海裏。那時候,劉伽茵上下班路上的時間很長,她在地鐵上,北京的地下,從這座城市的北邊穿行到南邊。她抱着電腦看學生作業,寫劇本,想這個故事。之後,聞善出現了,故事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逐漸清晰。2019年底,劉伽茵真正動筆,開始作大綱和分場。後來疫情暴發,大半年的時間她在家裏,每天早起,喝咖啡,寫劇本,然後外出散步,跑步,回家洗澡,繼續喝咖啡,抽菸,寫劇本……開學了,也是上網課,作息差不多。
那一年劉伽茵40歲。《牛皮2》完成後,多年來,就像一片陰雲或噩夢,某種說不清楚但強烈的直覺壓在她的頭頂,有的時候來,有的時候走,有的時候大面積地來,然後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讓她清晰地意識到,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得做我該做的事情”。

曹保平說,劉伽茵是一個和他完全不一樣的導演。在這一次的拍攝現場,“她好像是在進行一個祕密拍攝,偷偷摸摸的,雖然我們是名正言順的一個良善的行爲”。整個劇組都似乎逐漸“聞善化”。
曹保平自己是個非常有掌控力的導演。“只要我說往河裏去,岸上就不能有人”他比劉伽茵年長,但經歷相近,也是電影學院留校任教,從編劇開始導演。他說:“我覺得沒有對錯,每個方法都是正確的方法,只要這個方法執行下去它就是。她既然能執行下去,她這樣的方式就讓她去吧。”

短袖Polo衫、西裝長褲、流蘇綴飾皮鞋均爲 Brunello Cucinelli
教劉伽茵的時候,曹保平覺得她是一個特別努力,做事非常認真也非常較勁的學生。“我覺得最強烈的感覺和特點是她有自己在審美上想要表達的、堅持的東西。”
拍完《牛皮》以後,大概十年左右劉伽茵沒有拍片。這期間,曹保平跟她說過好多次,他覺得她的風格太獨特了,應該往下繼續。“迄今爲止,我也不知道她停下具體的原因。”曹保平說,“當然是因爲可能教學上她付出的精力比較多。但是我覺得可惜,就一直鼓勵她還是要拍。這句話我說了好多年。”
劉伽茵把曹保平當老師也當長輩。“也包括我父母,他們看我的一些事情比我自己要看得清楚。所有的這些,在瞭解和支持我的基礎上,也算是一個善意的壓力……他沒有直接表達出失望。我覺得更多可能是我自己對我自己失望吧。”
劉伽茵覺得自己可能是一個成長上不協調的人。
本科四年,劉伽茵的壓力很大,緊張、焦慮。當時家裏條件不好,對電影的熱愛又帶來了過多的使命感,使學習變得沉重。她非常認真地上課,非常認真地寫作業,花儘可能多的時間在學習上——後來就被曹保平認命爲班長。但是除了學習,她感覺自己什麼都沒做,並不想跟別人交流,也的確不需要交流。“因爲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有我要完成的事情,那是沒有退路的。”上到大二,她開始寫電視劇掙錢,只有很少的時間睡覺。直到現在,劉伽茵還是這樣的體質,每天可以只睡幾個小時依然精力充沛。

黑色襯衫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2003年非典,劉伽茵一直在家裏。內心的聲音響了起來:你丫趕緊的。之後,就有了《牛皮》。
再之後,就是考研、讀研,然後留校當老師。研究生階段,成長滯後的部分開始慢慢復甦,她纔有了和同學共同生活的感受。留校教書是她最滿意的選擇。“我是喜歡當老師的,我覺得若干個身份裏面,可能老師是我對自己最滿意的一個身份。這個部分我覺得帶給了我很多很多好的東西,樂趣、難度,很多事情是無意中在漫長的教學時間裏面明白的,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同理心。”但漫長而投入的教學工作給創作帶來了矛盾。那個聲音還在,但在她的頭腦裏,有些東西在一直打架。
2021年,劇本定稿。劉伽茵拿着劇本自己跑了跑,最後還是找到了曹保平。曹保平看完,第一感受就是長。“太長了。因爲我的劇本就夠長的,但是這把我的劇本都踩在下邊了,是我的劇本兩倍長。”曹保平說這要拍5個小時,肯定是不客觀的,“因爲我有非常強烈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是教訓”。但他認爲這個劇本有它的可行性和空間,於是開始推動。從曹保平第一次看到劇本到開機,不過經歷了半年時間。曹保平擔任這部電影的監製。
開拍的時候,劇本刪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但曹保平覺得依然很長。“但是因爲考慮到她這麼多年沒拍,我這次給她的容錯空間到30%甚至更多。”
最初看到劇本時,打動曹保平的還是故事本身。“每個東西總有多多少少打亮你眼睛的那一點。她寫了聞善和每個家庭的關係,以及每個家庭裏中國人的人情世故。聞善的抉擇,悼詞寫作這個職業,以及他們的角度,都有劉伽茵相對獨特的一面。這是我覺得這個片子最閃亮的原始出發點。”

短袖Polo衫、西裝長褲、流蘇綴飾皮鞋均爲 Brunello Cucinelli
像近幾年出現的類現實主義影片一樣,《不虛此行》討論的仍然是現實問題——普通人如何“找自己”?。因爲帶着劉伽茵自身的特質,它同時又是個寓言,是“嘗試性的現實主義”。“因爲我們其實只能觸到表皮。你穿透皮膚,疼,行了,就夠了。”曹保平說,“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還是比較難的。我們能在旮旯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東西,但是它永遠藏在陰暗的角落裏。”
曹保平告訴劉伽茵:“你最大限度地按你想象的去拍,不要顧及其他的東西。”90%甚至更多的時間,他都在現場,但他不會給劉伽茵任何具體的要求,只會在她選定的方向上提出建議。“我覺得我這個監製不是背書,不把我的審美意志,或者說商業意志加進一部作品裏。有一種監製是給予一個新人最大的表達空間,它和我自己審美上,電影方向上,都沒有一毛錢關係,但是我的權重可以保證新人百分之百去完成他要的東西——這不是一個更好的監製嗎?”

《不虛此行》的拍攝一共進行了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有過很多艱難的時刻和巨大的壓力,然後,拍攝完成了。之後是剪輯,劉伽茵在她家裏每天與同事一起工作,同事以前是她的學生,這次特地回來幫她。
劉伽茵又回到了喝咖啡、跑步、工作……無限循環的作息。她並不像曹保平描述的那麼“偷偷摸摸”,拍攝中,她有過六七次大發雷霆。只是,按她自己的描述,她的情緒很少,“大概只有五種”。影片接近完成,她的情緒是“平靜”。“它讓我平靜,讓我能夠感覺到自己的位置。不是滿足。”
從開始討論到拍攝,一直到現在的剪輯,劉伽茵一直用“聞善”稱呼她的主演胡歌。胡歌和她都覺得很自然,本應如此。

黑色襯衫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胡歌,不,聞善,與劉伽茵討論過很多次,聞善是否真實存在?劉伽茵實話實說:“我在生活中不認識這樣的人,更不可能做過什麼採訪,我之所以去寫不是因爲我看了什麼新聞或者怎樣,他就是在心裏……那個人其實就是我,是理想化的自己。雖然那個人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並不理想,但是對我來說是的。”
到了拍攝時,在劇照中,聞善與劉伽茵呈現出一種奇異的同頻,一個高大,一個瘦小,但都微微駝背,低着頭,臉上曖昧不清,有點呆滯,也有點感悟的樣子,有時候咧開嘴笑,要麼揹着手站着,要麼蹲着,表情和身姿都出奇的一致。
劉伽茵說聞善身上最好的地方是“自卑”。“我覺得自卑是一個非常好的品格。它能夠讓你腳踏實地,它能夠讓你總是被誤解而沒有機會誤解別人。聞善不會誤解別人,他會留有餘地,但是他始終被倉促地、粗糙地誤解。同時他能夠接受所有的對待,這造就了他現在的生活——當你有自卑這樣的好品質的時候,你就能看得清、聽得清,你不會高擡自己,你很少覺得有什麼東西是你應得的。”
電影中的聞善自始至終在替別人、替逝者找自己。在這樣的創作中,他建立了短暫但深刻的關係去放置自己綿長的情感,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是劉伽茵那個更理想的自己。劉伽茵說,聞善很溫和。“他比我要溫和。他的工作完成之後,投入的情感並不一定能夠戛然而止,但工作結束了就是結束了,他不再有一個位置繼續維持和他人的聯繫。所以對於聞善來說,需要他不斷去學習。他應該也沒有學得太好,但是他還有時間。”

暗紋西裝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不虛此行》的寓言性正在這裏,關係的短暫脆弱與情感的綿長,在這樣一個極端的故事中,人類亙古的孤獨得以被討論。“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這是劉伽茵很喜歡的一句話。“大家其實都在說,都在表達……但很少有人願意去聽。”
劉伽茵說她沒有表達欲。“我沒有要說話的慾望,我也沒有存在的慾望,我的生活不需要這些。這些同時也提供了更多誤解我的機會。”而拍電影,就是她的表達。《不虛此行》的形式是現實主義,但所表達的東西是理想主義的。這表達幾乎一定要被誤解、曲解,或承接各種各樣的評判乃至誤讀。劉伽茵說,沒有關係。“我是這樣的人,我用這樣的方式生活和工作,我就得接受被誤解。我覺得一個作品,即便是一個認真的作品,它也肯定會被誤解,這沒有那麼重要。”
電影拍完後,聞善,不,胡歌,告訴劉伽茵,他覺得不用再去想“聞善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了。他說,其實不用去想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你是不是希望這個世界上,這個城市裏,有一個像聞善這樣的人。”
這是聞善與劉伽茵,劉伽茵與胡歌,直至他們自己與自己的共識,一種非常難得的默契與信任。“我覺得這是最美好的事情。它是求不來的,但我就是碰上了,他也碰上了,所以會覺得非常美好,也很圓滿,我很少有這樣的感受。”

黑色襯衫外套、長褲、皮鞋均爲Giorgio Armani
聞善是一個更理想化的自我,這個想法產生於何時,劉伽茵已經不記得了,她只是知道:“這個人和我的關係,這種感受是在以前所有的創作裏都沒有的,可能以後也不見得會再有了。創作都會有很多遺憾,但是真的不重要。對我這個人的誤解這麼多年我都能接受,對電影的誤解算個屁。生活有更多的遺憾,所以創作的遺憾不算啥。”
寫《不虛此行》的時候,有一些戲、一些對話是自動寫出來的,劉伽茵不知道她是怎麼寫的,包括某些特別重要的部分其實沒有思考過程,更像是自動寫作,就像她所喜歡的跑步,跑到一定長度會有的興奮感,這也是求之不得的。劉伽茵說:“我只能說希望以後還有這樣的創作。”
“我這次還真的不會停下來,我過不了多長時間就要開始寫下個故事——可能後面再寫的東西,主人公還是一個聞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