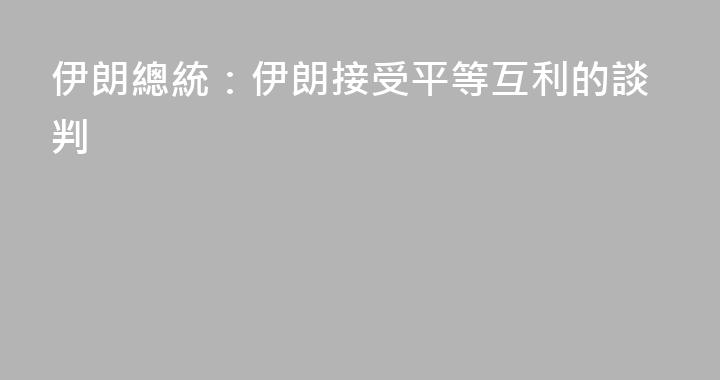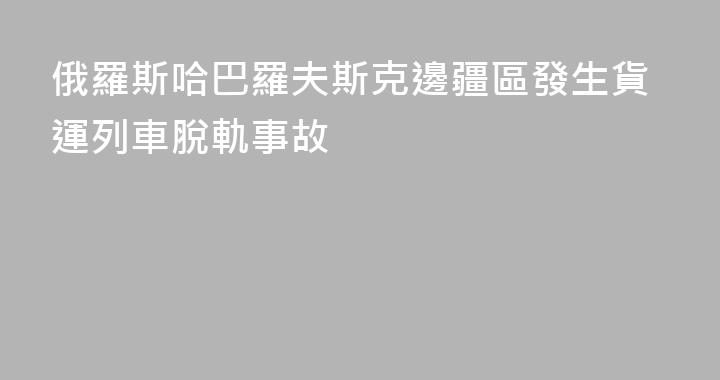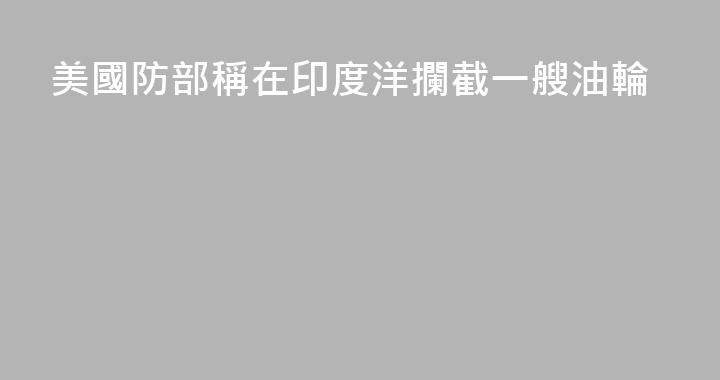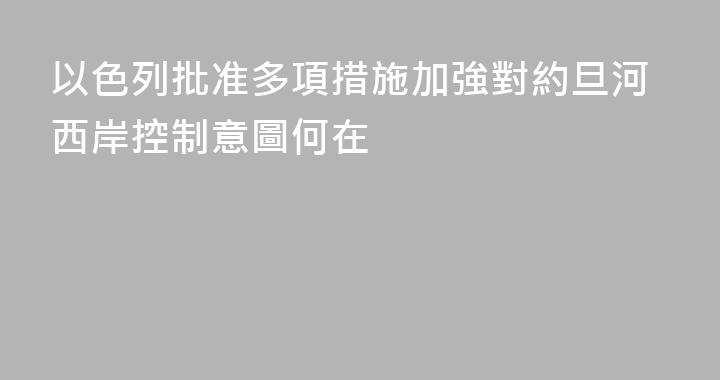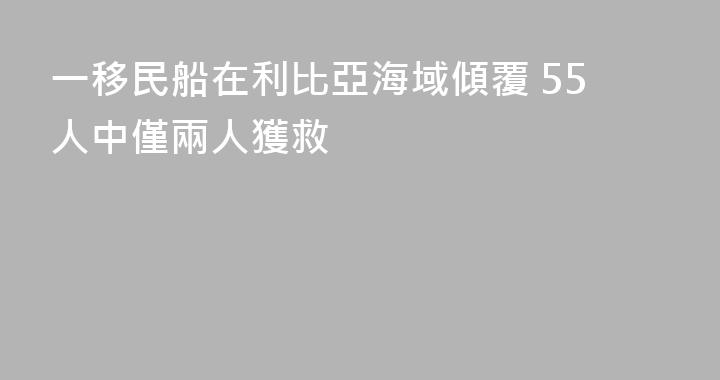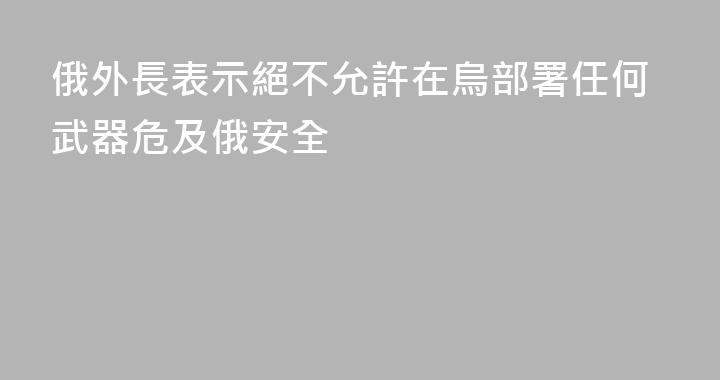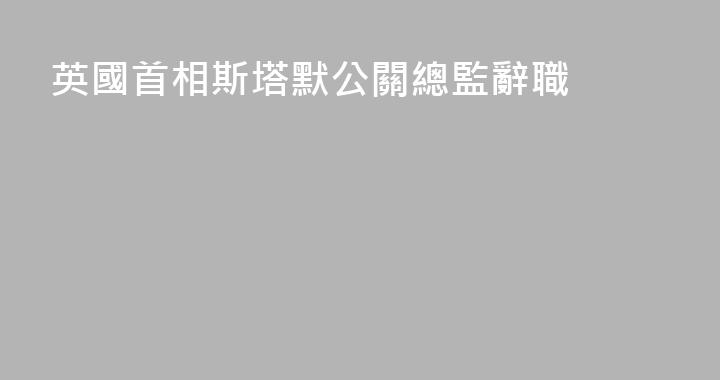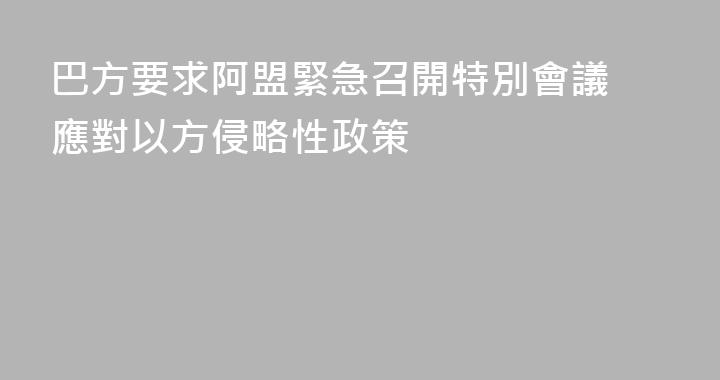《日本經濟新聞》11月25日文章,原題:印度真正自主,需要清晰、有效且自信的戰略 30年來,印度一直試圖在不放棄控制權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現代化,有選擇性地向全球開放投資,同時堅持獨立自主。這種雄心壯志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印度對戰略自主的追求往往可能演變成防禦性的官僚主義,而印度經濟需要的恰恰是它所抗拒的一些元素——外國資本投入、外國專業技術輸入以及與全球市場進行可預測的互動。
對外合作變“互相背刺”
戰略自主的概念本身沒有問題,但關鍵在於印度追求戰略自主的方式——它應該協調國與國之間的依賴關係,然而印度卻完全拒絕這種做法。無論是通過責任糾紛、本土化規則還是變幻莫測的法規,印度每一次試圖維護主權的努力都會拖慢保障其權益的進程。
這種“矛盾”模式出現在印度許多領域。例如,印度與法國公司合作建設的傑塔普核電站項目,一度被設想爲“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核反應堆綜合體”,然而在經歷15年有關責任法律和監管歸屬的爭論後,該項目仍處於停滯狀態。這項原本應成爲“對外合作”象徵的工程,如今卻成爲“互相背刺”的典型案例。
在汽車行業,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撤出印度市場,業界通常將其歸咎於該國監管的不確定性。印度在汽車市場的失敗並非僅僅因爲對本土企業的保護主義,更在於它並未營造一個足夠靈活的環境,可以根據全球形勢變化而適時進行自我調整,以留住投資者。換言之,真正導致印度資本外流的並非保護主義本身,而是其政策的不連貫性以及缺乏適應能力。
印度曾試圖改造其老舊且污染嚴重的燃煤電廠,邀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提供排放控制技術,但隨即又以“成本過高”爲由拒絕引入外國技術,轉而採用未經檢驗的印度國內方案。這導致工程延誤、產能浪費,以及長達10年的霧霾問題。在印度各行各業,這種自相矛盾、前後不一的套路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經濟面臨兩難困境
印度的“矛盾”也體現在其外交政策上。2014年印人黨執政以來,印度當局不再提及“不結盟”一詞,取而代之的是“多向結盟”(印度將在不同議題上依據自身國家利益作出結盟或不結盟的決定——編者注)。該政策承諾行動自由,但實際上印度的經濟和政治訴求卻時常相互衝突。譬如,新德里一方面購買打折的俄羅斯石油以抑制國內通脹,另一方面又積極爭取西方資本和技術。這些舉措在戰略上合情合理,卻減緩了印度融入亞洲供應鏈的進程,對沖地緣政治風險的本能反應也導致了印度經濟的分裂。
同時,對印度的投資也在降溫。第46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3年,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47%。製造業佔印GDP的比重停滯在14%左右,已長達10年。如果資本和技術不能大規模流動,原本應是戰略優勢的年輕人口可能會變成國家負擔。
印度面臨着真正的兩難困境。它認爲,融入東亞供應鏈固然能帶來經濟增長,但也會帶來依賴性,而這些依賴性或許也會帶來危機。實際上,對印度而言,在某些情況下,拒絕融入可能比明智地融入更加危險。
因此,印度需要自己的雙循環模式,也就是“清醒依賴”:一種管理國內增長與全球增長循環不對稱性的戰略。它基於三個要素:規則清晰,即投資和技術轉讓規則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執行能力,即監管機構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執行這些規則;增強信心,如果能夠引導外國參與服務於印度的項目,那麼選擇性的依賴可以增強而非削弱印度主權。
清晰的依賴政策可能意味着允許外國股權公司投資符合印度當地研發要求的初創企業,或者在保持關鍵礦產主權儲備的同時融入亞洲電池供應鏈。
將自我孤立誤以爲強大
印度主要面臨的障礙並非無知,而是聯盟策略的混亂。印度政府存在內部分裂,彼此之間也有潛在的制衡力量。電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出口導向型企業越來越需要供應鏈整合,具有競爭力的地區政府正在嘗試對投資者友好的模式。印度新一代科技企業家將開放視爲一種優勢而非劣勢。如果政策開始獎勵取得效益的公司而非保護本地公司,這些羣體或許能夠形成一個核心聯盟,實現“清醒依賴”。然而,他們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在汽車和鋼鐵行業,印度出口導向型企業仍然遠遜於受保護的傳統企業,地方政府更注重吸引投資而非改革。
印度自身的一些成功案例表明,這種協調是可以實現的:數字支付革命源於政治激勵以及官方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協力參與。這說明戰略自主都是通過多方合作,而非自我封閉來實現的。當印度政府的目標、官方機構的協調能力和市場能力指向同一方向時,可能實現共贏。新德里需要的不是配方,而是相應的政治協調能力。這種清醒的依賴是一項政治工程,印度的戰略自主也是一個合理目標。只有當印度不再將自我孤立誤認爲強大時,戰略自主纔可能實現。(作者亨利·霍普伍德-菲利普斯,白鷺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