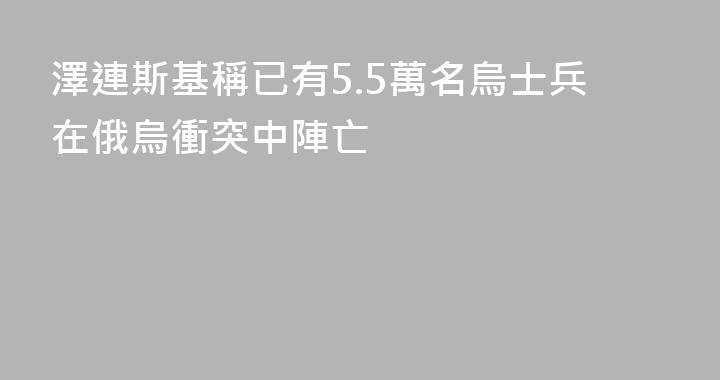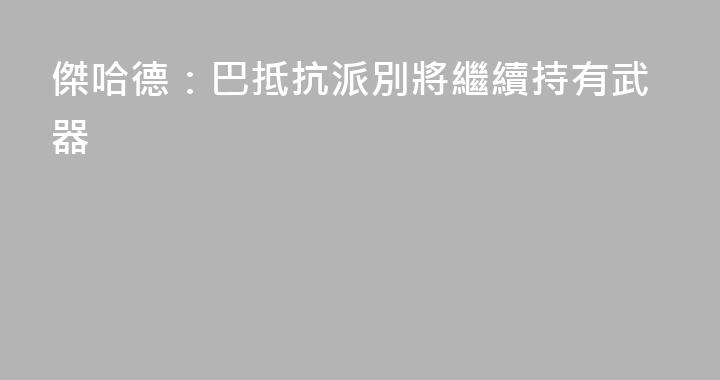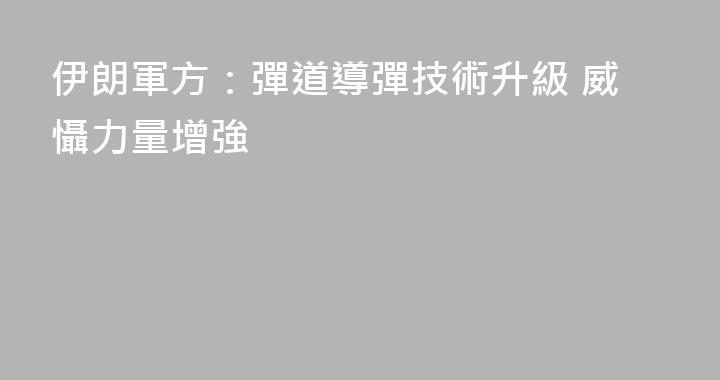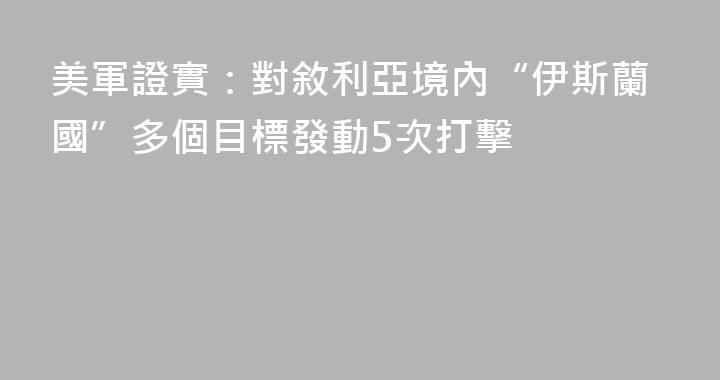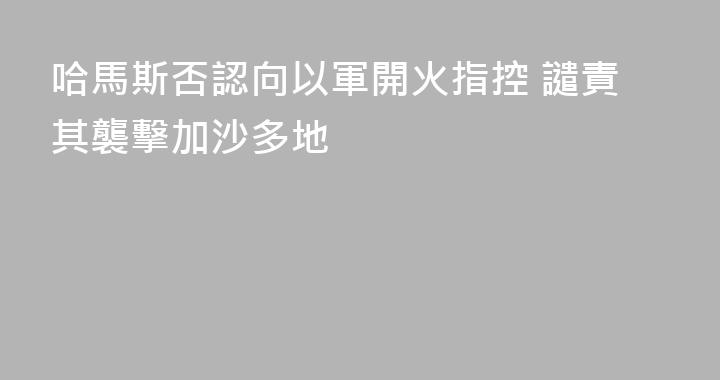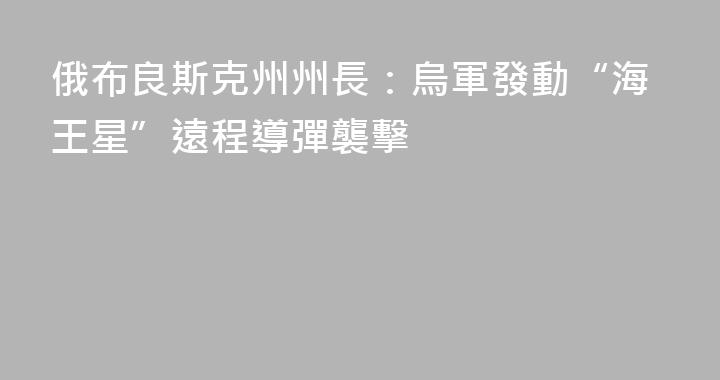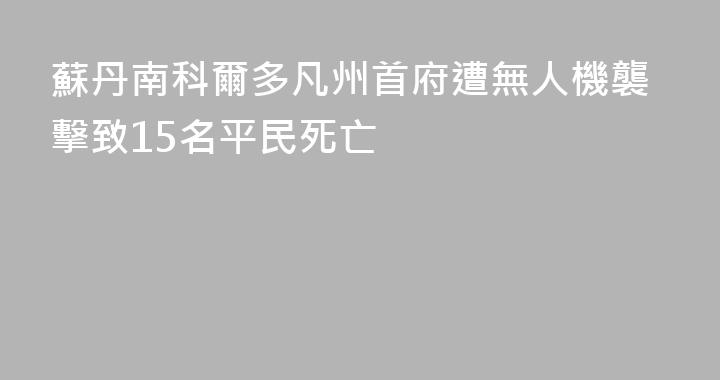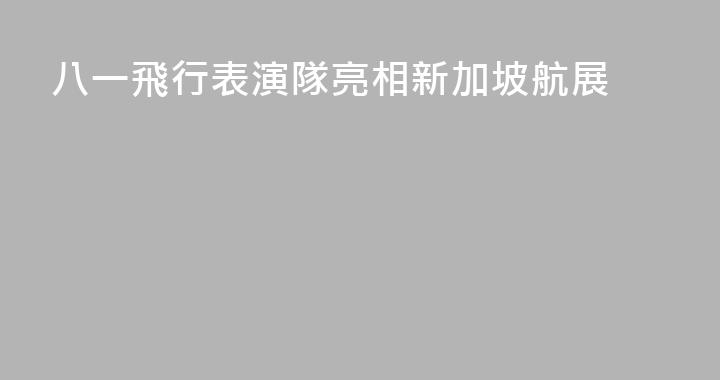潛艇兵的奮進之路
■解放軍報記者 程 雪
科學數據顯示,從水深150米開始,進入水中99%的光線都會被海水吸收,海底世界由此進入黑暗。
黑暗無光的深海之路上,一艘潛艇幾十天甚至上百天在水中游弋前行。
路,是腳下的方向,是前行的軌跡。沿着這條軌跡向遠方堅定前行,電工技師黃井磊和戰友們一次次出發,將自己的青春與成長書寫在深海之路上。
這條路,鐫刻成長的腳印——
遠航時遇到大風浪,即使再有經驗的老兵也會眩暈。一次遠航,電工技師徐亞胃裏翻江倒海。他和戰友們在戰位旁邊放一個小桶,一邊值更一邊吐。難受的感覺讓他近乎絕望,他咬緊牙關,硬挺着堅守戰位。
周禮是潛艇上的一名通信技師,負責的工作之一是信息發報。剛接觸專業時,他啥都不會,發送一串報文要花費很久。長期專注地進行發報訓練後,如今他不用看電鍵,只要聽到按鍵聲音,就能根據按鍵聲音的音色和音調高低,判斷其代表的內容。
多年潛艇兵的經歷與紮實的訓練,讓電工操縱長雷磊磊的身上平添了幾分從容的氣質。艇上遇到的絕大部分故障甚至險情,他都能從容應對。對於徒弟,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別慌,按平時訓練的程序來。”
這條路,見證執着的奮進——
水下長期密閉的環境,賦予了潛艇兵一般人難以具備的能力:在一些時刻真正忘我,眼裏只有一個目標,更加純粹專注於自己的職責。
在聲吶技師臺學超的世界裏,似乎只有“聲音”與“聲音代表的含義”兩件事。戴上耳機,聲音信號有規律地響起,臺學超凝神專注,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他的大腦就是一個巨大的“海洋聲音數據庫”,耳朵總是先於其他感官開始感知。根據聲紋信息,臺學超能精準判定聲紋背後的物體,甚至還能細化不同聲紋信息,判斷同一物體的不同狀態。
記者能夠感受到,沉浸在純粹專注世界裏的潛艇兵,非常渴求新知與成長。
路在腳下,心向遠方。
“每天都有新的東西要學”“我還有很多不會的知識要掌握”……採訪中,這是不同崗位潛艇兵常說的話。不出海時,黃井磊喜歡去公園或海邊等開闊的場地跑步。那天,陣陣微風拂面,腳踩在堅實的土地上,他迎着光,追着太陽向前跑。
“執掌大國重器在深海之路上巡航,我一定幹好工作,不負期待,不負重託!”黃井磊說。
向前,向深海,向未來
■解放軍報記者 程 雪

潛艇出航。

潛艇兵進行脫險基礎訓練。
這是一個密閉無窗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裏,頭頂是微弱的燈光,耳邊充斥着嘈雜的噪聲;
沒有網絡,不能與外界聯繫;
要持續在這個環境中生活幾天、幾個月甚至更久;
因爲水資源有限,不能經常換洗衣服和洗澡;
空氣不流通,柴油味、身上的汗味和各種機械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不斷刺激着神經……
很少有人會想象這樣的情境。
事實上,對海軍某基地某艇員隊電工技師黃井磊而言,這樣的環境與工作狀態早已習以爲常。
潛艇遠航時,黃井磊每週都會爬上陡峭的舷梯、穿過狹窄的通道,開始他的“巡線之路”:從艦艏走到艦艉,查遍近百條線路和電纜,細心巡檢密若蛛網的潛艇管路和儀器閥門的電路安全情況。
入伍20年來,這條連接艇上不同戰位的“巡線之路”,黃井磊走了無數次。
這條路不長——黃井磊每次巡線的直線距離,不過數十米。
這條路很長——潛艇一次出航,征程便是千里萬里。正是因爲有黃井磊和戰友們在水下日復一日地堅守和付出,潛艇的航跡纔不斷向遠海大洋延伸。
1974年8月1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正式編入人民海軍戰鬥序列。凝望深海里的這條路,我們彷彿能感受到新時代潛艇官兵對“長征”精神新的接續與傳遞:鑄造堅不可摧的水下鋼鐵長城,向前,向深海,向未來……
成長之路上,他們變得和潛艇一樣“精密”
沿着“巡線之路”出發,每每引起黃井磊警覺的,是不同艙內設備聲音和氣味的變化。
在黃井磊看來,設備運轉的轟鳴聲也是有規律可循的:某型裝備內部發生故障時會發出“咔咔”的摩擦聲,發動機正常運行時是低沉的“嗡嗡”聲,甚至在一臺尚未出現故障的裝備中,聲音頻率高低的變化也能反映出裝備的狀態……
此刻,一臺正在運行的裝備似乎發出異樣的聲音。黃井磊俯身,緊皺眉頭,貼着裝備仔細聽。直到檢查完畢,確定裝備無故障,他才放心繼續向前走。
在潛艇上,一名成熟的電工技師必須善於發現細節。
“細節決定故障處理時間的長短,早一點發現潛藏着隱患的‘細節’,意味着潛艇和戰友們的安全係數就提高一點。”黃井磊提起了一次難忘的排查故障經歷。
那天,潛艇上某裝備突發故障。一時間,刺耳的尖嘯聲響起。黃井磊衝了上去,在設備間反覆排查,最終找到了故障點。“如果當時故障解決時間延長,後果不堪設想。”回憶當時的情景,黃井磊至今感到後怕。
沿着“巡線之路”繼續向前走,黃井磊用扳手依次檢查眼前的儀器閥門是否鬆動。如果說捕捉裝備聲音的細微變化是一名潛艇電工技師的特殊技能,那麼“擰閥門”的動作就是刻在他們身體裏的“肌肉記憶”。
扳手觸碰到閥門的瞬間,黃井磊記憶的閘門隨之打開——
一次任務,某艙室設備突發進水險情,水流呈噴射狀灌入艇內。黃井磊和戰友們每人一手一個扳手,左右同時操作,一口氣擰緊40多個螺絲,磨破了手指也渾然不知,迅速恢復了潛艇戰技狀態。黃井磊說:“當時,腦子裏顧不上想太多,所有的處置動作都是下意識的‘肌肉記憶’。”
對此,電工技師沈陶金也有深刻感受。剛上艇時,他曾對老班長們的“肌肉記憶”瞠目結舌:一次給車訓練,老班長數都沒數,大手一掄,舵輪停下的位置,剛好達到訓練規定的圈數。
事實上,這種“肌肉記憶”,建立在嚴格紮實的訓練基礎上。
潛艇兵的篩選,從一開始就很嚴格。黃井磊清楚記得,入伍前徵兵體檢他做了3次。體檢時,醫生專門檢查他的牙齒,牙齒咬合必須嚴絲合縫,否則不合格。最終,在黃井磊老家只有3人通過潛艇兵徵兵體檢。
入伍後,黃井磊要學習十幾門理論課程。鋪開一張A3大的白紙,他能熟練默畫不同裝備的原理圖,這才具備上艇資格。
然而,這僅僅是具備“資格”。
到了艇上,年輕的潛艇兵會跟着老班長進行五花八門的操作訓練。沈陶金記得,他們經常會蒙上眼睛進行“摸螺絲”訓練。桌子上,螺絲和螺母的順序被打亂,他們必須用手仔細觸摸不同螺絲和螺母的紋路,找出一一對應的螺絲和螺母。
剛上艇的新兵們還會被要求畫“故障分析樹狀圖”。一個裝備就是一棵樹,從樹幹向外生長的不同樹枝上,寫着不同故障;這根樹枝再向外蔓延出新的不同分枝,每個分枝上又寫着一條條故障原因……通常一臺裝備的故障分析,沈陶金能寫好幾頁A4紙。
還有一些難度極大的“生理”與“心理”疊加訓練。
“魚雷發射管脫險”課目,訓練的是當潛艇失事時,潛艇兵的自救能力。注水、加壓……4名潛艇兵穿戴脫險裝具,疊羅漢般擠在狹窄的管道里,在逼仄和黑暗中感受水位一點點上漲,直到淹沒自己的身體。在訓練過程中,他們必須時刻調整自己的身體,使身體適應不同水深的壓強。剛開始訓練時潛艇兵沒有經驗,壓強往往會使他們的耳朵轟鳴、眼睛充血。
在訓練中,老班長們會反覆強調基礎操作,“眼高手低”是實際操作中最忌諱的事,如果有哪名新兵基礎操作不到位,會立刻被班長毫不客氣地指出。
成長之路上,一定少不了艱難險阻。然而,當經過重重磨礪,必然會在路的盡頭看到繁花盛放:日復一日近乎嚴苛的訓練,內化爲他們身上的“肌肉記憶”,並轉化爲強大的戰鬥力。
在人民海軍潛艇史上,被大家熟知的“奇蹟”發生在2014年。
那一年,海軍372潛艇在執行戰備遠航任務時,突遭“水下斷崖”,潛艇瞬間下沉,急速“掉深”。迅猛的海水噴湧進艙室,危急關頭,全艇官兵在3分鐘內,執行了30多個口令,憑藉“肌肉記憶”做出500多個動作,關閉近百個閥門,用180秒化險爲夷,完成自救,創造了潛艇史上的奇蹟。
再看黃井磊和戰友們,經過一路磨礪,他們也似乎具備了和潛艇一樣“精密”的特質,不管遇到何種緊急情況,總能條件反射般迅速完成最優處理動作。
這份“精密”,是潛艇賦予他們的特質,也是他們走過荊棘叢生的成長之路後,應該獲得的回饋。
走好已經選擇的路,別老想着選一條好走的路
“巡線之路”繼續向前,黃井磊安靜地跨過水密門,從一個艙室進入另一個艙室。
在潛艇有限的空間裏,潛艇兵習慣了保持這樣的“安靜”:他們很少快跑,艙內低矮的艙頂與枝枝杈杈、硬邦邦的機械容易磕碰,一旦磕到了留下傷口,潛艇中沒有陽光,空氣不流通,傷口不容易癒合;他們也很少劇烈運動,“劇烈運動會出汗,在艇內水資源有限,沒辦法洗衣服”……
文藝輕騎隊的一名演員對潛艇兵的“安靜”印象深刻。他記得,那次來艇員隊演出,他和戰友們在臺上又唱又跳,使出渾身解數表演節目。可無論他們怎麼“賣力氣”,臺下的官兵們表情始終很平靜。演出結束,這名演員有些失望,以爲是節目演得不好。仔細詢問後才知道,大家很喜歡他的表演。“我們已經習慣安靜了,就算很開心也不會有強烈的表現。”一名潛艇兵說。
似乎,就連愛好也是安靜的。
和往常一樣,巡線路過艇上餐廳時,黃井磊看見幾名休更的潛艇兵在餐廳裏的“模擬太陽”下靜坐。
“模擬太陽”是艇上的一盞大功率功能燈。這盞燈能模擬太陽光的各種波長,緩解官兵的疲勞和壓力,關鍵時刻也能用作手術時的“無影燈”。
休息時,每當燈光亮起,“模擬太陽”下會圍坐一羣潛艇兵,沈陶金就是其中之一。“閉上眼,靜靜感受暖洋洋的光落在臉上的感覺很舒服。”他說。
沈陶金還會在每次遠航前帶上一盆綠蘿。每天,他都會細心擦拭綠蘿的葉子,讓葉子看起來更亮。
更重要的是,這抹在水下珍貴的綠色,讓沈陶金能在這個分不清白天還是黑夜的密閉空間裏,透過綠蘿每一天的生長,真實感知生命與時間的變化:如果綠蘿的葉子開始變多變密,意味着他們已經出海1個多月了;等到它的葉子可以垂到地面,意味着時間又過去了1個月……
沈陶金能深刻地感受到,在這條深海之路上,戰友們對家人的牽掛與思念就像綠蘿的葉子一樣,不停地蔓延生長。
一名叫梁偉健的潛艇兵,遠航時每天都會拿起筆給女朋友寫信。這個看似有些不符合信息時代潮流的方式,讓人有一種特別的感動。
還有許多潛艇兵用“航跡瓶”寄託思念。不同地點、不同深度、不同顏色的海水,被他們裝進一個個不同的玻璃“航跡瓶”裏,收集到一起。
“如果時間倒流,你沒來當潛艇兵,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站在人生的岔路口讓你重新選擇一次,還會這樣選擇嗎?”記者問。
前一個問題的回答五花八門。電工操縱長雷磊磊說,如果沒有來這裏,他現在可能在老家的企業工作,工作日穩定地“三點一線”;電工技師曲文超說,他可能會在老家的海邊開一家燒烤店,跟朋友們過自由自在的日子……
然而,他們對於後一個問題的回答堅定地一致:“我會。”
“走好已經選擇的路,別老想着選一條好走的路。”沈陶金覺得,儘管選擇的這條路並不安逸,但那些難忘甚至刻骨銘心的經歷豐盈了自己的內心,讓他對生命與價值有了更多思考,增加了人生之路的厚度。
黃井磊喜歡讀《海底兩萬裏》。他對書中的一句話記憶深刻:“耐心和持久勝過激烈和狂熱,不管環境變換到何種地步,只有初衷與希望永不改變的人,才能最終克服困難,達到目的。”
感受路,成爲路,延伸到更遠更深的地方
這些年,一批新裝備列裝潛艇部隊。黃井磊和戰友們經歷了潛艇部隊的跨越式發展,迎來了更多的機遇和挑戰。
聲吶技師臺學超幸運地參加了某型潛艇極限深潛試驗。這一天,無論對臺學超還是人民海軍潛艇史來說,都是向前跨越的重要一步。
極限深潛試驗是一次極其危險的任務,一着不慎,艇毀人亡。
潛艇一點點下潛,臺學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當聽到任務成功的消息宣佈時,臺學超和戰友們激動地相互擁抱,熱淚盈眶。
後來,參與此次任務的人一起合影,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如今,這張照片就展陳在基地軍史館裏。
從那次經歷以後,臺學超用“與艇共榮與艇共進”8個字勉勵自己,“潛艇兵和潛艇是一體的,未來要更加精進業務,讓潛艇走向更遠更深的海域。”
或許只有經歷過“漫長”的人,才能深刻感受此刻“前進”的步伐有多大。
25年前,電工操縱長何京德畢業後來到該基地。“對比以前,新艇裝備性能更優異更先進,生活條件也得到了明顯改善。”提起這些欣喜的變化,何京德感受到了潛艇部隊發展變化的“大步向前”。
如果時間的維度再拉長,我們能從我國某型潛艇首任航海長範喜德老人的經歷中,感受到如今潛艇部隊“大步向前”的背後意味着什麼。
50多年前,範喜德和戰友們駕駛某型潛艇進行百餘次試驗,一次次敢爲人先,挺進深海。潛艇下潛的過程中,他能清楚聽到鋼材形變的聲音。“當時,一切都是未知數,今天出海了,回不回得來,誰也不知道。”在一部紀錄片中,84歲的範喜德說。
直到現在,每到過年,範喜德老人還會爲潛艇兵們錄製祝福視頻。
一代代潛艇兵接力向前,讓潛艇的航跡走向更遠更深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成了鋪路石,託舉新一代潛艇兵走向遠方。
新時代潛艇兵眺望着這條路,感受路,成爲路,延伸到更遠更深的地方。
慶祝人民海軍成立70週年海上閱兵活動,黃井磊有幸參與,他和戰友們一起光榮接受習主席檢閱。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黃井磊至今記憶猶新。
又一次遠航歸來,傍晚,金色的霞光灑向大海,潛艇漸漸浮出水面。站在艦橋上,海風迎面撲向黃井磊的臉。
看向遠方,黃井磊想起了艇員隊營房牆壁上的《水下先鋒賦》:“奮楫篤行,披堅執銳,武備文攻,克敵制強震雷霆。傳薪火,立新時代潮頭,永當先鋒。”
(攝影:劉再耀、宋潤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