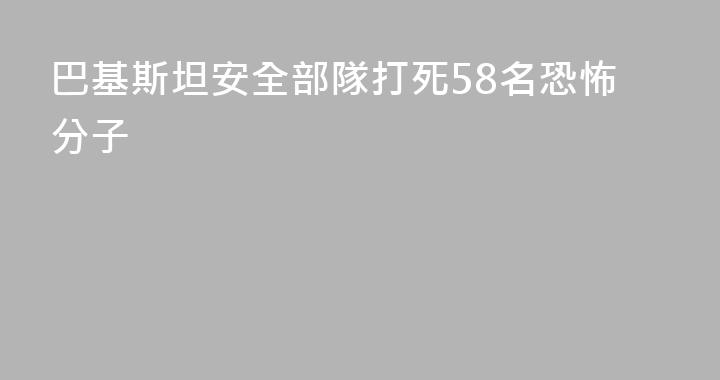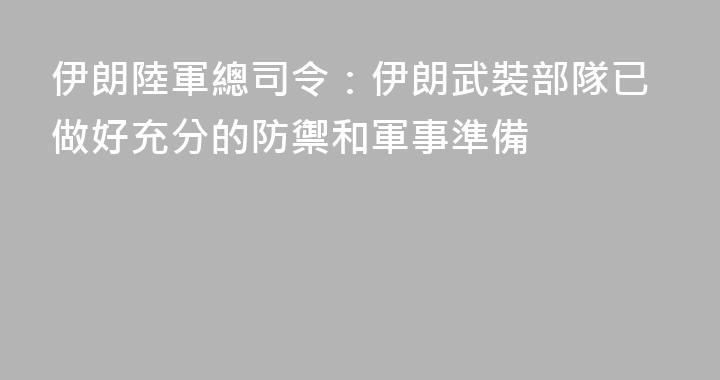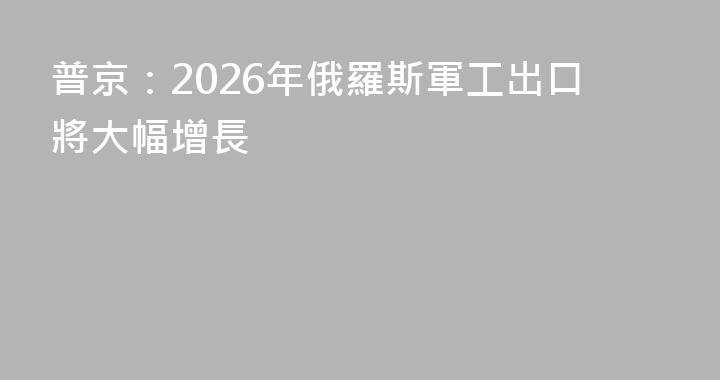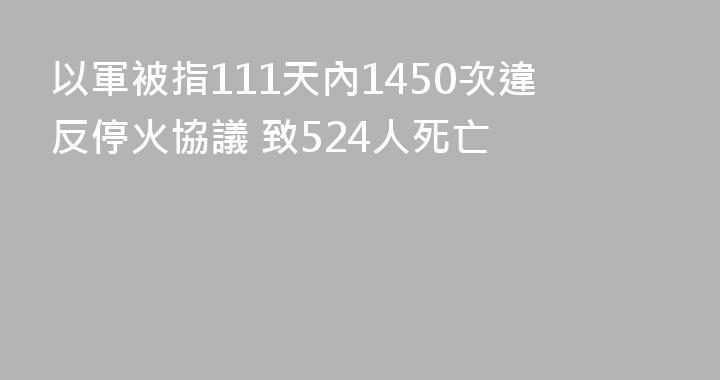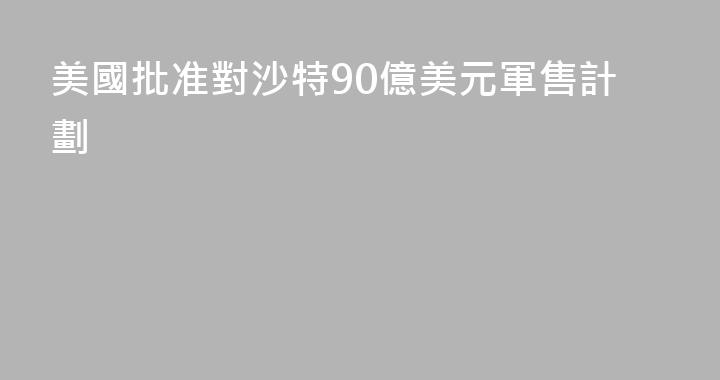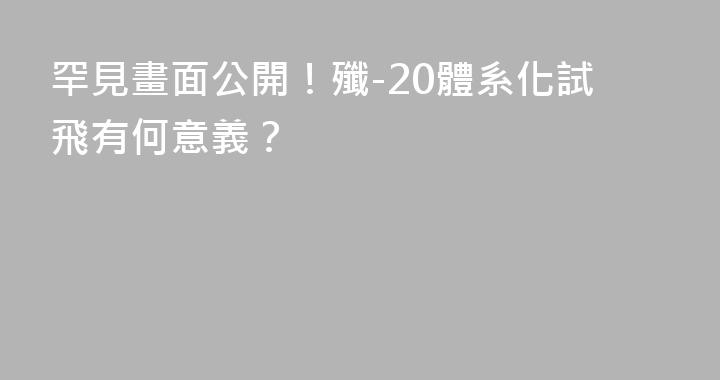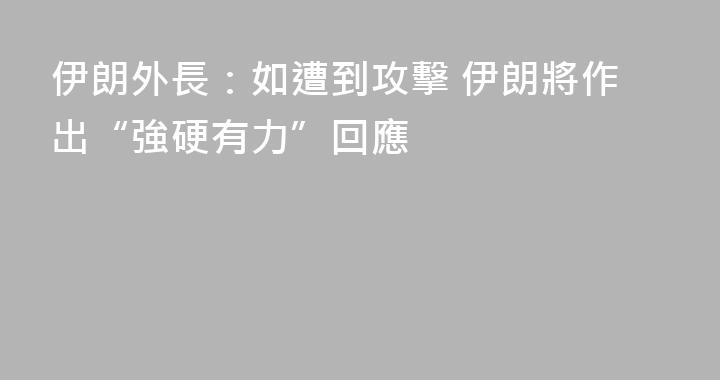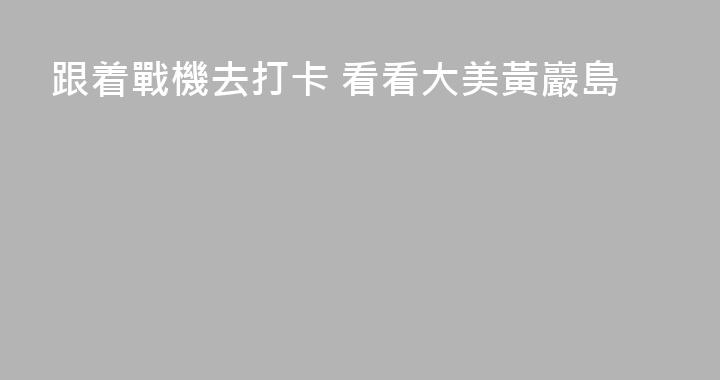走近戰場“破壁者”
■解放軍報特約通訊員 劉 凡
到中部戰區陸軍某旅某爆破連採訪時,恰逢該連組織實爆訓練。訓練前,筆者跟隨三級軍士長穆恆貴對場地中的鐵絲網進行巡檢、加固。
在巡檢過程中,穆恆貴時不時從工具袋裏掏出一些草籽撒在抵近鐵絲網的路上。這些草籽有些像蒼耳,周身帶刺,但略大一些。
“這些撒草籽的地方,都是需要匍匐前進的地方。”穆恆貴解釋道。
筆者趴下身子,在撒有草籽的區域匍匐,隔着作訓服接觸到草籽的感覺就像走路時鞋裏進了沙子,有些刺痛,不至於受傷,卻能對執行前線破障任務的爆破兵造成一定的干擾。
“干擾越多,越能檢驗本領扎不紮實。”穆恆貴隨即講起自己的一段經歷。
多年前的一次戰術訓練,穆恆貴所在的爆破小組執行爆破任務。在草叢中匍匐時,穆恆貴爲了躲避這種草籽,雙肘撐地往一側挪了挪,不經意間將捧在手中的炸彈往懷裏摟了一下。這一幕,恰好被跟在他身後的班長看了個真切。
“有敵情時,拉火管是提前裝好的,你爲了躲草籽把炸彈往懷裏摟,身上這麼多裝具,掛到拉火管的引線怎麼辦?!”訓練結束,班長嚴厲批評了穆恆貴。
該連的專業訓練場,大都是平坦的黃土地,並不能對匍匐造成太多阻礙,有的地方,軟塌塌的浮土甚至像一層軟墊。雖然砂石不多,但這種長有帶刺草籽的植物卻有不少,官兵們便將草籽收集起來,訓練時撒在匍匐的必經之路上,爲自己製造些“阻礙”。
之所以如此加壓,是因爲爆破兵面對的任務非同尋常,他們總想着如何“刁難”自己,如何讓對手捉摸不透。
二級上士郭江偉,爲探索新領域遂行任務方法,主動請纓從零開始學習潛水;排長高迎仍,將對抗思路融入專業訓練,常態化組織對抗,改進戰術戰法……
採訪中,筆者發現,穆恆貴很喜歡用一個詞——“披着”。
“披着夜色。”
“披着震天的聲響。”
……
“這應該是獨屬於爆破兵的一個習慣,有的老兵說話時,常常冒出‘披着’這個詞。”穆恆貴解釋道,“要說緣由,是因爲在戰場上,身處接敵一線的爆破兵往往要衝向敵人防守最堅固的位置,雙方火力都非常猛,子彈像毯子一樣,覆蓋在頭頂,就像‘披’在身上一樣。”
訓練結束,筆者再次走上爆破兵的訓練場,入目處,巨石破碎、硝煙瀰漫、碉堡崩塌、炸坑遍地。那一刻,勇氣忽然變得具象,筆者明白了什麼是爆破兵——一羣擊穿敵人銅牆鐵壁的“破壁者”,用轟鳴與震盪爲戰友開路的先鋒,用炸藥與方程式爲勝利批註的勇士。
正如該連營房牆壁上,那紅底金字的《爆破手之歌》中唱的那樣:“我們是英雄的爆破手,戰鬥在最前線。冒着那槍林彈雨,把進攻的通路開闢,爲戰友勝利的前進,我願把青春貢獻……”

中部戰區陸軍某旅某爆破連開展布設爆炸裝置訓練。郭輝 攝
爆破兵:在轟鳴中完成蛻變
■解放軍報特約通訊員 劉 凡
哪有天生的勇敢,只有鍛煉出的無畏
前方,雷場、碉堡虎視眈眈;身後,戰友、戰車嚴陣以待。
身處接敵一線的爆破兵最需要什麼,中部戰區陸軍某旅某爆破連下士林鵬年回答了一個詞:勇敢。
在這裏,下連1年左右,每一名爆破兵都會經歷自己第一次模擬實戰。那一年,林鵬年也走上演訓場,第一次在“炮火”中向“敵”碉堡發起衝鋒——
“能不能順利到達任務點?能不能配合好戰友?”躍進前,在土坎後隱蔽的林鵬年有些緊張,默唸着攜炸藥戰術運動的要領和行動預案中的炸藥佈設原則。
“大家跟我沿着地上的炸坑,蛇形前進,快速躍進!”在三級軍士長穆恆貴的指令聲中,林鵬年所在的小組衝出土坎、向“敵”碉堡奔去。
演訓場頓時炸聲四起,塵土飛揚。
“嘭!”出發不過10秒,一個炸點在距林鵬年5米左右的位置炸響,強烈的震感瞬間清空了他的大腦。
“不能停,絕對不能停!”壓住心中的錯愕與慌亂,林鵬年繼續躍進,觀察戰友的位置,把控好和戰友間的距離,最終與戰友同步完成起爆,順利完成任務。
戰場爆破,並非只是佈設炸彈這麼簡單,潛水、攀巖……他們恨不得能夠上天入地,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因爲戰場環境複雜,對爆破兵而言,多一項本領,就可能多一條破敵之路。
1935年,紅4團受命奪取臘子口,面對天險和國民黨軍隊的嚴密防守,苗族小戰士“雲貴川”帶上戰友們用綁腿布帶連結起來的長繩,用一根帶鐵鉤的竹竿,勾住峭壁的縫隙,一步步攀上絕壁。隨後,他又讓戰友們順着長繩一個個攀了上去。入夜後,我軍如神兵天降,自上而下向沒有頂蓋的敵軍碉堡扔下手榴彈……
對如今的爆破兵來說,攀巖是必訓課目。然而,對於面對400米障礙中2米深坑都有些發怵的戰士孫宇涵來說,這是一座大山。
兩年前,孫宇涵應徵入伍,成爲二級上士鄭海清班裏的一名新兵。他工作認真,訓練也十分刻苦,鄭海清對他的表現很是滿意。唯有一點讓鄭海清着實頭疼——孫宇涵恐高。
訓練時,面對攀巖訓練的牆壁,孫宇涵說什麼也不上去。看着班長着急又無奈的表情,孫宇涵更加緊張了。
一個週末,鄭海清在心理行爲訓練場看見孫宇涵站在一個高臺前,慢慢扶着梯子爬上去,緊握扶手站一會兒,又慢慢順梯爬下來,一直反覆。那一刻,鄭海清下定決心:“一定要幫他克服恐懼。”
自那之後,鄭海清丟掉了催促與急躁,開始陪着孫宇涵上高臺、下深坑……藉助輔助設施幫助他克服恐懼心理,直至他能獨立站在巖壁面前。
現如今,孫宇涵已經能在攀巖牆上自如上下。
哪有天生的勇敢,只有鍛煉出的無畏。成長路上,爆破兵在一聲聲轟鳴中完成蛻變,成爲一名戰勝恐懼的勇士。
往勇氣中注入“智慧的火藥”,會催生更強大的爆破當量
“真正的勇者須以智謀傍身。”穆恆貴悟出這個道理,要從一次破障行動說起。
2022年,該連參加上級組織的演訓,穆恆貴帶領一個破障小組執行破障任務。
破障小組順利突破“敵軍”佈設的反坦克壕和地雷場後,在由碉堡和壕溝構成的最後一道障礙前,遭遇了密集的炮火打擊,他們不得不停下前進的步伐。
“班長,炮火太密集,我跑得快,讓我上吧”“班長,我去吧,我有經驗”……面對戰士們爭先恐後的請戰,穆恆貴卻很冷靜:“不怕犧牲是勇敢,但無謂的犧牲沒有什麼意義!”
根據爆炸頻次,穆恆貴現場推算出“敵”炮火打擊規律,並利用短暫的炮火間隙,觀察並記錄了地面已引爆的模擬炸點位置。藉助這些點位,穆恆貴規劃出了一條通向第三道障礙的路徑。
“一路縱隊,跟我來!”迅速抵近的爆破小組讓防守方措手不及。
“準備完畢,起爆——”穆恆貴一聲令下,霎時間,障礙一線如大壩決堤般被炸得粉碎。
“一個小組打出了乘風破浪的氣勢!”演訓結束後,指揮員讚歎道。
往勇氣中注入“智慧的火藥”,會催生更強大的爆破當量。
2023年的一次訓練,鄭海清和二級上士廖志文受命破壞“敵軍”的一處防禦陣地。抵達任務地域,他們發現防禦陣地在一處陡坡之上,居高臨下,易守難攻,陡坡上植被稀疏,僅有幾處土包可作爲掩體。顯然,這是一塊“硬骨頭”。
鄭海清和廖志文權衡再三,決定各帶一個小組從兩翼對“敵”陣地發起攻擊。可連續幾番試探未果,還引起了“敵人”的警覺,一時間,破障行動陷入僵局。
鄭海清和廖志文對整個任務地域地形展開偵察,尋找可以滲透的縫隙。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在陡坡一側發現了一處陣地觀察死角。雖然受限於地形,不能在此實施爆破,但可以由此而上,抵近後佯攻吸引“敵軍”注意,再由正面實施爆破。鄭海清主動攬下佯攻任務,帶領一個小組從觀察死角抵近“敵軍”。果然,“敵軍”發現鄭海清小組時瞬間亂了陣腳,誤將該小組當作進攻主力,調轉火力予以反擊。廖志文抓住機會,帶領破障小組衝到“敵”陣前,成功實施爆破。
從戰術到謀略,這羣“令敵破防”的爆破兵,也在苦苦追尋思維的“爆點”——
近年來,多型無人裝備陸續列裝,作爲技師的穆恆貴帶着幾名無人裝備操作骨幹,探索通過有人無人協同改進戰術戰法。
傳統爆破行動中,都是由人將爆炸裝置運送到指定位置,再進行引爆破障。二級上士楊小鵬開始思考如何用無人裝備替代人力進行爆炸裝置的轉移。
一次實爆訓練中,楊小鵬提出,夾取型排爆機器人雖然是針對排爆設計的,但本質上就是一個夾持爆炸物進行位移的工具,可以反向運用夾取型排爆機器人,把爆炸裝置運送至任務點位進行設爆。經過試驗驗證,在合理地形中,此法可行,利用無人裝備設爆不僅大幅降低了人員傷亡風險,還提高了戰場條件下運送炸藥的速度與成功率。
爆破行動中,有時需要跨晝夜執行任務,夜間警戒非常消耗精力和體力,爆破行動的編組人數本就較少,經過一整晚的警戒,勢必影響第二天的行動。
爲了緩解夜間警戒壓力,一級上士湯清洲利用少量簡易材料,自制了一種可快速設置的低藥量警示裝置。雖然沒有什麼殺傷力,但可以發出巨大的聲響並升騰起黑煙,佈設在宿營地周邊,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警示效果。
一次對抗訓練,一股藍軍本想趁着夜色對該連進行襲擾,卻誤觸了湯清洲設置在宿營區外圍的警示裝置,巨大的聲響震懾住了藍軍。
那一回,藍軍指揮所裏流傳起了一句話:“爆破兵的宿營地太危險了,到處都是炸藥!”
有勇者不可擋,懷智者無難事。奮戰路上,爆破兵用勇與謀交織出獨屬於他們的青春答卷。
角色的不斷切換,讓他們對攻與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咕嚕,咕嚕……野外湖泊,一座廢棄大橋下,二級上士郭江偉扶着橋墩下潛,感受着逐漸增大的水壓和降低的水溫,緩慢調整身體姿態,找尋佈設模擬爆炸裝置的最佳位置。
令他沒想到的是,他預想的最佳安放區域已被預先佈置了不少懸浮的障礙物,經過幾番處理也沒能清理出一個合適的點位,氧氣耗盡,郭江偉鎩羽而歸。
“今天的障礙設置得真好,防得密不透風!”剛上岸,潛水服也沒脫,郭江偉就把剛纔訓練過程中遇到的障礙佈設方式記錄下來。
在該連,大傢伙會輪流分享自己近期的爆破經驗。此次訓練前,擔任防禦方的二級上士亢延鵬根據郭江偉分享過的水下目標爆破經驗,反向鑽研防禦手段,利用廢舊的鐵絲網、泡沫等材料,將可能設置水下炸藥的位置給遮了起來。水下處理障礙遠不如地面方便,在沒有稱手工具的情況下,幾根長條狀鐵絲網纏繞着雜物,便會給進攻造成很大阻礙。自此之後,爆破小組進行水下爆破時,都會帶把大剪刀。
善於破障,也要善於製造障礙。該連經常根據官兵專業、能力、經驗等條件,將大家分成對抗訓練小組,常態化互設難題,提高爆破能力的同時,防爆破能力也不斷迭代。最熟悉爆炸物的他們,並不是只知道如何“搞破壞”,到了戰場上,他們既可以是撕裂敵方堡壘的勇士,也可以是鞏固己方防禦的衛士。
訓練中,防禦方通過改造現地環境、重設防禦工事結構等方式阻止進攻方設置爆炸裝置;進攻方則通過改進裝置結構、創新手段佈設、革新戰術戰法等想方設法克服阻礙,實施爆破。
湯清洲說,角色的不斷切換,讓他們對攻與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近些年,大家逐漸喜歡上了這種訓練中的彼此“刁難”。
一次對抗訓練,擔任防守方的二級上士郭輝在己方防禦設施的牆面上噴了一層薄薄的食用油,使得對手的爆炸裝置無法粘貼固定。針對新的防禦措施,他們的解決方法也很直接——在隨行裝具裏多裝了一包溼巾。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油都容易清潔乾淨。官兵們陸續嘗試了機油、潤滑油等不同油料,發現靠溼巾擦拭這種簡單清潔效果並不好,又不可能每次任務都隨身攜帶專業的清潔工具。一次訓練中,郭輝偶然看見,塑料袋會粘在有油的表面。郭輝由此聯想到了會隨身攜帶的水袋:“我們用的水袋錶面就是塑料的,將水倒掉,就是個比較厚的塑料袋。”經過試驗,將空水袋按在覆有油脂的防禦工事表面,再沿着縫隙滴上幾滴水,空水袋便牢牢吸附在了工事上,再將炸彈粘貼在空水袋上,便實現了固定。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真正的博弈早在上戰場之前便已展開。
“敵人也在快速進步!”在他們心中有一種“本領恐慌”,因此總想着進步得再快些、發現的漏洞再多些。
在該連爆破專業研修室裏,掛着一張爆破藥量參考表,這是衆多技術骨幹根據歷年訓練經驗總結的。執行任務時,根據先期偵察的情報,他們可以參考這張表確定攜帶量,在保證備有足夠餘量的情況下減少負重。
說起這張表的來歷,一級上士李琨講起一段經歷:那年,他帶隊對特定目標實施精準爆破,沒有經驗可供參考,只能憑感覺確定裝藥量。第一次爆破用量過少,門沒有炸開,第二次用量又太多,將整面牆炸塌了。
“在之前的爆破訓練中,坦克壕的寬度、門窗的材料、牆壁的厚度等,都相對固定,導致這次遇到新材料摸不準炸藥用量。”李琨說。
痛定思痛,從那次訓練開始,該連將對不同材質、不同結構目標成功爆破的炸藥用量記錄下來,總結出參考值區間,形成了這張爆破藥量參考表。目前,這張表仍在不斷更新。與此同時,湯清洲還根據對抗訓練中遭遇的實際困難,鑽研不同類型建築、障礙物的爆破規律,製作出對應的輔助裝置和簡易爆炸裝置……
這便是爆破兵,他們有着兩種氣質——既有陣前衝鋒時英勇無畏的豁達豪邁,又有設計防禦時周全謹慎的沉穩老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