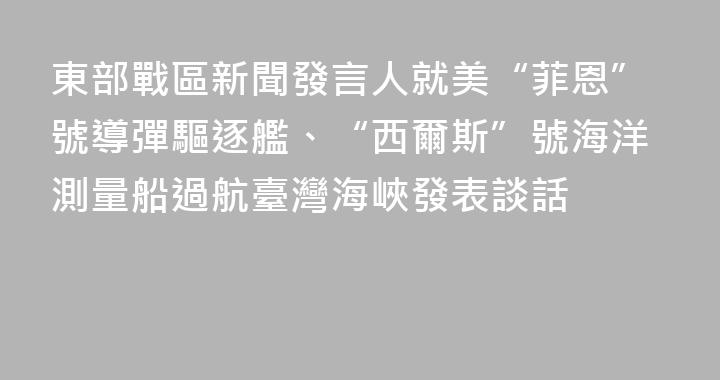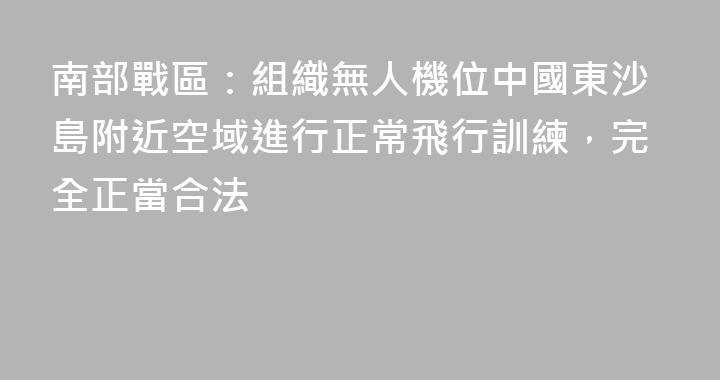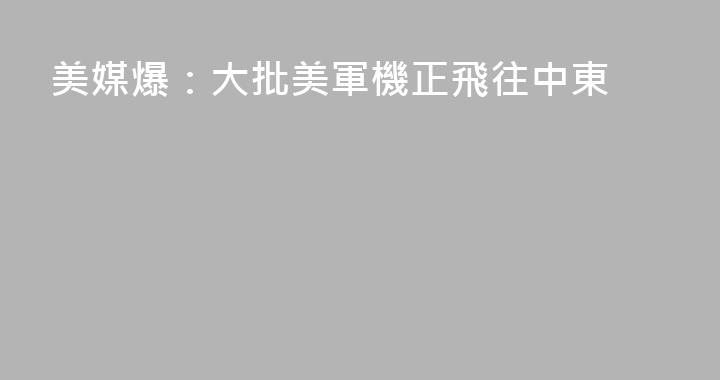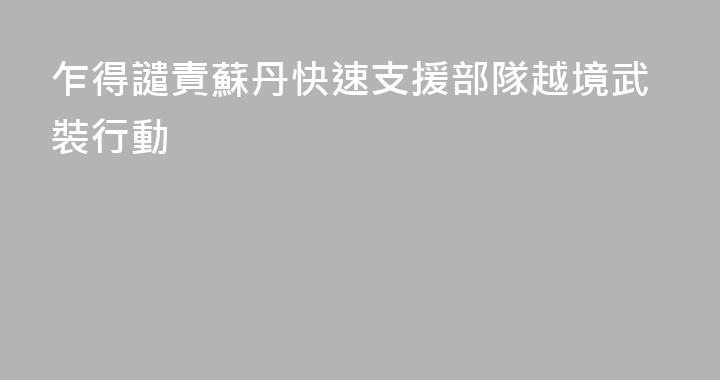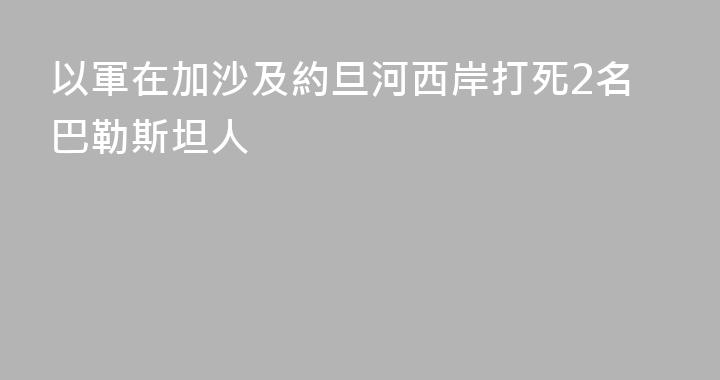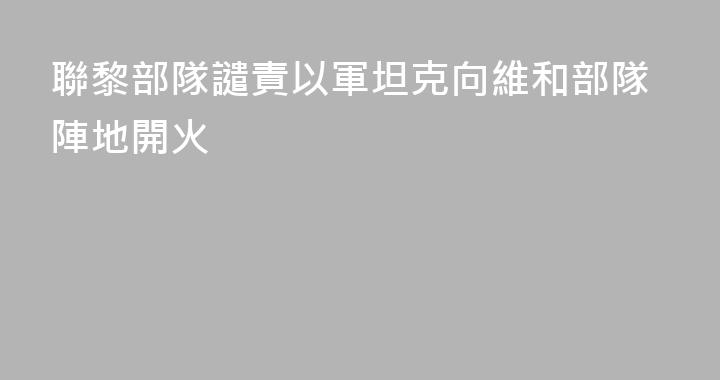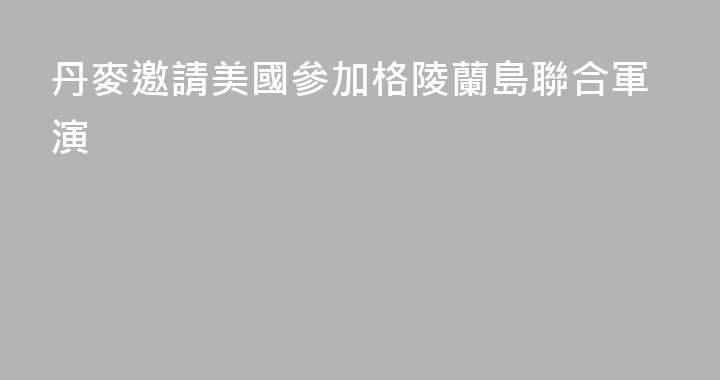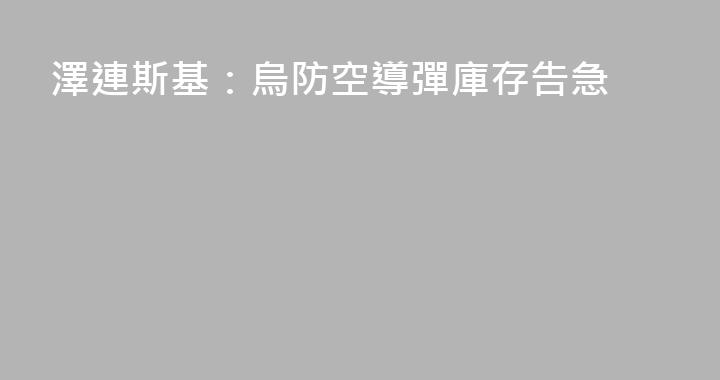【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林雪原 環球時報記者 丁雅梔 徐嘉彤 鄭璇】編者的話:本系列上期文章回顧了日本確立“專守防衛”原則的歷史脈絡,闡述了這一原則是日本對國際和平秩序的政治承諾,而日本不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是國際社會給予日本信任的基礎。然而,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對“專守防衛”原則進行了系統性破壞,其中最具代表性、政治與法律意義最重大的舉措就是安倍政府2015年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事實上,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日本右翼處心積慮、不斷蠶食“和平憲法”根基的長期圖謀。本期文章將繼續爲讀者講述,日本通過哪些招數一步步“自我鬆綁”,背離戰後對國際和平秩序的政治承諾。
提出“正常國家論”,擴大自衛隊規模和活動範圍
何爲“集體自衛權”?根據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在遭受武裝攻擊的情況下可以行使。其中,集體自衛權是指,當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比如盟友)遭到武力攻擊時,即使本國沒有被直接攻擊,也有權以武力介入、援助該國。
但是,由於日本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之一,日本戰後制定的新《日本國憲法》(也稱“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了“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爲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隨後日本還制定了“專守防衛”原則,事實上禁止了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僅保留個別自衛權。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是二戰後日本在“和平憲法”原則指導下,根據國內外形勢做出的重大政策選擇,也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構成其“專守防衛”基本國策的一個具體要素。
日本對這一政策選擇的悔意,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後外顯。1991年2月底,以美國爲首的34國聯軍對伊拉克發動的海灣戰爭在多國部隊宣佈停火後告一段落。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1991年3月的報道,日本政府在海灣戰爭中向聯軍提供了近130億美元,但由於拒絕了向阿拉伯半島派兵,日本被貼上“支票外交”等標籤。戰爭結束後,科威特政府在美國報紙上刊登整版致謝廣告,卻在致謝國家清單中遺落了日本。“我們所做的事情沒有得到適當的重視,這讓我咬牙切齒。”報道援引了時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的表態。
在此背景下,執政黨自民黨極力倡導所謂“國際貢獻”“維和行動”。1992年6月,自民黨推出的《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簡稱PKO法案)在日本在野黨的反對聲中通過,使自衛隊邁出了“合法”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1993年,日本政治人物小澤一郎發表了《日本改造計劃》,主張日本應成爲“正常國家”,強調日本要使自身政治安全責任匹配經濟大國地位。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劉江永對《環球時報》記者強調,日本的“國際貢獻論”其實是包裝其擴軍野心的幌子。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王瑞告訴記者,自從PKO法案通過,日本便開始不斷突破憲法限制,擴大自衛隊的規模、活動範圍與權限。從規模上來看,日本近年來多次發佈的《防衛計劃大綱》(2010年、2013年、2018年)以及2022年新“安保三文件”不斷提升陸海空自衛隊的規模上限。例如,海上自衛隊的潛艇數量從16艘提升到22艘,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從約260架提升到約320架。從活動範圍與權限來看,日本2001年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以出兵印度洋;2003年通過《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派遣自衛隊至伊拉克進行所謂“人道復興支援活動”;同年,日本還制定了“有事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給予自衛隊戰時特殊法權。
“9·11”事件後,配合美國反恐
劉江永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集體自衛權禁區開始鬆動,主要原因是日本和平力量逐漸衰退、右翼鷹派勢力崛起,後者主張擴軍、突破憲法束縛,甚至要修改憲法,導致日本政治右傾化加速,集體自衛權議題被炒作升溫。與此同時,美國希望日本分擔東亞軍事分工,這使得日美形成利益契合。日本企圖借用集體自衛權給自己在海外配合美軍作戰鬆綁尋找法理依據,從而使日本突破限制、實現重新武裝。
1997年,日美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明確將“日本週邊事態”納入合作範圍,日本隨後於1999年通過《周邊事態法》。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分析說,這一法案允許日本在本國周邊地區出現糾紛時,能爲開展所謂“維護和平與安全行動”的美軍提供“後方支援”,確立了可在日本主權範圍外的地區支援美軍的機制。
自2001年“9·11”恐襲事件發生後,美國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屢次要求日本“參與應對”,配合其全球反恐戰略。曾任日本駐美大使館防衛長的伊藤俊之對日本《朝日新聞》回憶說,“9·11”事件發生後不久,包括他在內的多位日本官員接到白宮和美軍官員的電話,詢問日本對於此次恐襲事件的應對計劃。日本外務省隨即開始籌備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緊急訪美行程,日本防衛廳也開始籌備相關法案。
2001年10月,日本國會通過有效期兩年的《反恐特別措施法》,授權海上自衛隊在印度洋向美軍艦艇執行補給等非戰鬥支援。此法突破了之前自衛隊只能在日本“周邊地區”支援美軍的限制,使其能在海外執行非戰鬥任務。《反恐特別措施法》通過後迅速實施,日本對美補給任務持續多年,日本國會於2003年、2005年和2006年3次延長該法。
“我希望日本以首相認爲履行承諾所必要的程度參與(伊拉克)重建。”2003年5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美時,美國時任總統布什在記者會上說。2003年7月,日本迅速通過《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使得日本自衛隊能被派遣至伊拉克進行所謂“人道復興支援活動”“安全確保支援活動”等,也爲日本後續海外軍事行動(如2009年的索馬里護航、吉布提基地支援等)“亮了綠燈”。
修改憲法解釋、出臺新安保法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是解禁集體自衛權的主要推動者。早在2007年安倍晉三第一任期內,他就成立了“關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懇談會”(簡稱安保法制懇談會),旨在探討修改憲法解釋以允許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在2012年12月底開始第二次執政後,安倍晉三再次將修改憲法解釋提上日程。2013年2月,他正式重啓安保法制懇談會。
2014年1月,安倍晉三在日本第186屆例行國會開幕之際發表施政演說,明確表示“將參考‘安保法制懇談會’的報告,審議如何處理集體自衛權、集體安全等相關議題”。同年5月,安倍晉三在北約理事會會議上發表演講,表示將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來解禁集體自衛權,還妄稱中國的軍事動向“是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日本希望與擁有“共同基本價值觀”的北約推進合作。幾天後,安保法制懇談會提交了有關報告,報告核心結論是:在全球化和安保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僅靠個別自衛權無法充分保障日本的安全,建議修改憲法解釋,允許在“存在可能威脅日本生存的明確危險”等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
有了專家諮詢小組提供的理論基礎,安倍晉三便開始與聯合執政的公明黨進行談判,隨後通過內閣決議案的形式,繞過“修憲”這一爭議巨大的程序,通過修改憲法解釋,實質上給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綁。2014年7月,安倍內閣正式通過“關於爲保全國家存立、守護國民,完善安全保障法制”的決議,推翻了歷屆內閣關於集體自衛權違憲的憲法解釋,設定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條件”:日本存亡受威脅、無其他應對手段、行動限於必要最小限度。
如果說內閣決議是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方針,那麼安倍內閣隨後又批准了一系列法案來爲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提供支撐。2015年5月14日,日本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從政府層面批准了11部法律,統稱爲“新安保法案”。相關法律於2015年9月在日本國會以執政黨優勢強行通過,2016年3月29日正式實施,從實質上解禁了日本集體自衛權,架空了“和平憲法”第九條和“專守防衛”原則,引發了日本在野黨和衆多日本民衆的強烈反對。
圖謀將臺灣問題與集體自衛權捆綁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常思純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有4個戰略意圖:首先,擺脫戰後體制。日本企圖掙脫戰後“和平憲法”的束縛,通過行使集體自衛權,重新成爲擁有軍隊和交戰權的所謂“正常國家”;其次,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日本試圖打破“美主日從”的單向依附格局,於是迎合當時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爲美分擔地區安全責任,深化與美安全合作。再次,擴大政治安全影響力,謀求成爲“政治大國”。長期以來,日本一直認爲其政治和安全話語權未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日本希望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更主動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以實現成爲“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目標;最後,對中國形成威懾。安倍晉三在任時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無理指責中國“試圖改變國際現狀”,制衡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
劉江永對《環球時報》記者強調,在臺灣問題上,日本的介入意圖愈發明確。無論是最初“周邊事態”的模糊表述,還是安倍晉三煽動美國“應對臺灣問題”,以及高市早苗本次公開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都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將臺灣問題與集體自衛權捆綁。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地區不符合集體自衛權的適用前提,日本若要介入臺海,必須依託日美同盟,迫使美國一同進行軍事幹預——這恰恰反映出日本妄圖在臺灣問題上掌握主動性,甚至在“帶節奏”推動美國介入。
劉江永表示,從所謂的“參與民事維和”到向衝突地區派遣自衛隊提供“支援”,再到安倍晉三鼓吹的“積極和平主義”論調,日本右翼不斷試探海外用兵邊界,爲實現軍事鬆綁尋找藉口,這與戰後“和平憲法”精神及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和平期待背道而馳。
下期預告: “國際貢獻”“維和行動”等是日本最初試圖爲自衛隊鬆綁時所用的說辭,但日本右翼顯然不滿足於此——他們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把中國等國視爲“假想敵”,強推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企圖實現成爲“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戰略野心。近期,高市政府的一系列行爲都表明其企圖進一步擴軍備武,讓日本在“自我鬆綁”、倒行逆施的路上越走越遠。對此,國際輿論的擔憂正在增多,警戒的呼聲日益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