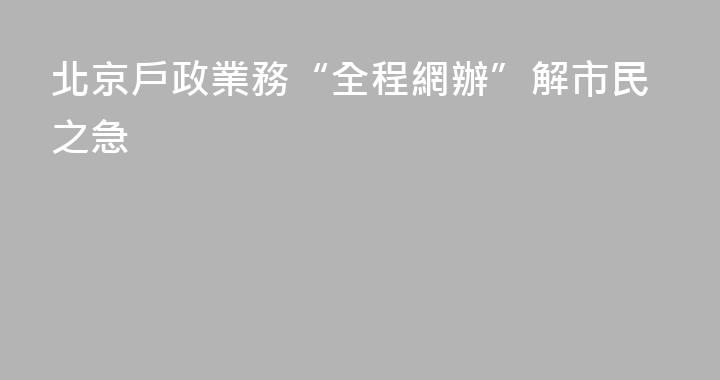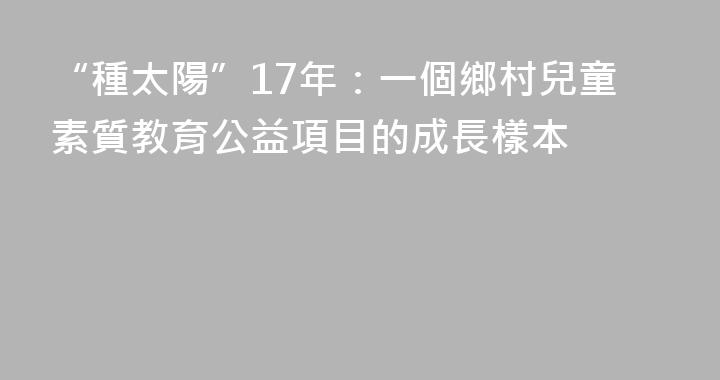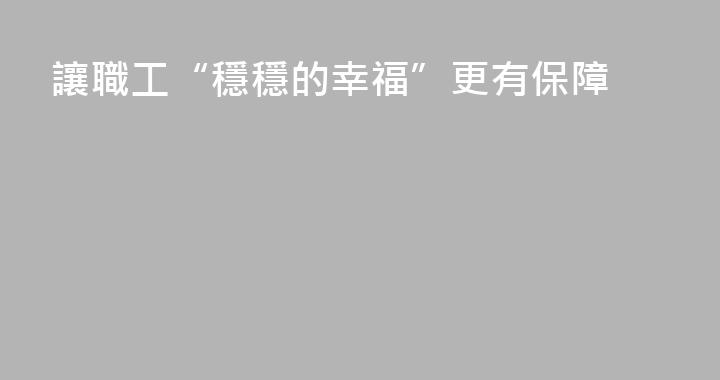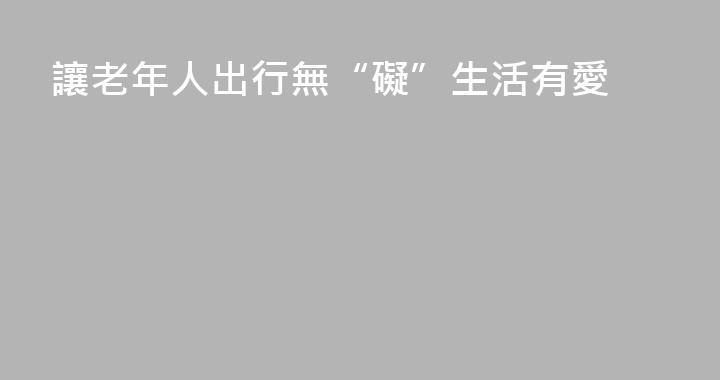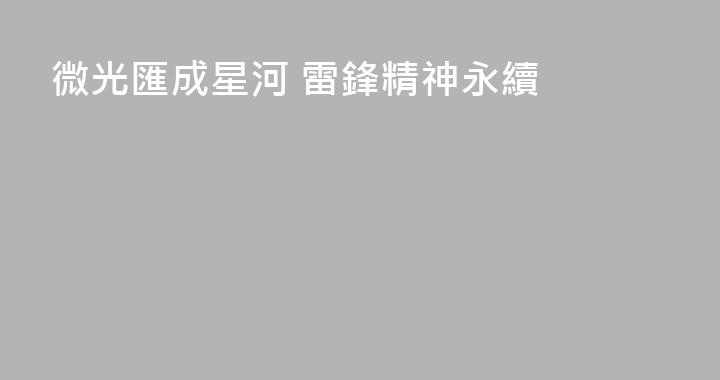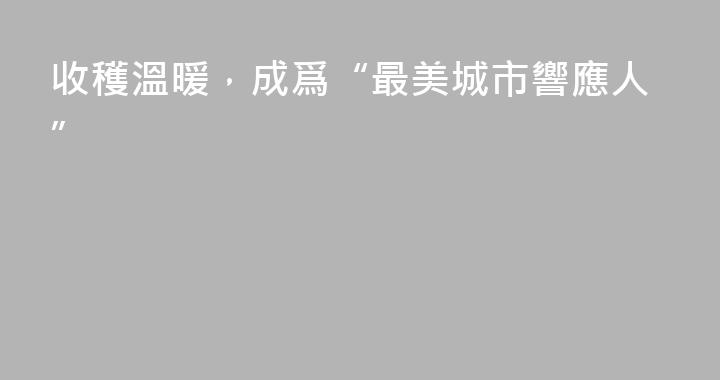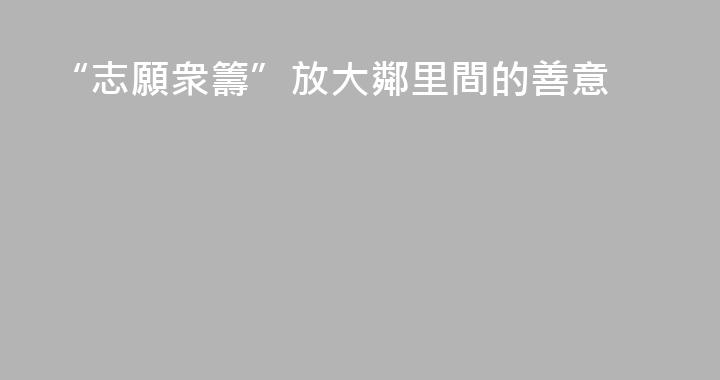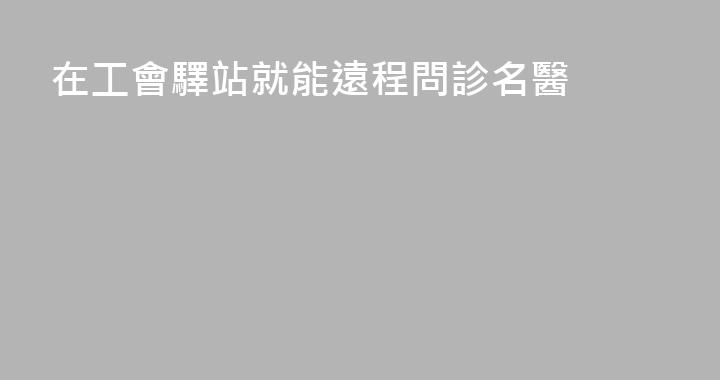【環球網報道 記者 文雯】鄭子寧以“語言學手術刀解剖文明DNA”,通過十個關鍵名稱的歷史演變,在最新著作《中國的十個名字》中,揭示中華文明的深層基因。在環球網專訪中,鄭子寧分享了書中顛覆性的研究案例,並闡釋了語言考古對歷史敘事的獨特價值。

環球網:您在書中通過“中國”等名稱追溯文明基因,能否分享一個在研究中發現的最具顛覆性的命名案例?它如何挑戰了我們對某個歷史時期權力結構或文化認同的既有認知?
鄭子寧:可能有一個比較有意思。洛陽在外語中的古稱被叫做Srg或者Sarag。那之前關於洛陽爲什麼叫Sarag?有主流的說法是認爲來自“rag”,對應的是上古漢語中“洛”的讀音。
但是,我通過綜合的比較研究發現,其實這個Sarag應該是跟中國在希臘語中的古稱Σῆρες(Seres),也就是絲國有關。
這麼看,Sarag表達的意思,應該是絲國都城的一個省稱。據此可見,在像羅馬之類的西方,把中國稱作絲國的時候,就已經認爲洛陽是中國的都城了。
環球網:《中國的十個名字》將語言視爲“文明的活化石”,能否以書中某一名稱爲例,解析其語音演變如何像地質層一樣疊合着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記憶?這種“語言考古”方法對傳統歷史敘事有何補充價值?
鄭子寧:其實很明顯的一個就是China這個名字。
我們知道China這個名字,它最早要麼是來自秦,要麼是來自晉,或者也有說法是來自滇。它最早的時候的,讀音可能是類似於“chin”這樣。
中古時期波斯人則是把中國稱作chin,現在我們熟知的China,能看出是在chin的後面加個一個a,這也能顯現出葡萄牙人在其間起到的影響作用。因爲葡萄牙語不太喜歡用輔音鼻音收尾,而是一定要在後面加個a,這樣的構成纔是葡萄牙語所認爲的比較妥當的國家名構成方式。由葡萄牙人加了a的China,再傳到像英語之類的語言體系中,就成爲了現在西方語言對China最主要的稱呼。
環球網:當“元宇宙”“AI”等新命名正在重塑人類認知時,您如何看待傳統命名體系在數字時代的存續價值?您認爲《中國的十個名字》能爲未來文明命名提供哪些啓示?
鄭子寧:關於傳統地名,我認爲這個和元宇宙或者AI關係並不是那麼大。因爲實際上地名是居民在長期使用中,會自己慢慢地形成一個名字,當然也可能有一些官方推動的因素存在。
我覺得新的地名的形成也未必需要AI的參與。現實中,我們說規劃的新區、路名什麼的,自然也會有屬於它的名字出現,似乎也並沒有太多需要AI參與的內容。
環球網:您曾說《中國的十個名字》是“用語言學手術刀解剖文明DNA”,能否說明這種研究的獨特性?在您看來,爲何名稱比文字更能承載文明的深層密碼?
鄭子寧:爲什麼我認爲名稱會比語言的很多其他成分更能承載文明密碼,主要是名稱它的傳承,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語言本身。名稱它是可以從一種語言介入另外一種語言的,所以哪怕是之前的那個語言早就消失,它仍然可以以名稱的形式存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歐洲有很多河流的名字都叫Dan或者Don,像頓河、多瑙河啊等等,說明這個Dan、Don是之前的古代語言裏的對河的稱呼。但是現在這種語言在歐洲已經不見了。同樣的中國也有類似情況,如江浙地區有很多地名,像無錫、姑蘇、餘杭都是古代百越人的語言留下來的地名,我們現在仍在沿用,但是百越的語言本身已經消失了。所以,我們如果要想對這個上古時期的百越有所瞭解的話,那地名就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證據。
環球網:在您的閱讀經歷中,哪本書籍對您的創作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
鄭子寧:我覺得讓我產生對研究古代語言興趣的,是鄭張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這是一本關於上古音的非常有意思的書籍。這本書也問世20年了,雖然裏面一些關於語音的研究已經稍顯陳舊,但是還是相當具有啓發性的。
環球網:您還有哪些書籍推薦給您的讀者們閱讀?
鄭子寧:除了我近期最新出版的《中國的十個名字》外,後浪傳統文化編輯部還出版了一部關於長城的攝影集《長城形態圖志》,我想把這本書推薦給大家。和之前提到的一樣,中國兩個字好像總能濃縮成絲綢、瓷器等具象化的事物,顯現在人們大腦中。而長城也是一個象徵着中華民族的縮影,它是中國古代精湛的營造技術與文化智慧的巔峯體現,更是世界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偉大建築成就。
市面上現有的涉及長城的書籍大多聚焦於描述和體現其歷史沿革、地理分佈、旅遊價值或自然景觀,相比之下,《長城形態圖志》的視角則十分獨特,它用影像和文字深入探索長城建築形態的細節在記錄現實的同時,發現這長城獨特的美,是一本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