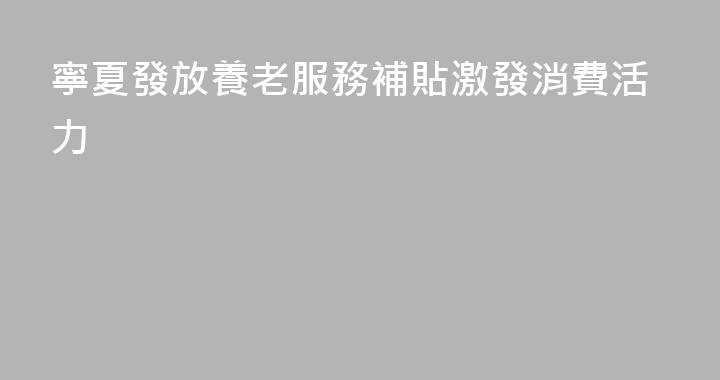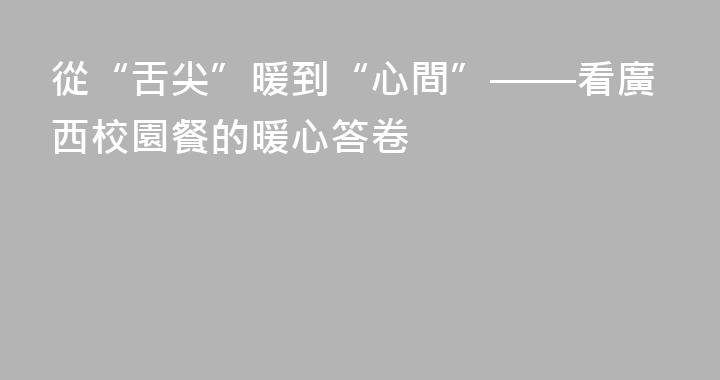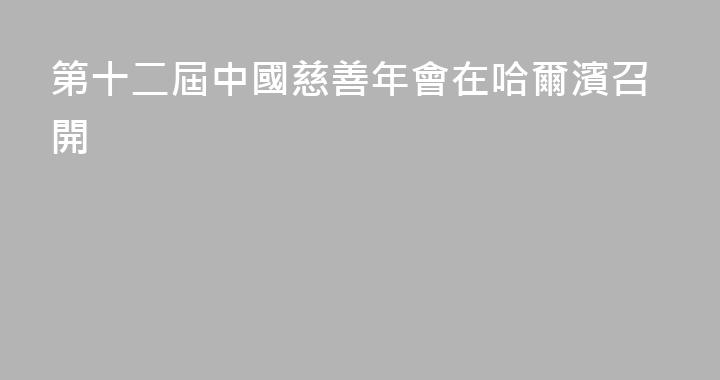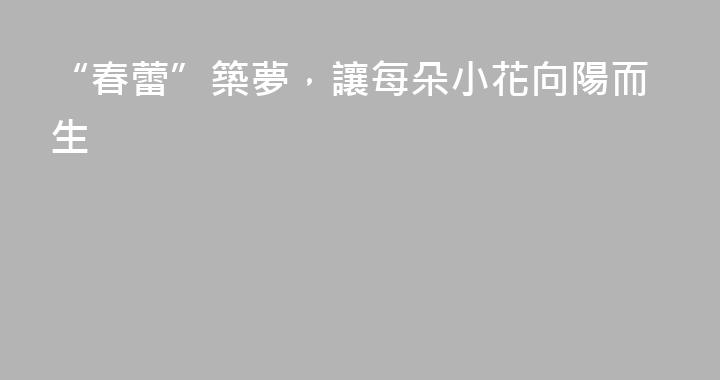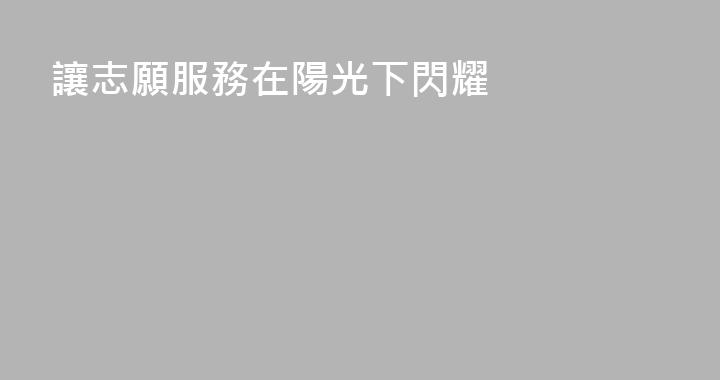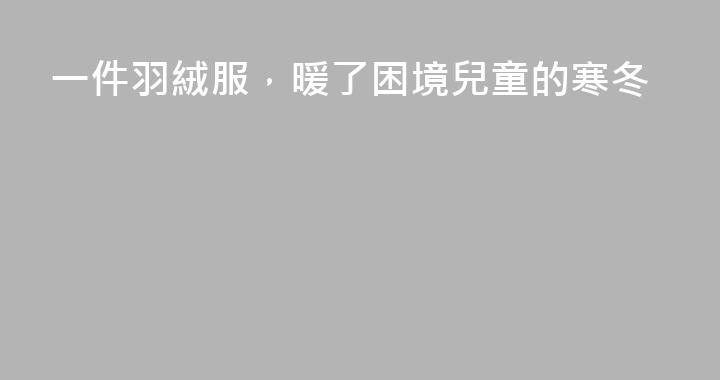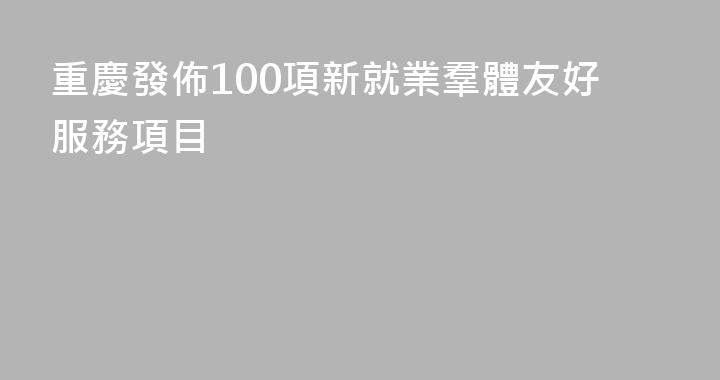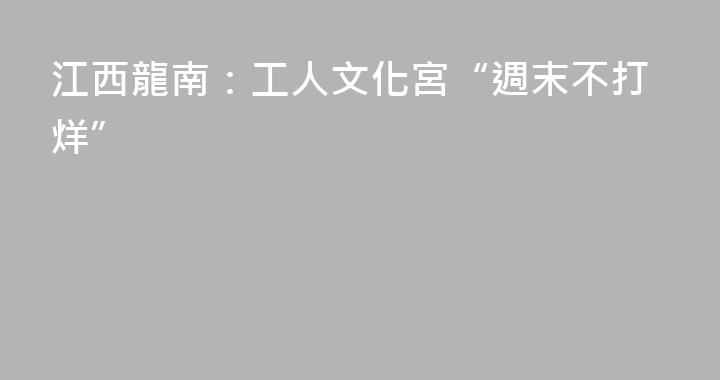【環球網公益頻道 記者 文雯】“我認爲閱讀真的有用。新媒體閱讀是未來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但碎片式閱讀不能替代讀長作品,聽書也代替不了紙質閱讀。因爲接受的方式不同,獲得的成果也是不一樣。”——張之路

見科學,也見文學
張之路畢業於師範大學的物理系,在中學當過物理老師,後又在電影廠工作多年。豐富的從業經歷,對張之路的創作有着很深的影響。張之路認爲,他的作品是集理科思維、影視思維與文學思維,三種思維“團結”在一起所展現出來的。
在構思創作科幻作品時,張之路會堅持三要素原則:第一,是“順理成章”即邏輯自洽;第二,是科學元素;第三,是人文思考。“當然,新奇性也是我非常注意的事情。”張之路補充道。
在構思新作品的初期,張之路就想寫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圍棋的故事。如何寫出新意?張之路想到了“讓機器人下圍棋”。創作過程中,張之路腦子裏也閃現着一種思想——製造機器人有兩個方式:一個是把機器改進爲機器人,另一個是把人“改進”成機器人。由此,張之路創作完成新作——《棋門幻影》。
《棋門幻影》是一個弟弟尋找姐姐的故事;是一個圍棋盤上棋子的故事;也是一個機器人的故事……圍棋是這部作品環境背景和故事發生的場地。張之路在這部作品中,更是注入了一份思考和擔憂——人類向何處去?
張之路對環球網記者表示:許多作家只要拿起筆,將書寫頻道轉到科幻的時候,就不由自主的陷入“只見科學,不見文學”的狀態,書中的人物開始具有不食人間煙火的能力。這種狀態寫出的作品,可能神奇、可能怪異,但是缺乏情感,把文學中強調的表現人性、刻畫人物放在了一旁。張之路認爲,這樣的科幻文學作品,在“文學”二字上是欠缺的,這也是他極力想克服的一點。
不忽略兒童的純真的天性
說起張之路的代表作品,無一例外會想到《霹靂貝貝》,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回憶。這也讓張之路感到欣慰,“我要感謝廣大觀衆和讀者。當時科幻類型的影片稀少,我以爲受到歡迎的原因,是因爲這部影片跟上了那個改革開放年代的步伐……”
張之路始終堅持真實地表達少年兒童的心理變化。想成爲普通孩子的“霹靂貝貝”,爲了重返童年的康博思,手握充滿魔力蟬筆的秀男……每個故事所展現的人物形象,讓觀衆、讀者在感嘆張之路對少年兒童的共情力之深外,也不難發現,其作品除了內容新奇,更重要的是細膩地情感表述與人生哲思的傳達。張之路對記者表示:書寫這樣的角色,才能打動人心。
張之路的文風和現在的主流文風不同,沒有刻意的“優雅”或“煽情”,而是平實的敘述。這種平淡的風格,在現在衆多語句華美、文辭誇張的文學作品中顯得獨樹一幟。故事地敘述方式和人物的心理描寫都十分貼合孩子的視角和情感,更能夠引發讀者的情感波動。這無一不體現了張之路的堅持:不忽略兒童的純真的天性。
記住肩上的責任
如果把陶冶情操、感染、影響或者潛移默化都看成是教育的一種方式和路徑,那麼書對人的教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張之路認爲:關鍵在於對青少年讀者給與什麼樣的教育。
“當然小學生和中學生接觸的書也應該有所區別”張之路對記者強調。“我寫過一本書叫做《第三軍團》,寫的是中學生,讀者也主要是中學生。在題記中我寫道:明天的幸福和光榮屬於你們,明天的痛苦和艱辛也屬於你們……但是我們更要告訴青少年,挫折是通向成功的橋樑,未來是光明的!”
張之路認爲,應該告訴青少年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們,這個世界除了幸福還有艱辛。這些提醒和告誡會有助於他們的成長。
“我在給孩子寫東西的時候,還是很注意:多些美好,少些苦難。但對於他們成長中的煩惱,我還是沒有迴避。”張之路舉例道,“比如我寫《羚羊木雕》。作品似乎都要有個主題,我以爲主題並不是單一的符號,而是表達人類多方面的追求與思索。面對困惑,面對抉擇甚至是痛苦的抉擇,也是一種主題。這個主題也不是僅僅存在於少年兒童當中。”
“給青少年寫作的尺度與電影分級的道理是一樣的。”張之路反覆強調“決不能爲了吸引眼球而寫作,在爲青少年寫作的時候,更應該記住肩上的責任。”
而提及兒童電影的現狀,張之路更是懇切呼籲:請電視臺在固定的時段開闢專欄,播放幾十年來我國優秀的兒童影片。讓孩子們享受這些本來就是送給他們的、卻與他們失之交臂的好電影。讓這些電影再次登上熒幕,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