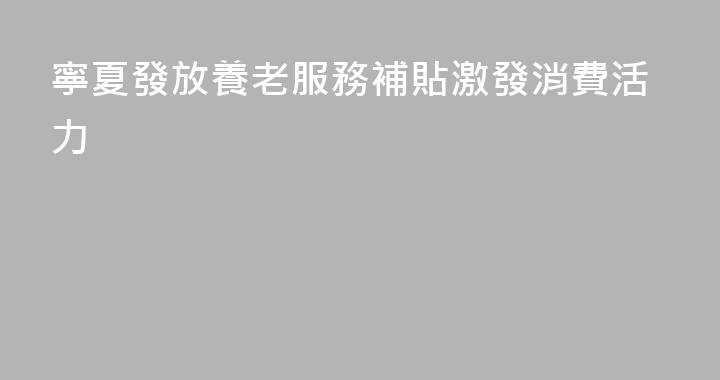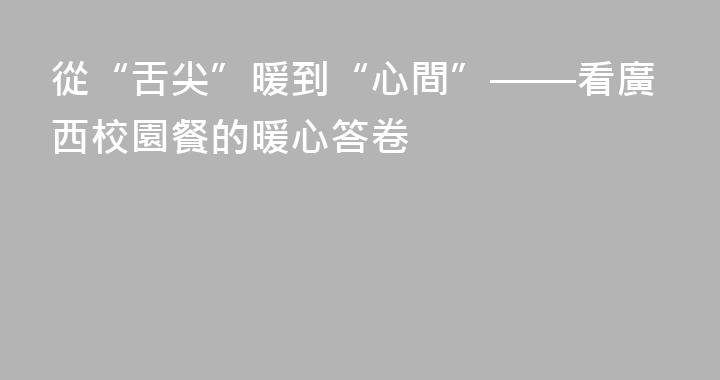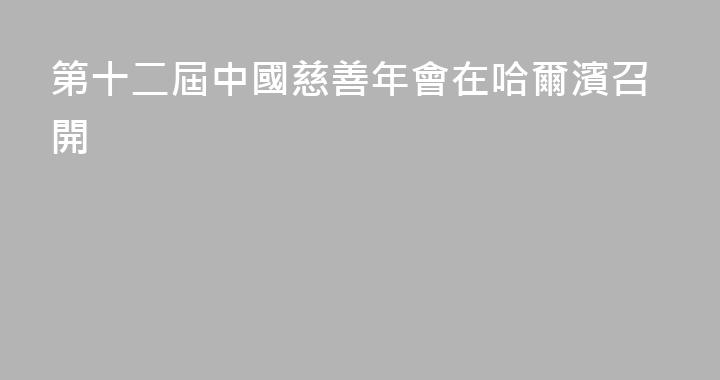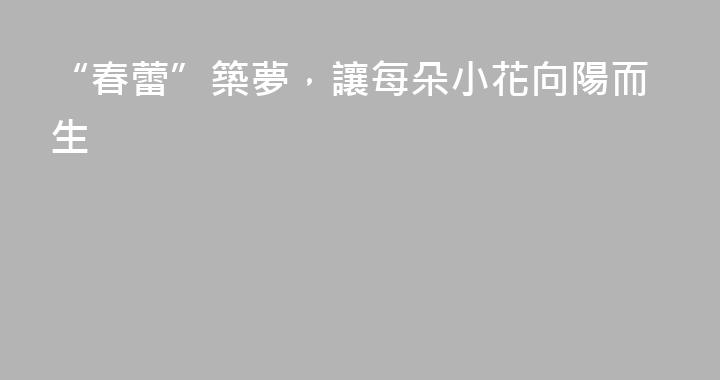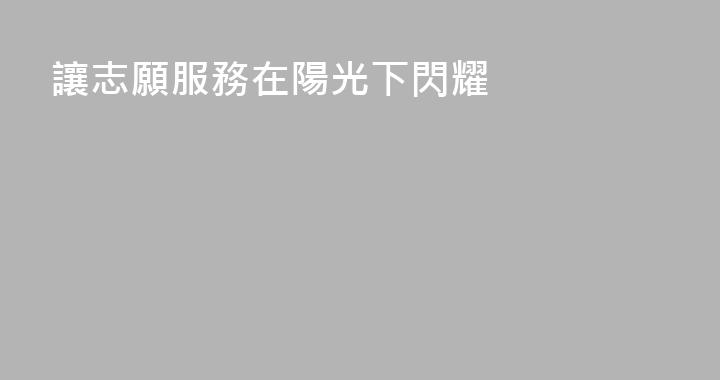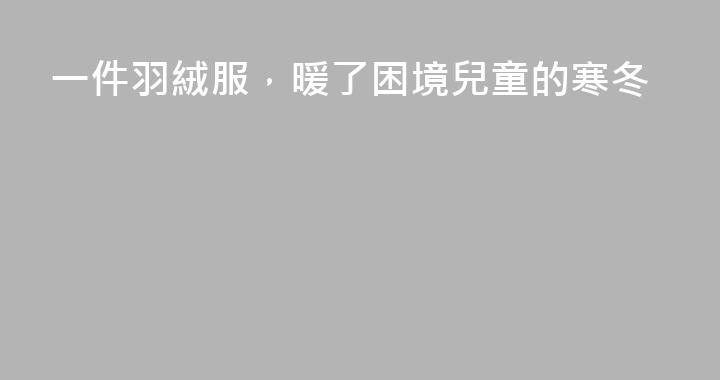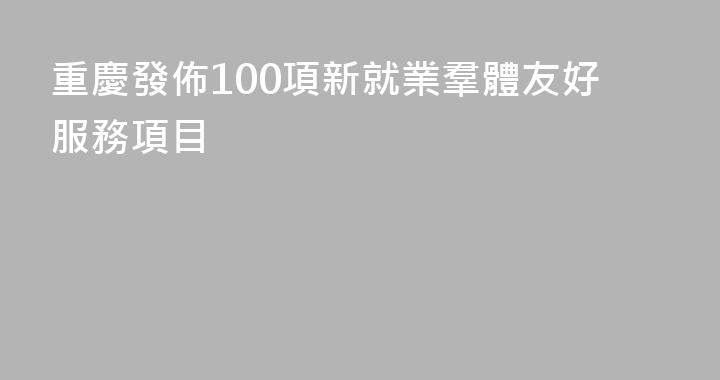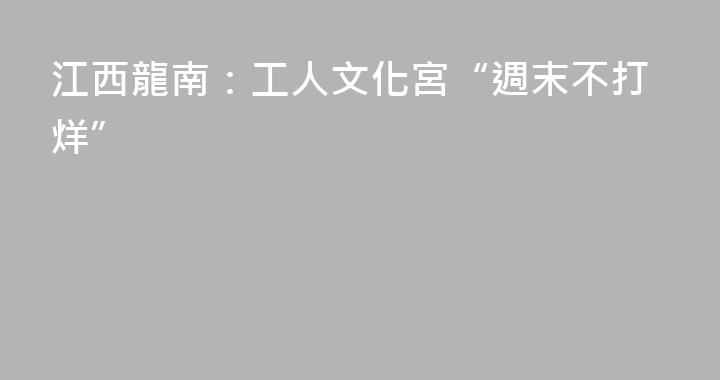【環球網公益頻道記者 文雯】2017年3月15日,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民法總則》,中國邁向民法法典化時代,其中新增規定了“綠色原則”,即第9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該原則在2020年《民法典》中得以進一步確立。一般認爲,“綠色原則”的確立展示了國家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以及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決心。“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中的確立更是中國民法對世界民法發展的一大貢獻。
武漢大學的陳海嵩教授從事的專業是環境資源法,這是一個綜合性、交叉性學科,涉及到多個傳統部門法,其中民法與環境法的交往非常緊密。在確立“綠色原則”後,對所有民事主體的行爲都提出了相應的規範要求,有許多新問題需要結合民法和環境法知識進行分析理解,陳教授認爲“有必要加以宣傳普及”。
陳海嵩教授在此次公益普法活動中,就“民法典‘綠色原則’的法律適用”的問題,從“具體規範及其要求”和“典型案例”兩個方面,爲大家進行講解。

《民法典》中貫徹“綠色原則”的具體規範及其要求
民法典中貫徹“綠色原則”的具體法律規範,主要在物權編、合同編以及侵權責任編中有所體現。
首先,爲物權設定“綠色限制”。具體包括:民法典第286條、第326條將“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作爲用益物權行使的基本要求;第346條把“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作爲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並嚴格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條件。
物權領域中引入綠色原則主要是對傳統物權的限制。傳統意義上的物權是一種絕對權,權利的行使不受其他阻礙。但是在綠色原則要求下,物權的行使需要負擔生態環境保護義務,符合相應的環保要求,否則就是違法而不受法律保護。
第二,爲合同履行設定“綠色約束”。具體包括:民法典第509條第3款把“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作爲合同履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對所有類別合同的具體履行提出了環保要求,否則就不予成立或沒有法律效力。在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還配套出臺或調整了一系列司法解釋,例如《關於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對此進行了細化。其中專門規定,當事人約定在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勘查開採礦產資源,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者損害環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依法認定爲合同無效。
第三,完善侵權責任以守護“綠色底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對綠色原則的體現比較集中,即該編第七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其中規定了生態環境侵權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有代表性的規定有:第1232條新增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懲罰性賠償責任;第1234條和1235條明確了對生態環境損害應當承擔的修復責任和賠償範圍等。
侵權責任編貫徹綠色原則後出現的變化比較大。其一,在原有的環境侵權責任之外增設了生態環境損害責任,將民法對生態環境領域侵權行爲的調整,從傳統的環境污染責任擴大至生態破壞責任。其二,從法律層面上鞏固和確認了自2015年以來實施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改革,爲追究生態環境損害行爲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和生態修復、賠償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
適用“綠色原則”的典型案例
第一,綠色原則在物權領域的司法適用。物權糾紛類案件主要是請求恢復原狀、排除妨礙等類型案件。在大部分案件中,法官基於綠色原則認定,恢復原狀或排除妨礙容易造成資源浪費或不利於保護環境,故不予支持原告的訴求。
綠色原則在物權領域的典型案例,代表是原告依據相關條文要求被告限期處理污染物、廢棄物,以及運用綠色原則駁回原告排除妨礙的訴訟請求。例如,在朱某某與何某某相鄰關係糾紛案中,原被告是鄰居關係。被告長期將生活垃圾傾倒在原告宅基地後,嚴重影響原告的生產生活,因此訴至法院。湖北省保康縣人民法院認爲,被告丟棄垃圾對原被告雙方的生產、生活,居住環境都會產生影響,理應清除。又比如,在沈某某與沈某某排除妨害糾紛案中,原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伐去或移走其種植的椿樹。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認爲,椿樹不屬於有害植物,且有一定的綠化價值和環保價值。故原告要求將該椿樹排除妨害,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也無現實緊迫性,更不利於保護生態環境、不予支持。
第二,綠色原則在合同領域的司法適用主要圍繞合同效力、違約責任的承擔等類型的案件展開。相關典型案例中,法院援引綠色原則對因保護環境的違約行爲作出不需要承擔違約責任的認定,以及援引最高院《關於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損害環境公共利益的採礦行爲作出未履行合同無效的認定。例如,在上訴人何某某與被上訴人趙某某合同糾紛案中,涉案企業或者個人與該地水務局均沒有簽訂河道採砂合同,沒有辦理河道採砂許可證。法院認爲該協議涉及在黃河一級支流渭河河道內無證採砂的行爲,不僅侵害國家的自然資源所有權、政府對礦業市場的監管,而且極易引發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危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依法認定該合同無效。
第三,綠色原則在侵權責任領域的司法適用。主要案件類型包括綠色原則在各類污染侵權責任案件中的說理應用,以及環境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28號“李勁訴華潤置地(重慶)有限公司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中,正對原告住宅的萬象城購物中心外牆上安裝有一塊LED顯示屏用於播放廣告等,該LED顯示屏廣告位從2014年建成後開始投入運營,每天播放宣傳資料及視頻廣告等,其產生強光直射入原告住宅房間,給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影響。法院判決中援引了綠色原則,判決被告構成了環境污染侵權。
第四,綠色原則在司法適用中的輔助性功能,主要包括藉助綠色原則進行規範填補,以及利用綠色原則中“節約資源”的規定補強說理。例如,在郭某某與武某某等租賃合同糾紛案中,原告租用被告的土地準備用於建加油站,後因客觀原因未能在該土地上建加油站,也未用作其他用途,土地處於閒置狀態,原告以相關部門不予批准建加油站爲由要求與被告解除合同,並要求被告返還租金。法院在判決書說理中援引民法綠色原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認爲若繼續履行合同對原告明顯不公平,並會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因而支持了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訴求。

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宣佈將在 2060 年達到“碳中和”。碳中和目標,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環境保護法》作爲環境基本法,從基本原則、基本制度上促進“碳中和”目標實現;《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節約能源法》等作爲單行法,從各自領域促進“碳中和”目標實現。陳海嵩教授表示:環境法在實現“碳中和”目標中發揮着核心作用。
陳海嵩教授從事法學教育已經有13年左右,地點包括浙江、湖南、湖北等地,教學的對象也比較廣泛,最大的體會是“隨着依法治國戰略的推進,人民羣衆對法律知識的興趣和需求不斷提升”。陳教授舉例道:比如說,原來社會上對環境法並不是很感興趣,但近年來有明顯改觀。這裏面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對環境法給予了更多重視,通過各種方式加強了相關普及工作,使得越來越多人加以瞭解。陳海嵩教授對記者強調:“普法的最大意義在於促進社會各界更加理解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更好的形成法治建設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