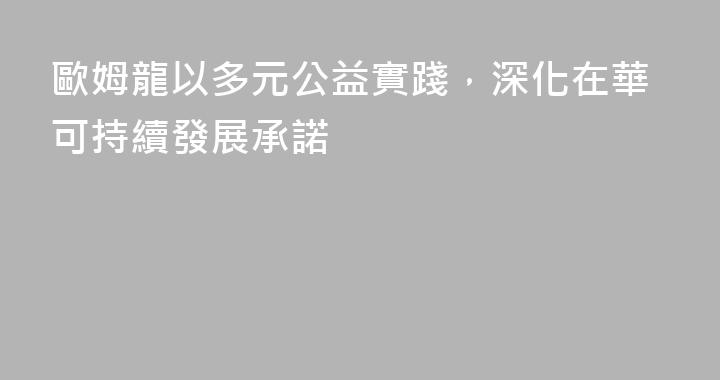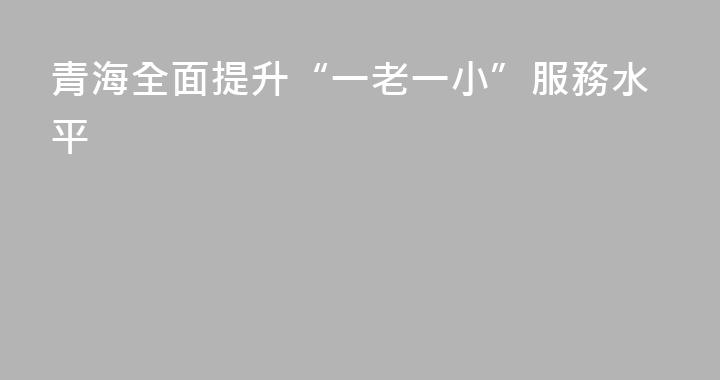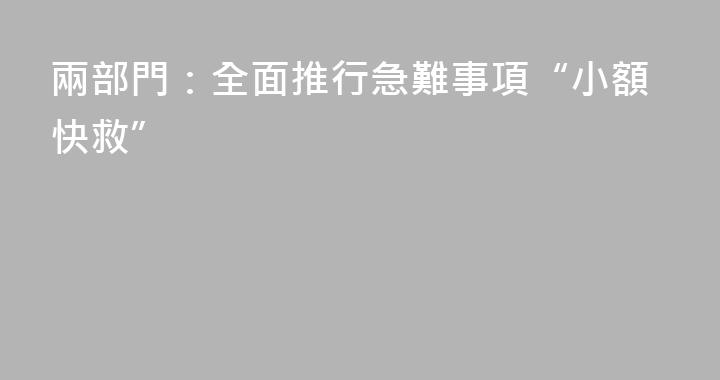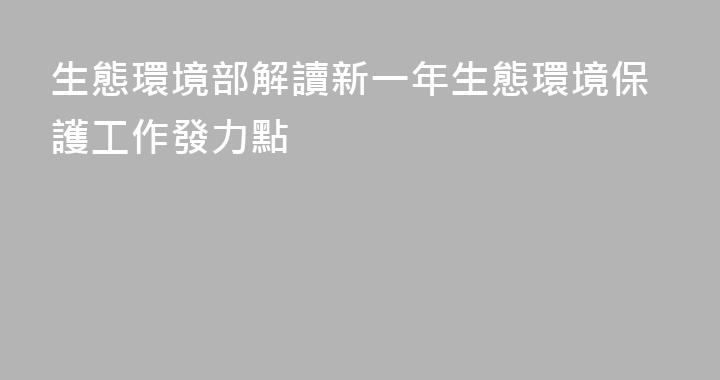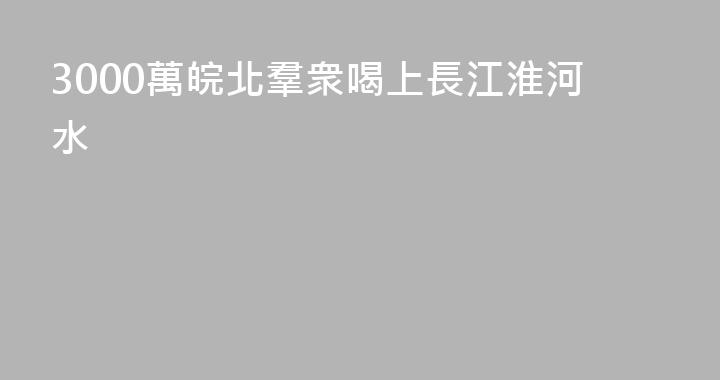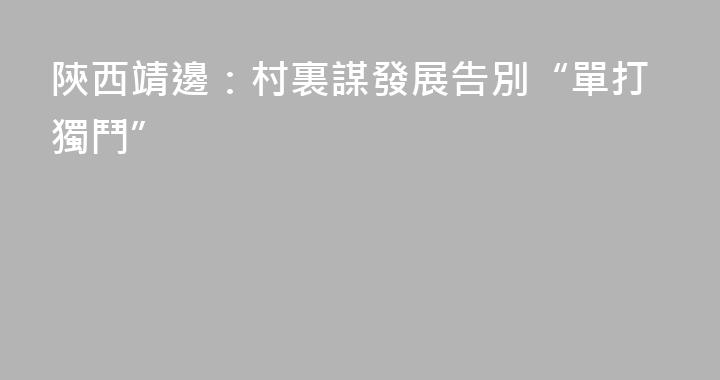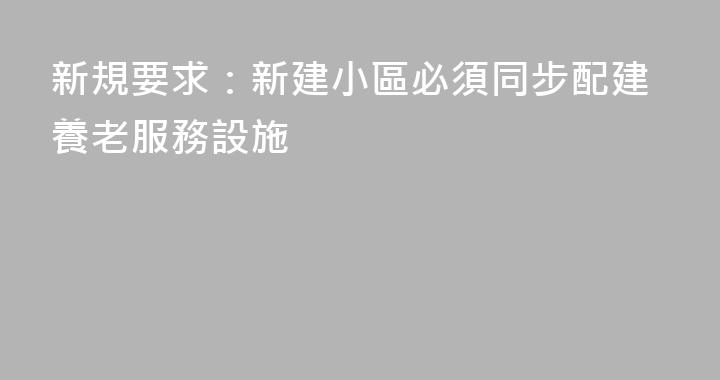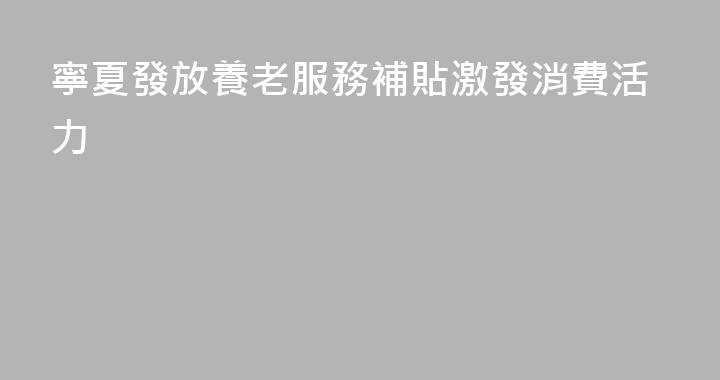“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戰爭還遠沒有結束的意思,但或許它的初級階段即將結束了).”
這是二戰時丘吉爾的名言,近日被美國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醫院引用,以鼓舞醫護、病患和市民。因爲感染人數激增,防護物資儲備不足,醫生們面臨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4月初至今,喬治城大學非營利組織領導人能力提升研修項目校友會、鳳凰網聯合美國道·安基金會、美國華人民間組織公益基金會、美國鋪路石基金會發起的“中美NGO聯合拯救生命行動”(下稱“行動”),已採購近3萬隻N95口罩,並送達紐約、大華府、紐黑文地區的15家醫院。另有20萬隻從中國採購的一次性醫用口罩,正在分發給公共服務人羣和貧困人口。
從醫生們的介紹中,志願者們感受到恐慌、感激和義無反顧。15家醫院的情況,只是當下戰疫一線的一隅,但好在還有更多的志願者在行動,年齡跨度從60後到00後。
春陽煦暖,希望醫生們口中嚮往的“慵懶日子”,不再遙遠。
01 大華府
N95口罩需被重複使用
Shelly和Peter(均化名)是一對印度籍夫妻,供職於大華府地區一家綜合性醫院。疫情爆發後,他們所在的醫院開始收治新冠肺炎確診病例。Shelly是麻醉科醫生,在一線重症病房做插管工作,Peter是內科醫生,接診非重症患者。
他們說醫治患者是本職,願意爲此付出時間和精力,但沒想到醫院儲備的防護用品會日益緊缺。新冠病毒突襲全球,人類還處於對它的逐步瞭解過程中,很多大型醫院沒有長期儲備防護物資,以應對如此大型而兇險的流行病。得知病毒會通過氣溶膠傳播後,Shelly和同事們想領N95,被院方建議,如果現有口罩沒出現肉眼可見的污染,請重複使用。
Shelly和Peter的一隻N95口罩,有時候可能要用幾天甚至是兩三週。頻繁摘脫也容易污染口罩,沾染病菌,他們的心理壓力很大,因爲家裏還有個小嬰兒。
迫於無奈,夫妻倆向朋友們求助,希望借到或是買到一些N95口罩。3月底,他們找到了朋友Jane。Jane是當地華人,在大華府地區工作生活了20年。她說,當時家裏儲備較多的是工程防塵口罩,並不防液體,但還是拿了一些給Shelly和Peter,“他們說可以想辦法在工程口罩外面再加戴一隻醫用外科口罩”。
Shelly和Peter的遭遇讓Jane心疼。4月初,她加入“中美NGO聯合拯救生命行動”,以志願者身份,參與查詢、統計大華府地區醫療物資的短缺情況,再根據已採購的口罩量,分別捐贈給有需求的醫院。

在和醫生們的溝通中,她發現,所有人都對當下的工作義不容辭,唯一的顧慮是身後的家人。有的家屬正在化療,或患有高血壓、糖尿病,抵抗力低。有的華人醫生夫妻自己帶孩子在美國生活,只能輪流上班。在醫院時,他們比其他人更頻繁地洗手,在家只要和孩子在一起,就會戴着口罩。還有人把自己隔離在地下室,關閉了中央空調,三餐由家人送到樓梯口。
除了口罩緊張,還有的醫院會抱怨隔離衣不足、呼吸機耗材不夠等問題,Jane介紹了她瞭解的情況。因爲新冠肺炎不同於以往任何一種傳染類疾病,個別醫院能操作呼吸機的專業人員數量不夠,一些耗材的儲備也不足,另有的醫院隔離衣質量不佳、數量不多。“比如現在確診病例還在上升,美國醫院會盡量保證每人一間負壓病房,所以醫生每走進一間病房,都要更換一次隔離衣。爲了方便穿脫,他們的防護服比較簡易,不像國內是從頭到腳多層包裹。”

02 紐約
定點醫院一天收治百人
行動發起方之一美國華人民間組織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姚南負責統計紐約一線醫院的需求。他介紹,布魯克林SUNY Down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是目前紐約州三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之一。這裏共有400多張牀位,ICU和急診室早已滿員。即便如此,還會有救護車源源不斷地送來病人,醫院平均每天都要收治百名患者。
救護車急診室門外的路上,搭建了幾個臨時收治的帳篷,較大的一個負壓帳篷裏,大約能收治40名新冠病例。

Lorenzo Faladino是這裏的急診室主任,看着身邊的“戰友們”,有的已經確診、或是被隔離觀察。他和堅守一線的醫生們每天輪班,一個班次大約十二三個小時,隨時還可能繼續加班。除了一部分不可避免需要使用呼吸機的危重病例,他們會盡量通過使用氧氣面罩等方式,爲病人輸入高流量氧氣,協助治療。
如此高壓狀態下,Lorenzo和同事們小心翼翼。他說,院方正考慮將部分病人轉到周邊的診所或醫院。因爲除了人手緊張,他們對口罩等防護用品的需求量也日益提高,比如一線醫生的單日口罩用量大約四五百隻,他們有職責醫治病患,也必須保護同伴。
法醫日接死亡案例激增10倍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Chief Medical Examiner分子遺傳實驗室主任唐迎迎向志願者姚南介紹,疫情期間,很多病人在家中去世,可能存在未確診就死亡的情況,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因此設立了鑑定疑似新冠死亡的小組,檢查除醫療機構、養老院之外的死亡病例,不少有明顯新冠肺炎症狀的死者,會被判定爲疑似死亡病例,計入紐約市衛生局總死亡人數中。

唐迎迎說,特殊時期,他們接收的死亡病例鑑定需求,由之前平均每天25例,增加至每天超過200人,“既包括感染新冠導致死亡的病例,也有非新冠的死亡情況。”
爲應對激增的死亡鑑定需求,實驗室部分人員已經被調去協助一線法醫,同時幫助前線收集資料,做好後方工作,所以法醫們對口罩的需求也不小。
03 捐贈
N95口罩發放15家一線醫院
對於一線醫院物資儲備不足的情況,《紐約時報》曾在3月30日刊發評論文章《Nurses Die, Doctors Fall Sick and Panic Rises on Virus Front Lines(護士死亡、醫生病倒、一線恐慌心理加劇)》。該文章稱,新冠肺炎病毒正在向紐約市的醫療隊伍蔓延,醫護人員焦慮情緒激增,目前已有2名護士死亡。在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因爲一半ICU特護人員感染,有主管鼓勵外科醫護上前線;紐約市內一家大型醫院的醫生形容,自己的辦公區域是一個“培養皿”,有200多名工作人員在這裏感染。

3月29日,紐約布朗克斯區,雅各布醫療中心的醫護在街頭抗議防護物資急缺,包括N95口罩。據《紐約時報》
根據志願者們一週多的需求摸底,行動組從洛杉磯採購了近3萬隻N95口罩,截至北京時間4月15日凌晨,送達紐約8家醫院、大華府地區5家醫院和紐黑文的2家醫院,支援一線醫生的防疫工作。



“這批醫用物資非常及時,感謝捐贈,我們一定會充分利用這些口罩。”New York City Office of Chief Medical Examiner受捐方代表說。
從醫生們的表情、言語間,60後、發起方之一鋪路石基金會成員饒冰頗有成就感。這是他第一次參與公益項目的執行工作。前期蒐羅大華府地區各醫院防護物資需求時,他感受到了強烈的緊迫感。但因爲自己有本職工作,屬於美國基礎領域的工作,疫情期間也不能停,他只能充分利用週末和工作日空閒時間參與志願服務。“醫院急缺防護用品的情況,我原本只是在新聞中看到過,現在卻真實地發現它們也發生在我身邊。這也成了我和其他志願者夜以繼日的動力,必須儘快釐清需求,依實際情況給他們幫助。”
他對接的受捐醫院裏,Medstar 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是美國第三大醫院,目前有1200多張病牀,已痊癒或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100多名。得知志願者饒冰和Lance帶着捐贈品即將抵達,該院兩位中國醫生Mark Lin博士、Tom Deng博士提前換下手術室的衣服,迎接他們。慈善事業部高級官員Gabriel Pinski說,這批物資有如及時雨,因爲就在當天,馬里蘭州長髮表講話稱,該地區未來一週將迎來疫情高峯,各醫院需做好準備。

志願者Lucy在往返醫院的路上,看到了不少安置死亡病例的冷凍集裝箱。製冷壓縮機的馬達聲讓她揪心,但也讓她更迫切地感受自己參與志願服務的意義。“中國疫情嚴重時,我們籌集了口罩、呼吸機等物資回國,現在病毒就在眼前,我們團結一心,爲鄰居、社區、醫生羣體送去他們需要的物資。這是特殊而光榮的事!”

“不過也有很多護士或護工會小聲問我們,還有沒有醫用外科口罩可以提供給他們。”Jane說,不少醫生會感動,覺得自己有了防護保障,可以從一定程度上保護家人,但那些不直接接觸確診病例的崗位,還在想辦法籌集低級別醫用防護物資。
目前,在查閱媒體報道和需求調研中,行動組發現,除了醫護羣體,美國東部比如紐約,越是貧困的地區,感染率越高,這也讓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服務這一弱勢羣體的公共服務人員,比如警察、送餐員、公交司機等。目前,用於支援這部分羣體的20萬隻一次性醫用口罩從中國江蘇運到了美國。這羣60、70後志願者們正發動親朋好友,一起爲口罩加貼活動標識,分發給受捐方。



北京時間4月17日凌晨,紐約警察、救濟所收到志願者送去的一次性醫用口罩。
Jane通過這一場抗疫行動,更真切感受到了“地球村”的概念,“來自不同城市、不同國家的人,爲了同一個目標付出時間和愛,這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善。”
作爲當地華人,饒冰覺得他的行動意義除了拯救生命,緩解一線醫生的心理壓力,還能讓鄰里多一個角度,理解“中國形象”。“很多志願者有本職工作,不能完全投入行動,但我們還在招募有激情的成員加入。”
抵抗疫情的每一條路上,都不會是一個人在“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