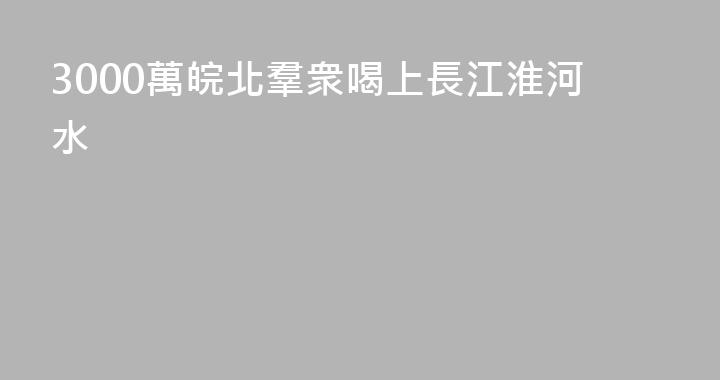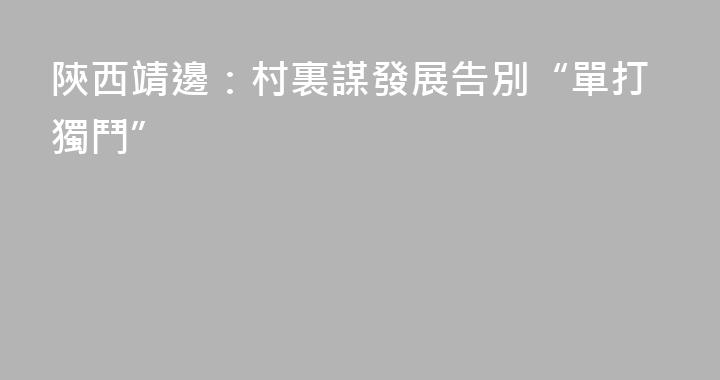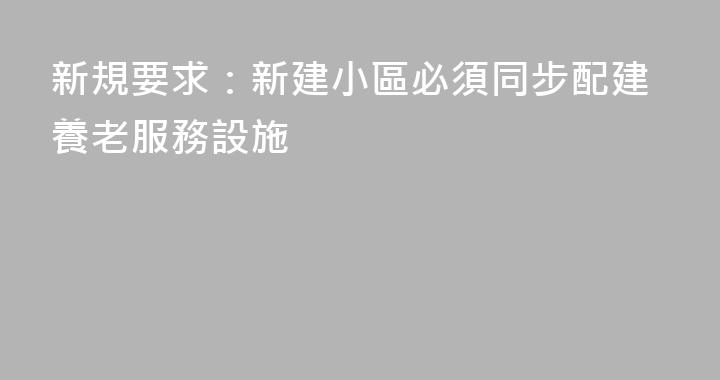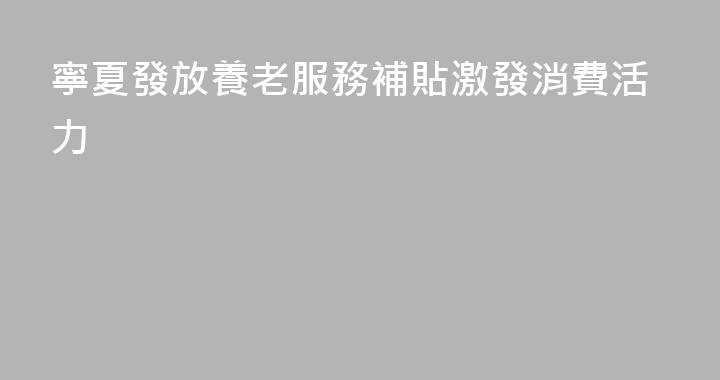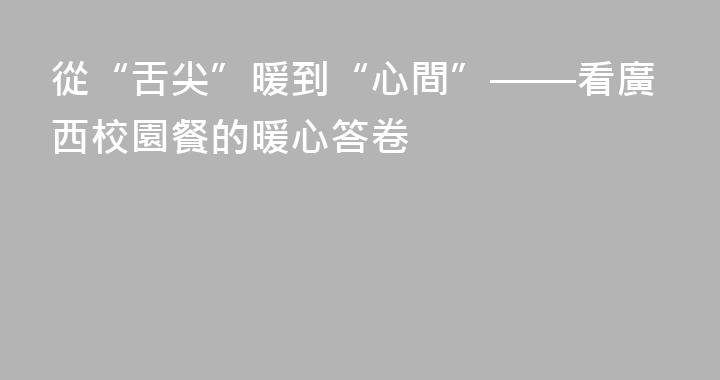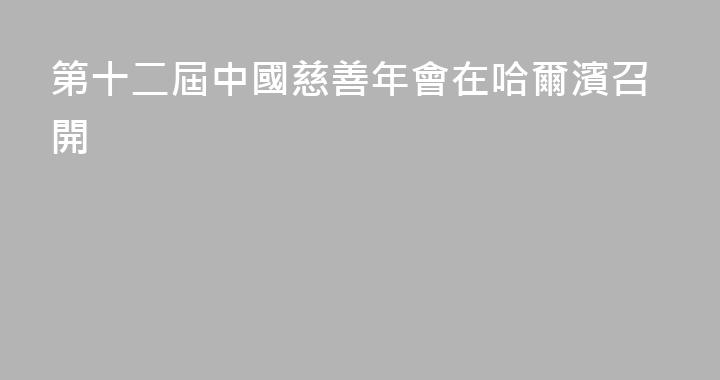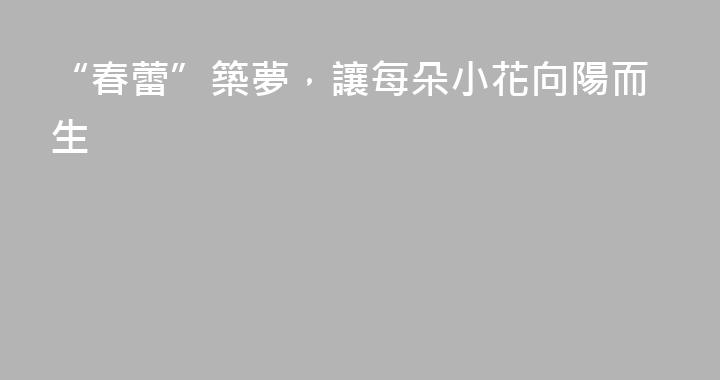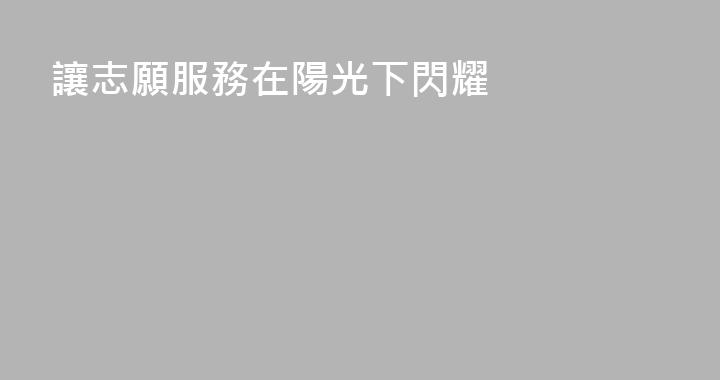作者:愛德基金會副祕書長 何文
中國社會組織最近些年發展很快,目前總數已經超過八十萬家,業務區域從最初只限於國內到逐漸走向國外,國外工作涉及的專業領域從最初的人道主義救援擴展到其它民生髮展領域。
在發展過程中,不少社會組織都表現出了走出去開展國際發展援助工作的衝動與興趣,有些社會組織已經在國外實質性地開展發展援助工作。針對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話題內容的各種討論和交流越來越多,新聞媒體對社會組織走出去的報道也越來越多。
從這些具體行動、討論交流及新聞報道內容來看,人們對社會組織走出去表現出的態度與看法多種多樣,這反映出人們對社會組織走出去參與國際發展援助工作的理念和認識差異。

3月23日,喬治城大學非營利組織領導人能力提升研修項目校友會、鳳凰網聯合美國道·安基金會、美國華人民間組織公益基金會、美國鋪路石基金會共同發起“中美NGO聯合拯救生命行動”,用於支援美國東部地區一線醫生和公共服務人員防疫工作。
當今世界,很多社會問題都日益呈現出全球性和國際性特點,國際社會大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國社會組織作爲世界社會組織大家庭中的一員,在推動國際人道主義和社會發展事業的過程中應發揮自身的作用。
但是,針對最近幾年有關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實踐和各種論壇交流和媒體報道情況來看,爲了有效地走出去參與國際發展援助及國際治理工作,無論是行動上還是認識上,中國社會組織都應該走出幾個誤區,否則,會給中國社會走出去帶來巨大的困難和麻煩,甚至走向失敗。
首先,走出企業工具論誤區。
不少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有關專家學者或者媒體人員認爲,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目的和作用是爲中國企業走出去鋪路,或者通過社會組織去國外當地社區開展各種發展援助工作,緩和中國企業與當地羣衆的矛盾和衝突。這樣的論調,在不少論壇中都出現過,甚至,有些論壇直接打出類似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和中國企業國外發展挑戰內容的主題。
其次,走出政府工具論誤區。
這樣的認識誤區在當前也十分普遍,不少專家學者或者媒體人員,甚至社會組織領導人經常提到,諸如,“爲了推動政府一帶一路戰略,中國社會組織應該走出去“”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爲增強國家的軟實力服務“等等,把中國社會組織當作政府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工具,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再次,走出方法傳授者論誤區。
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與普通中國公衆一樣,中國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在國際交流合作場合中越來越自信。的確,我國在最近幾十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各行各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並且爲全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於自身的發展,我們總結了不少寶貴經驗和方法。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時候自認爲可以在很多領域,包括人道主義與社會發展領域做他國社會組織的老師,可以教導他國社會組織如何開展人道主義和社會發展工作。
最後,走出制度改造者論誤區。
通過中國人民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探索,我國目前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社會制度的優越性。這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感覺,是不是要把改革他國的政策或者有關制度安排作爲我們走出去的重要目的之一。
上述幾個有關社會組織走出去的誤區在我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歸根揭底是人們對社會組織走出去的使命或者目標認識上存在根本性差異。
這其中有我們自身的原因,也有不少是因爲受到西方歐美中心主義思想的非政府組織走出去開展國際發展援助的影響造成的,最典型的莫過於美國一些社會組織熱衷於在世界各地改造他國既有制度安排,推行美國的民主理念與方法及其美式文化。
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究竟是爲什麼呢?這個問題是我們在走出去時需要首先回答的根本問題,也是最近些年國際上,包括外國政府、非政府、外國的學術界和媒體以及普通民衆都特別關注的問題,在他們關注的過程中,不排除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新聞媒體作出以己度人的判斷,心懷叵測地過度解讀和歪曲宣揚和報道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種種行動,給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甚至國家的發展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和挑戰。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角度看,關於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使命或目標,我一直以來都堅持這樣的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目的不是做企業和政府的工具,也不是新技術新方法的教師爺和制度的革新家,而是與世界上有需要的各國人民共同分享人類的愛與友誼,是愛與友誼的分享者。
這與中華民族樂善好施、友愛互助的歷史傳統以及當前國家在世界範圍所倡導的建設人類民運共同體精神一致。
因此,在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這件事情上,我們一定要從這樣兩個方面糾正和深化我們的認識和理解,並付諸於腳踏實地的行動。
首先,從主客體關係的認識調整到主體間關係的認識上來。
社會組織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必然與外國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大到國家、民族,小到一個機構及其個體成員。人是具有豐富內涵和意義的存在,社會中的每個人或者人羣之於其自己和周圍環境各要素來講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價值。如果不轉變這樣的認識,勢必會使我們在工作中,將與我們展開合作的國家、民族或是機構甚至社區普通羣衆的價值固化於主客體關係之中,讓我們作出具有工具性和暴力性傾向的判斷和行動。
就這一點,歐美發達國家在十五世紀進行殖民主義擴張和二十世紀推行的全球治理機制過程中,他們走出去的行動給世界的發展帶來了不少的問題和巨大挑戰,甚至在不少國家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我們不能不吸取他們的教訓。因此,要轉變這樣的認識模式,建立一種主體間關係認識模式,承認對方作爲一種主體性存在,具有獨特的此在的目的和意義。這是實現走出去與世界各國人民分享人類的愛與友誼這個使命和目標的前提。
其次,從國內思維轉變到國際思維的認識上來。
毋庸置疑,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探索和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和方法,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企業管理,即使是還處於發展的最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組織及民間慈善事業,我們也都有了比較多的值得借鑑的地方。在幫助社會組織處理在國內所遭遇的挑戰和問題時,有些經驗的確有着十分普遍的推廣意義和價值。
從最近幾年的觀察來看,我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過程中還沒有拋棄國內思維模式,因而在走出去開展人道主義和發展工作的所在國,往往做出一些不太適合當地情況、貽笑大方事情來,這不但會造成資源浪費,不能解決當地羣衆的實際問題、滿足其實際需求,甚至會在所在國社會上造成極其負面的影響,給國際社會帶去一種對中國社會組織甚至中國人都很不好的形象,久而久之,將會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組織和中國的誤解和偏見。這與社會組織走出去分享人類之愛與友誼的使命和目標背道而馳。
因此,社會組織走出去需要從國內思維轉變到國際思維的認識上來。這可以有效克服我們在工作中照抄照搬國內方法和經驗的教條主義,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結合國際發展合作的一些普遍性價值理念,根據所在國的歷史傳統、社會文化與經濟狀況,包括地方羣衆的風俗、宗教信仰和生產生活習慣等,完善項目管理、溝通管理以及其他日常工作管理的過程和方法,提高社會組織走出去開展國際發展合作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在單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保守的“逆全球化”肆虐的時代,在瓦解和超越當今世界不利於全球共同發展的“無人在場“的零和博弈與冷戰思維模式,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動全人類和諧發展的進程中,中國社會組織面臨着巨大的機遇,也負有不可推卸的時代使命與責任。

“中美NGO聯合拯救生命行動”捐贈現場

紐約民衆領取“中美NGO聯合拯救生命行動”捐贈物資
如何走出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的誤區?想起來很複雜,其實行動起來也非常簡單。正如前幾年,與一位我國駐外大使交流的過程中,大使對社會組織在所在國的工作建議一樣:作爲政府,我們對社會組織走出去開展工作沒有什麼要求,如果說有要求的話,那就是社會組織不用考慮別的,不要搞形式主義,只要真正深入到當地社區、深入到羣衆中去,根據當地羣衆的實際情況,和他們一起工作,共同解決他們關心的問題,發揚我們中國人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踏踏實實地爲當地羣衆做一點實事,以滿足當地羣衆實際的生產生活需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