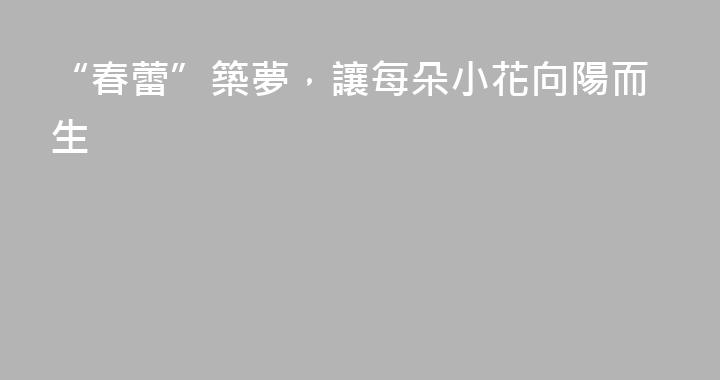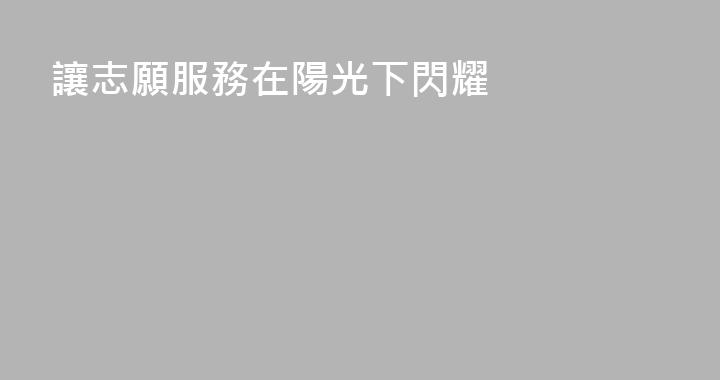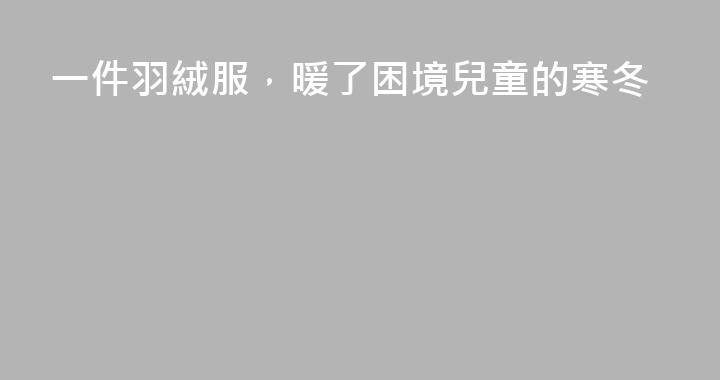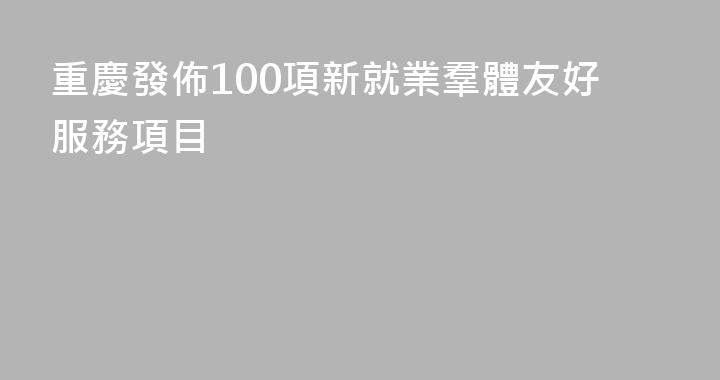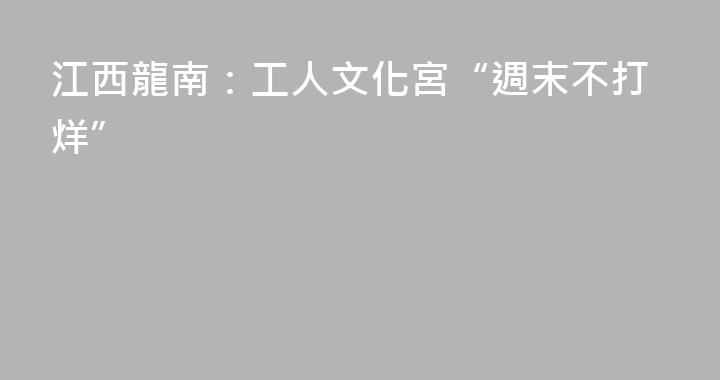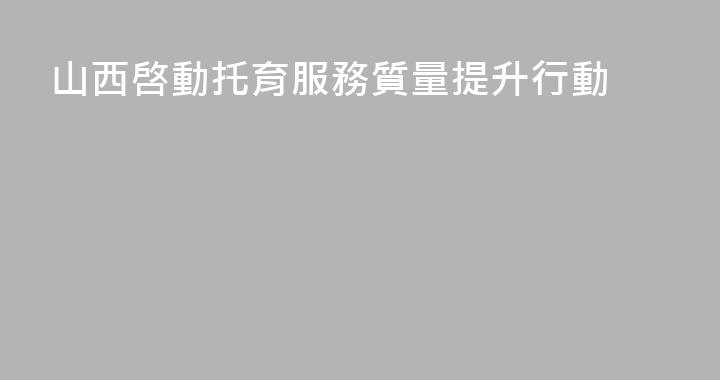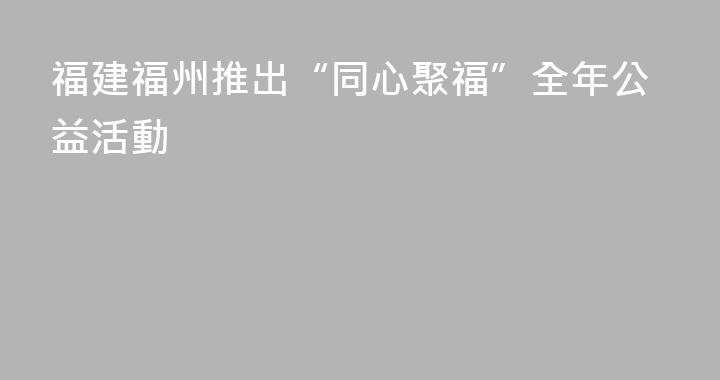今年4月,騰訊公益倡導舉辦首期公益股東人大會,截至目前已有84場公益股東人大會召開。至2022年99公益日期間,將完成100場公益股東人大會,儼然成了公益機構財報季。公益機構使用騰訊會議、視頻號直播等數字化工具召開公益股東人大會,與公益關係人溝通併發布財報,這在互聯網公益行業屬於首創。
數百家公益機構搶閘
99公益日前召開股東人大會
4月11日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滿天星公益”)作爲第一個喫螃蟹的公益機構,率先在線上召開公益股東人大會。

每一位參與騰訊公益平臺項目的愛心網友作爲所捐贈公益組織的“股東人”,可以與機構直接對話和交流,實現自己對公益項目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

第一次開會,滿天星的收穫就遠超預期。首場公益股東人大會後,滿天星公益的項目得到了有效傳播,更多人關注和參與進來。梁海光回憶,當時,騰訊公益做了一篇事後回顧的推送,稿件里加了項目捐贈的鏈接,迅速籌得4萬多塊錢。
對標平時籌款效率,4萬塊錢得半個月。而這一切,都是源於梁海光的敢於透明。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在滿天星成功“打樣”召開股東人大會之後不久,他們也想開了。
但平臺成千上萬的項目,不可能都由騰訊方來舉辦。這一次,騰訊公益沉澱相應的視頻教學和操作文檔,通過與恩派公益的合作,發起透明公益助力計劃。在這一計劃裏,騰訊與恩派對接開會的機構合作,通過線上教學,引導機構自主開會。

一番籌備操作後,如今公益機構已經可自行通過一臺手機進行開會。騰訊這一招可以說,只要機構有心透明,就不會做不到。

至此,公益股東人大會將開始一場量變積累。透明,逐漸成爲中國互聯網公益的行業趨勢。公益股東人大會正在潛移默化中豐富中國互聯網公益行業的透明內容。
400多家機構申請開會
退出的理由多爲知難而退
到底要不要開股東人大會?滿天星公益的梁海光、西雙版納州熱帶雨林保護基金會祕書長張錫炎、旬陽市守望大山志願者協會負責人張新斌堅定要開,但並非所有人都和他們一樣。

6月,騰訊發佈透明公益助力計劃機構夥伴招募,項目收到400多家機構申請。
這個問題讓不少機構從今年一季度就開始糾結。恩派公益工作人員李爽負責對接這些機構,她向我們描述了這樣兩種不敢開會的機構類型。
第一種是業務繁忙的大機構。李爽解釋,他們可能在早前的工作計劃裏已經將全年的工作任務安排得滿滿當當,人力上挪不出空閒,也就無法推進。
而另一種則是對“風險把控”比較嚴格的機構。比如有這麼一家機構。在前期騰訊公益做股東人大會宣傳的時候,他們就瞭解到了,也非常心動。 但該機構的管理嚴格,任何行爲都需經多個層級報批。
在項目負責人的推進下,報批成功,最終決定報名開會,也在層層選拔中脫穎而出,入選了開會項目。
培訓時,當他們得知這一批股東大會必須進行“自由答股東人問”環節,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如果他們亂問問題怎麼辦?我回答不出來怎麼辦?”
即使李爽用已經開會的項目案例打消了了項目負責人的顧慮,但遺憾的是,在負責人向上彙報後,領導沒有再一次批准,該機構最終退出了這一次活動。
激流勇進是勇士,知難而退是本能。即使他們都知道方向是對的。
因爲公益透明
他曾被追加50萬捐贈
“公益股東人大會”是否會對公益從業者不友好?對於這個問題,參加了騰訊公益人才數字開放計劃北師大教育第一期課程的公益行業從業者吳特立有他自己的看法。
“公益股東人大會用互聯網數字化工具,使得公益關係人(公益組織、捐贈人、受助者、平臺方)和公衆,第一次實現了無障礙互聯互通,探索公益透明和公衆治理的新模式。”
吳特立在課後與當天授課導師騰訊集團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騰訊公益高級傳播官黎明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真實情況。
2020年,剛畢業的吳特立入職珠海華髮公益基金會,從同一個捐贈人那裏陸續募集到了60萬的善款。
“其實最早的一筆他只捐了10萬,且很有可能這一筆捐贈以後就沒有下一筆了。收到第一筆後,他備註吳特立全權處理捐贈款,拿着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一直在糾結這個錢要花在哪兒,怎麼花才能讓捐贈人滿意?”
信任加滿,動力十足。捐贈人首期捐款打進基金會賬戶之後,吳特立每天晚上都會花費至少2小時的私人時間去和捐贈人聊天。“聊一下他對哪些公益事件是認可的?聊一下他認爲什麼樣的公益項目纔算公益項目?”
經過長時間的交流、打磨,捐贈人的捐贈款被吳特立獨立設計並執行了一個在珠海全市開展的創新型項目,並在去年獲了獎。
公益機構通過透明獲取信任,從而更高效地開展工作——事實上,最終的追求還是落到“高效”,實打實地幫到了項目的受助方。無效公益行爲再怎麼透明,也是對捐贈人信任的透支。
這也正如自媒體“公益資本論”創始人黎宇琳所說:“透明度無疑是重要的,但在透明的基礎上向公益機構提出“有效性”的質詢會更有意義。”
捐一塊錢的人
也和大額捐贈者監督同權
在第一次股東人大會結束後,有人就“1塊錢”的公益行爲展開討論。只捐一塊錢就能對機構指手畫腳,這合理嗎?
滿天星公益的梁海光就遇到過言辭犀利的“一元股東人”。但他並沒有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有什麼問題,甚至邀請對方前來做內部審計。“很多審計的老師來審計完了之後,都成爲了我們的捐贈人。”

梁海光們的坦然,也讓小額捐贈者捐贈熱情與日俱增。這其中就包括騰訊平臺月捐項目長期捐助人趙靜禕。作爲一名沒有穩定收入的大學生,趙靜禕很難進行大額捐贈。
“我們可以捐一塊錢、一杯奶茶的錢、或者是一根冰棍兒的錢。看到自己的捐贈能實實在在幫助到了項目受助方,就會想持續關注,持續捐助。”
令趙靜禕欣慰的是,小額捐贈非但沒有被嫌棄,她還受邀作爲股東人蔘與騰訊公益滿天星項目的股東人大會。項目工作人員曾告訴她,說你即使捐一塊錢,也是對於這個項目的支持。
在互聯網公益出現以前,捐款幾乎成爲公益行爲的終點,籌款數額作爲最大的公益成果,“1元”捐贈者的話語權極小。而這也導致部分公益組織活動雖然搞了不少,服務人數也不少,但所服務人羣並未受益或改變,沒有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這實際上是浪費資源和捐贈人的愛心。
"我們的項目越透明,公衆捐贈越理性。"騰訊公益平臺負責人劉琴指出,“公衆捐贈越理性,就越容易養成持續關注和投入公益的習慣,對公益行業的好感度也就越高。”

做好行業“連接器”
騰訊公益探索“透明公益”深水區
伴隨公益數字化發展,捐贈只是故事的開端。騰訊公益平臺通過公益股東人大會、公益真探等項目,在透明公益的基礎上對“有效”展開積極探索。捐贈人有包括並不限於查看進展披露、參加股東人大會、參與公益真探實地考察項目等方式,進一步瞭解項目的情況。

騰訊公益通過設立“公益股東大會”的形式,爲公益項目帶來更直觀、更透明、更智能的公益反饋,參與項目的用戶每個人都具有主人翁精神,履行對項目的關注與推動義務,鼓勵機構呈現自身執行進度與透明。作爲“連接器”,騰訊公益將受助人、慈善組織、企業和公衆連接起來,推動行業可持續發展。
“瑕疵和挑戰都是前進的動力。”正如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祕書長葛燄表示,“我們鼓勵更多機構和網友加入進來,真誠溝通和行動,消解誤會和質疑,一起幫助項目更加有效地落地執行。”
滿天星公益已經開完第二場公益股東人大會。對比第一場,他們甚至大膽地增加了30分鐘的“自由答股東人”問環節。對於公益細節的暴曬,梁海光依舊坦蕩。“有問題及時改進就好了,人無完人,自然也沒有完美的機構。”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說:“朝向正確方向的嘗試,本身就值得讚許。”騰訊公益如此,滿天星等敢於召開股東人大會的機構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