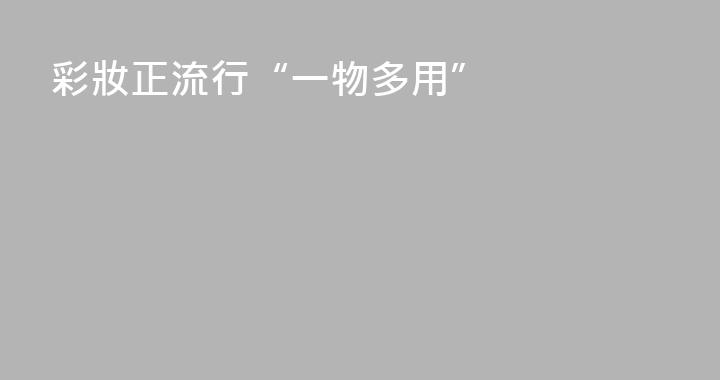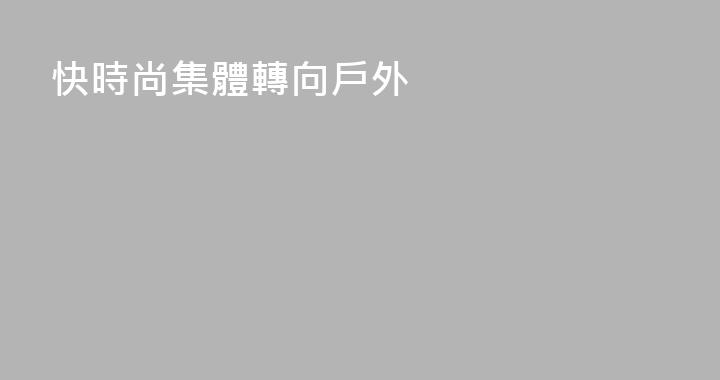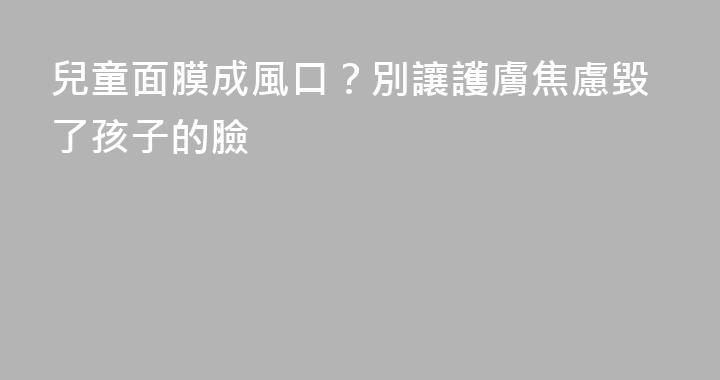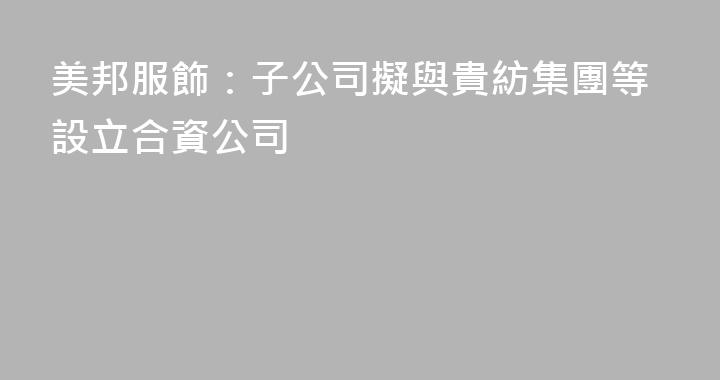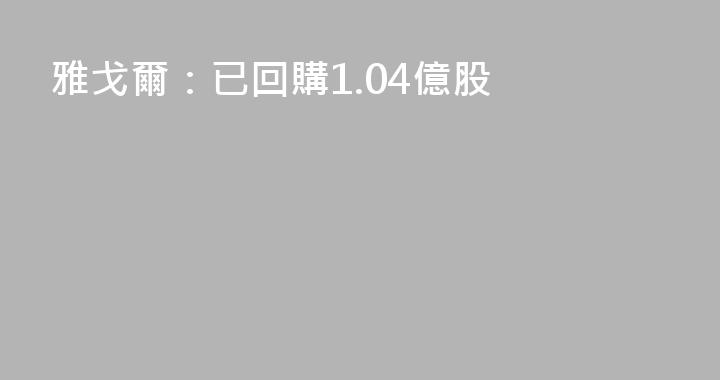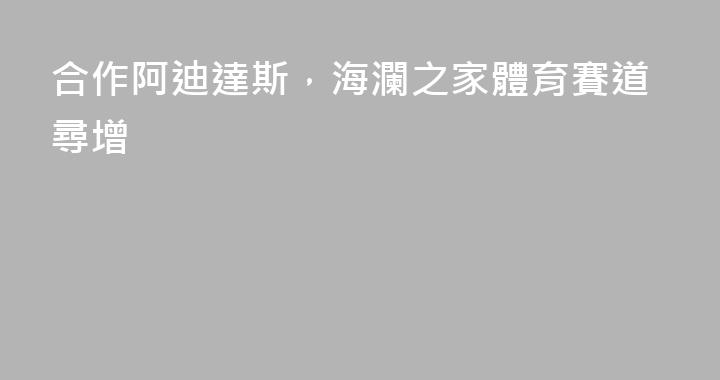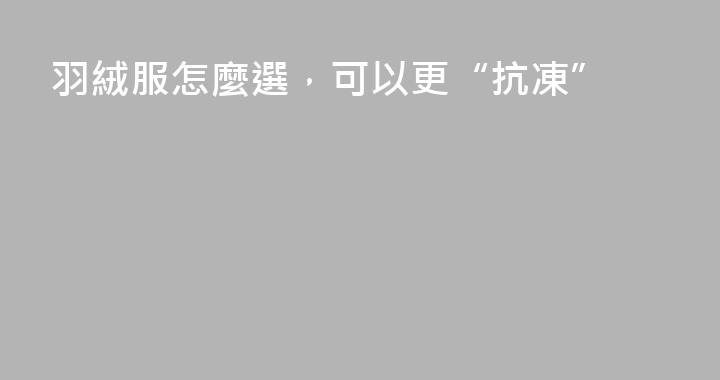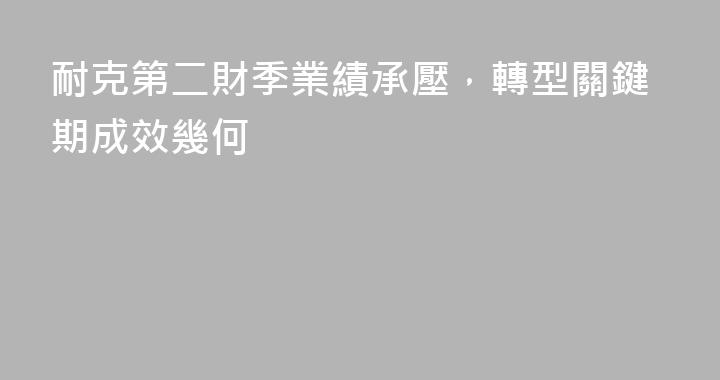作者:吳文科
對於“新大衆文藝”,除了鼓勵和包容,更要引導和拉昇,使其“大衆化”的實踐成爲提升大衆自己的“化大衆”旅程。
隨着網絡科技的迅猛發展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一種被稱爲“新大衆文藝”的文化現象倏然浮出水面並引發廣泛關注。
何爲“新大衆文藝”?雖未有着定於一尊的含義闡釋,但圍繞其所開展的討論,普遍認爲是新傳媒時代勞動大衆自發運用各種技術及媒介手段,自由參與創作並自主傳播和共享的文藝現象。所謂“新”者,一是創作主體爲普通大衆,且以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居多;二是表現內容鮮活多彩,題材廣泛、主題多樣、個性鮮明、貼近生活;三是呈現形態多樣靈活,比如短視頻、網絡小說、微短劇、才藝直播等,跨界融合、視角獨特、通俗直觀、不拘一格;四是傳播渠道以網絡爲主,即時互動、滾動黏合、橫向鋪展、共享交錯;五是創作姿態開放整合,創作、傳播、接受、評論一體兼顧,邊界模糊、互相映射、自發自主、自娛自樂。
不難看出,是技術的進步和傳媒的更迭,激發並賦予大衆自發參與和自覺涉獵文藝活動的熱情與機遇,也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給了普通勞動者“藝術地憩息”與“審美地生活”,更是寬鬆環境與自由氛圍提供給大衆審美創造和自我表達的土壤與陽光,從而也由一個側面,展示着當今中國人的全面發展。
對於新大衆文藝的湧現,歡呼喝彩自是必然,鼓勵肯定也理所當然。然而,關注的同時更要關心,引吭之外尤要引導。包括對其特徵、價值以及發展狀況的認知和看待,須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理性進行。
比如,觀念層面對新大衆文藝的描述,有兩組話語非常引人注目。一是“人人都能創作”及“人人都是藝術家”,或謂“人人皆可文藝”及“全民皆文藝”;二是“文藝就是生活”與“生活就是文藝”。這些頗具氣勢且令人振奮的表述,如果是對某種生活理想的詩性宣示,還可理解;若是將其作爲對於此等現象即“新大衆文藝”的發展認知與價值判斷,可能有所偏頗。其間的邏輯非常明顯:“人人都能創作”或“人人皆可文藝”即無所謂“創作”;如果“人人都是藝術家”或“全民皆文藝”,就沒有所謂“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人人都可創作表演,也不意味着“人人都是文藝家”;而“文藝就是生活”及“生活就是文藝”,同樣有泛化消解文藝的特殊價值並模糊消弭文藝的獨立地位之嫌,背離了“文藝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常識。而對新大衆文藝中“素人寫作”及其“草根氣息”的看重,包括因此帶來的由於沒有門檻且天花板較低的存在狀態與發展空間,也不能以“更平等”的文藝權利觀去看待。而像新大衆文藝中的某些創作及傳播運作,由於具有網絡傳播中商業操控背景下可能存在着的“飯圈文化”“精準推送”“信息繭房”等背景與套路,非但不是“大衆”的,恰恰具有十分鮮明和突出的“小衆”圈層與“分衆”特色。因而不可囫圇吞棗、籠統貼標。這進而警示我們:“人民大衆”的創作,不等於就是“人民文藝”。好比“寫什麼不重要,關鍵是怎樣寫”,由誰創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創作得怎麼樣。對於新大衆文藝內涵及品質的關切,纔是我們需要注重並用來衡量這一現象及其價值的核心與關鍵。同時也提醒我們:新大衆文藝的創造活力及所產生的積極成果,固然值得珍視和愛護,但其中存在的不足與問題,特別是侷限和偏頗,尤其值得思考和注意。
放眼當下某些新大衆文藝的創作實踐,不得不說,其中隱含的商業化趨向,使得許多短視頻及網絡直播節目,存在着內容浮淺、缺乏深度的短板;傳播過程中存在以“收割”用戶爲目標的情況,難免包藏着迎合甚或媚俗的弊端;一些標榜“草根”氣息的創作,不但不夠清新,還時常流露出粗鄙與草莽;有的網紅圈粉無數卻“蘿蔔快了不洗泥”,經常“泥沙俱下不客氣”;某些直播的低俗吆喝,停滯在“地攤式”的精神窪地,絲毫沒有跨越高原進軍高峯的理想與志氣。凡此種種,即便只是少數,也使新大衆文藝的創演,由於此類對情緒價值的簡單追逐,喪失着對思想價值的創造積累。而媒介化創作及網絡化傳播的便利,更加呼喚“內容爲王”的追求。許多人把“大衆文藝”定位於通俗性的審美範疇,實則“大衆文藝”是屬普及性的價值範疇。而文藝作爲精神食糧的基本屬性,要求新大衆文藝的“大衆化”創造,更要具備“化大衆”的資質與品格,亦即通過普及文藝而提高大衆。普及是手段,提高是目的。反觀新大衆文藝的場景,手段在不斷翻新,目標則道遠任重,需要激濁揚清、積極引領。在娛樂人和愉悅人的過程中塑造人並提高人,纔是使新大衆文藝健康發展而非野蠻生長的核心與根本。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