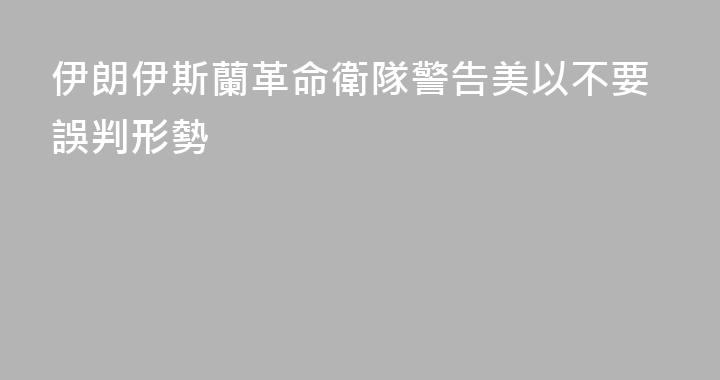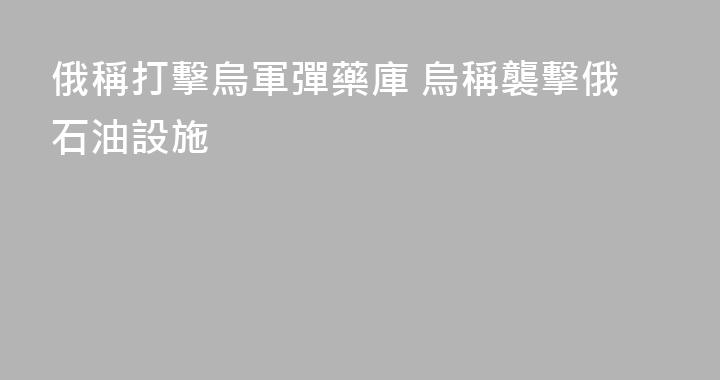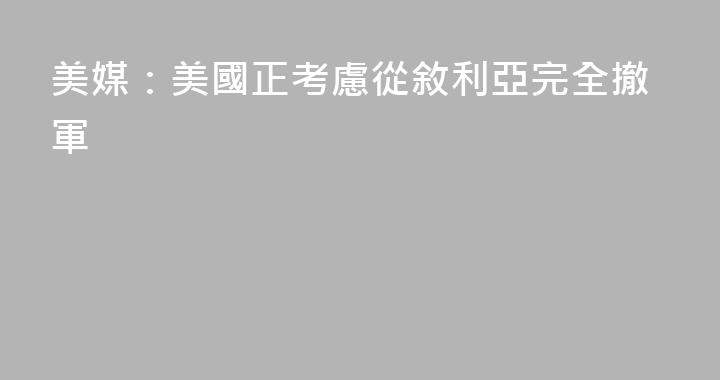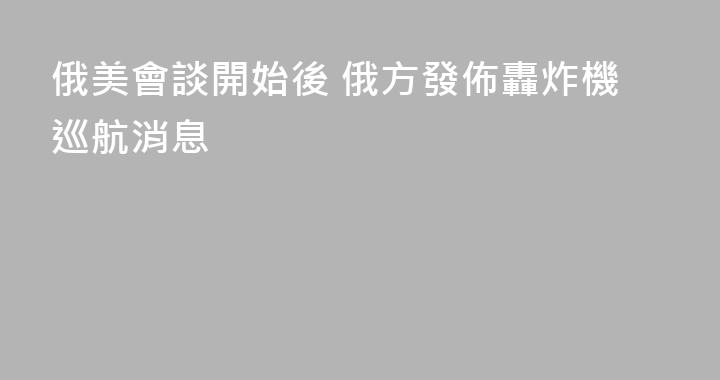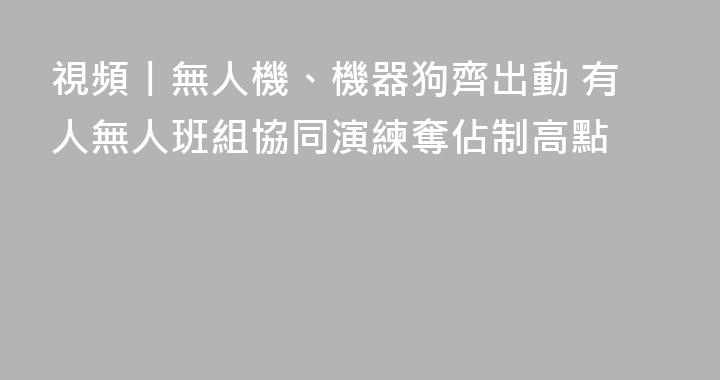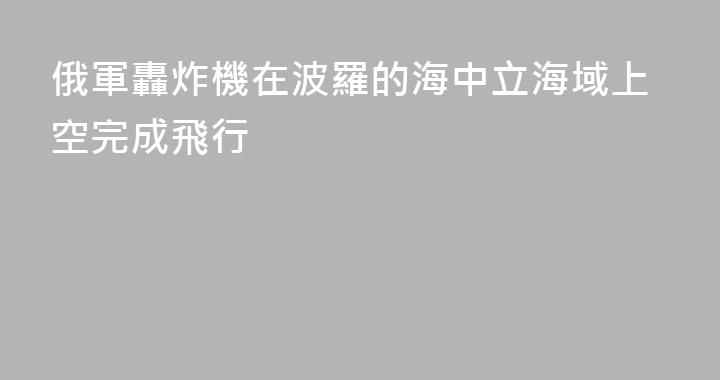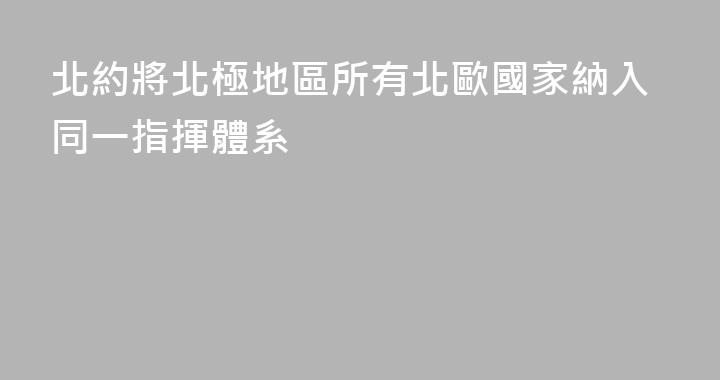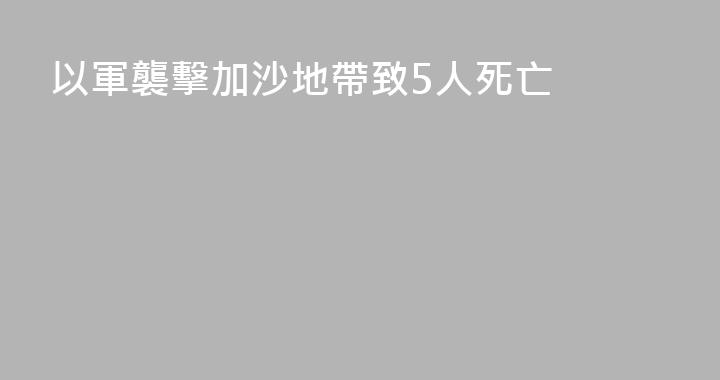原標題:一首大刀曲,一生報國情(尋訪)
“麥新”這個名字,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也許比較陌生,但在抗戰烽火中誕生的諸多響亮的戰歌中,由麥新作詞作曲的《大刀進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是從1937年傳唱至今、尤爲振聾發聵的一首。
孩子劇團,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個進步兒童戲劇團體,20多名只有十幾歲(最小的年齡才9歲)的小團員,穿越日寇封鎖線,歷盡艱苦,從上海到武漢,再到長沙、桂林、重慶等地,輾轉跋涉3000多里,用歌詠、演劇等形式宣傳抗日救亡,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同仇敵愾、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和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孩子劇團及其奮鬥故事,被文學家茅盾譽爲“抗戰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
我在爲創作長篇小說《孩子劇團》蒐集史料和素材時,意外發現音樂家麥新與孩子劇團多有交集。孩子劇團在上海成立時和千里跋涉到武漢後,麥新和冼星海、張曙等音樂家,都曾在街頭和碼頭,指揮和教唱過這羣熱血少年,演唱了不少抗日戰歌。
20世紀30年代,年輕的麥新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音樂運動,成爲革命音樂家冼星海的學生和戰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槍聲響起。當時,在長城腳下揮起大刀殺向日寇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的英勇壯舉,很快傳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大刀隊的戰士陳永德,一人一刀,殺敵9名,繳獲日軍槍支13支,而他的年齡只有19歲。每一個有民族尊嚴的中國人聞此消息,無不熱血沸騰。
23歲的麥新在上海看到這位19歲的大刀隊員的故事後,激動得徹夜難眠。臨近黎明時分,他索性從牀上爬起來,從書架上找出蕭紅的小說《生死場》讀了起來。不知不覺,一縷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個黎明到來了。這時,年輕的音樂家走到窗前,一把拉開窗簾,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是啊,中國人民從平津和華北的危急中,認清了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奮起抗戰,纔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抗戰的一天來到了!”麥新第二次重複這句話時,突然興奮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這就是後來人們都十分熟悉的“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這個復沓的樂句。
先是有了這句“抗戰的一天來到了”,麥新反覆哼唱了多次後,感到比較滿意,但又總覺得來得有點突兀。所以,稍微冷靜了一會兒,他又循着激越的情緒,構思出了開頭兩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他把這兩句和“抗戰的一天來到了”這個復沓樂句連貫起來又哼唱了多遍,最終確定了一個完整的樂段。
一個月後,8月8日這天,麥新去參加一個抗戰宣傳組織在南市文廟召開的羣衆集會。開會前,他站在文廟臺階上,一邊指揮,一邊教大家合唱這支戰歌。1000多名民衆齊聲高唱,唱了一遍又一遍,仍然覺得意猶未盡,現場羣情高漲。
這時後面有人高喊:“我們看不清指揮,請指揮先生再站高一點唄!”麥新應聲立刻跳到更高的一處臺子上,繼續指揮大家合唱。
根據民衆試唱效果和戰友們的建議,麥新把歌詞初稿裏的“二十九軍的弟兄們”這句歌詞改成了“全國武裝的弟兄們”,又把“咱們二十九軍不是孤軍”,改成了“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這樣一改,《大刀進行曲》就變成了一支號召和鼓舞全國抗日軍民奮起抗戰、血戰到底的戰歌,很快傳遍了抗日前線和後方。
又有一次,麥新在指揮羣衆合唱這支歌時,受到全場激昂情緒的感染,到了最後呼喊的時刻,因爲用力過猛,竟然把手中的指揮棒折成了兩截!此時此刻,音樂家胸中就像熊熊燃燒着一團烈焰,又似正在席捲起一場無法止息的風暴,那一瞬間,只見他迅速甩掉手中另一截指揮棒,握緊雙拳,奮力地指揮大家繼續演唱下去:“……看準那敵人,把他消滅,把他消滅!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經過多次集會合唱之後,不知從何時起,當大家唱到歌曲結尾也是整首歌的最高潮時,總是會齊聲加上一句高亢有力的呼喊:“衝啊——殺!”麥新明白,這一聲振聾發聵的吶喊,是全民族共同的憤怒的呼聲,也是振奮民族精神、爭取民族解放的慷慨激昂的號角。所以,音樂家自己漸漸也習慣和認同了結尾處那一聲凝聚着無限憤怒和力量的高亢的呼喊。
《大刀進行曲》誕生後,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知有多少抗日誌士和熱血青年,高唱着這首令人熱血沸騰的戰歌,奔赴抗日戰場最前線。
因爲創作的緣故,我希望詳細梳理《大刀進行曲》這首抗日戰歌的誕生過程。前年,我特意沿着麥新當年參加的“戰地服務隊”的路線走了一趟,從上海到浙江嘉興,再到江山、金華,然後經江西南昌、萍鄉到達湖北武漢。麥新和“戰地服務隊”在江山駐紮的時間比較長。正是在江山,我尋訪到了一條生動的史料。
1938年初春的一天,在江山縣城郊外一處小山坡上,面對着噴薄而出的一輪朝陽,24歲的麥新莊嚴地舉手宣誓,成爲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到達武漢後,麥新與從上海出發、輾轉千里到達武漢的孩子劇團的小團員們重逢。麥新把這些從敵人炮火中倖存下來的小弟弟、小妹妹,一一地緊緊摟抱在懷裏,和孩子們一起流下了歡欣的淚水。
1940年10月,麥新輾轉到達重慶,在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得到一個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黨組織批准了他多次提出想去延安的請求。
啊,延安!那是無數抗日誌士和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奔赴而去的革命聖地,也是麥新多年來心馳神往的地方。這年秋天,麥新穿上黨組織發給他的第一套灰色粗棉布軍服,戴上了嶄新的八路軍臂章,和幾位同志一道,從重慶到西安,再經過洛川,風塵僕僕地到達了黃土高原。在延安魯藝,麥新作爲一名革命文藝戰士,繼續投入到抗戰洪流之中。
麥新少年時,曾想過要到東北參加抗日義勇軍。後來,在科爾沁草原上,他對一起在開魯縣參加土改的戰友說:“少年時就想來東北的願望總算實現了。”不幸的是,1947年6月的一天,他在開完縣委會,騎馬返回五區途中,遭遇了一股殘匪的突然襲擊。在經過一番英勇搏鬥後,麥新等4名同志壯烈犧牲。
麥新犧牲的地方,是在科爾沁草原上,開魯縣西拉木倫河西劉祥營子以南,一處名叫蘆家段的沼澤地邊緣。幾年前,我陪作家熊召政到東北和內蒙古草原尋訪和蒐集歷史素材時,到過這裏。當時,站在波濤滾滾的西拉木倫河邊,我的眼前瞬間閃過音樂家麥新死不瞑目地倒在血泊裏,鮮血汩汩流淌的一幕,心裏頭真是難受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