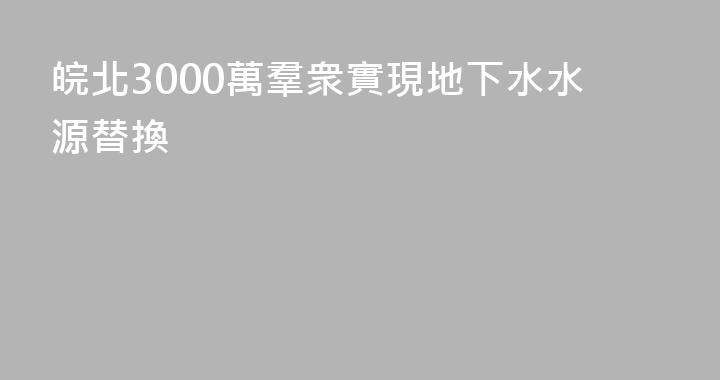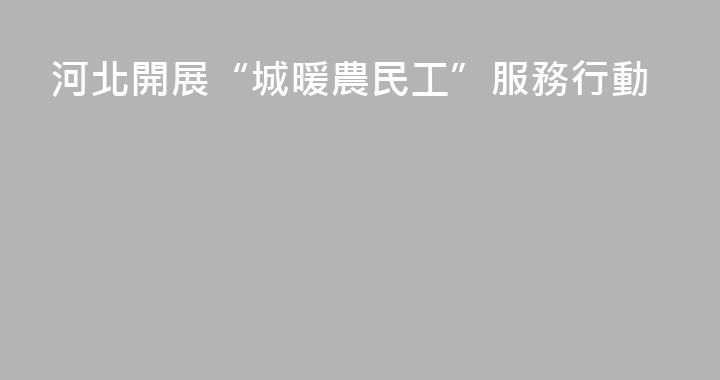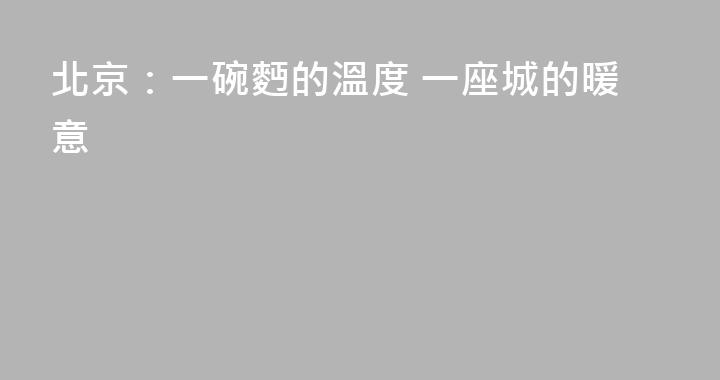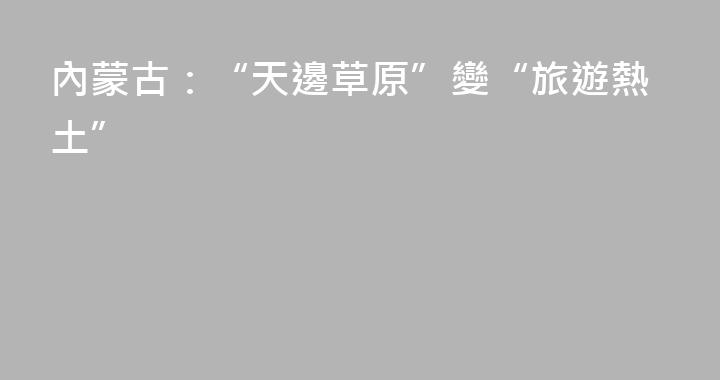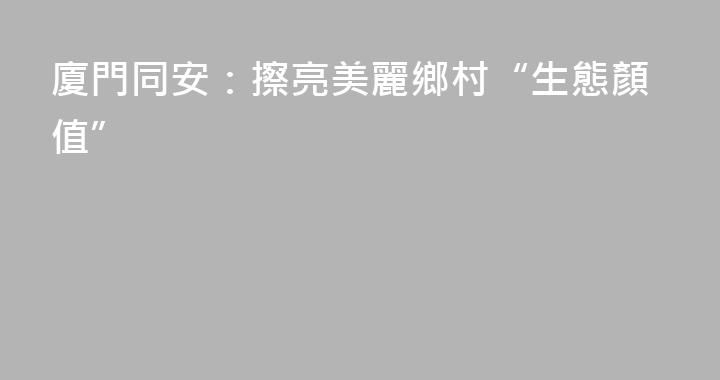無論是“寒窗苦讀”努力實現大學夢想的莘莘學子,還是即將告別象牙塔邁入社會的準“職場萌新”,青少年正處在快速變化的階段,身心逐步成熟的同時,也面臨着個體認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社會認同的多重考驗。也正因此,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更加凸顯,抑鬱、焦慮等成爲不可忽視的風險。
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門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將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5月25日“全國大中學生心理健康日”來臨之際,對於怎樣看待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正確對待抑鬱症治療,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劉薇教授給出了相關呼籲與建議。

誘因:學生羣體易陷入“高度內耗”
今年21歲的林葉(化名)已是一名大學二年級學生,但她關於“高考”的噩夢似乎在過去的幾年間從未離開。3年前,她因家庭變故和備考壓力等原因患上抑鬱症。“那是一段至暗的記憶。”林葉感到自己被一切消極情緒纏繞着,“寫不出習題怎麼辦?睡不好怎麼辦?影響考試怎麼辦?高考失利怎麼辦……”林葉控制不住地感到悲傷,時常不自覺地哭泣。儘管在接受藥物治療後,她堅持完成高考,但成績卻受病情影響並不理想。
像林葉這樣的學生羣體並不在少數。中科院心理所發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在採集的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在內的逾19萬份總樣本中,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成年人樣本6859份後,結果發現,抑鬱風險檢出率爲10.6%,其中青年爲抑鬱的高風險羣體,18-24歲年齡組的抑鬱風險檢出率達24.1%;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2022年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則顯示,大約21.48%的大學生可能存在抑鬱風險,45.28%的大學生可能存在焦慮風險。
“當前,隨着經濟快速發展、轉型,社會上往往強調競爭和績效,而學生羣體也過早地被這種模式裹挾,正如人們常說的‘贏在起跑線’、‘從娃娃抓起’。這種壓力對於身心還處於成長期的大中學生羣體來說,往往是抑鬱風險的誘因之一。”劉薇教授對於青少年羣體的高抑鬱風險進行原因分析,“外界壓力還只是一個方面,青少年抑鬱症發病原因複雜,還可能因爲青少年的神經系統處在生長髮育期,抗壓能力比較弱。另外,青少年激素水平波動較大,比如女生面臨的每個月例假引起的經前緊張,男生的第二性徵發育等。”
識別:關注情緒、認知行爲等多維度信號
針對青少年羣體中頗爲嚴峻的抑鬱風險問題,劉薇教授指出,“早預防、早治療是抗抑鬱的關鍵。家長、老師應多關注青少年情緒、認知、行爲和生理層面的變化,這些變化能夠提示病情的發生與發展。如果孩子原本較爲開朗,最近卻變得比較孤僻,可能是情緒出現問題。還有認知層面,比如孩子在人際交往中變得自卑,特別介意別人的看法等。此外,孩子突然失眠,暴飲暴食、厭食、厭學等行爲問題,以及疲勞、頭疼、腹瀉、肌肉疼等生理層面的問題,可能也是情緒問題的早期徵兆。”
劉薇教授特別強調,部分患者和家長對疾病的認知存在誤區,家長覺得孩子只是學習壓力大、心情不好,想開了就行了,不可能是抑鬱症;而罹患抑鬱症的孩子往往陷入“誰也救不了我”的狀態,失去治療的動力,再加上家長的忽略,有些孩子甚至會自傷、輕生。因此,正確認識抑鬱症、儘早尋找專業治療至關重要。
治療:殘留症狀是社會功能恢復的“攔路虎”
針對抑鬱症治療,國內外權威指南均強調以“獲得臨牀治癒、減少復發風險、改善功能損害、提高生活質量”爲目標,但臨牀研究發現,仍有不少患者在經過抗抑鬱藥物治療後,會伴隨出現快感缺失、動力不足、疲勞、認知損害等殘留症狀,僅有1/3的患者完全緩解,而殘留症狀不僅是患者復發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嚴重阻礙了患者社會功能恢復到病前水平,影響其生活質量。
“林葉在治療後,便有部分症狀殘留”。據劉薇教授瞭解,林葉在三年前首次確診抑鬱症時,已接受過相關藥物治療,服藥後雖然悲傷情緒有所改善,不再無故哭泣,但同樣也感受不到開心,整體情緒從原先的“傷感”變得“無感”,且依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學習成績也因病情受到很大影響。這反映其依舊有快感缺失、認知障礙等殘留症狀,即無法從外界獲得正向反饋,其內心也沒有動力去恢復正常的學習和生活。升入大學後,在心理誘因的刺激下,林葉的抑鬱症再次復發。
結合林葉的病情狀況,劉薇教授選擇了去年剛上市的若欣林(鹽酸託魯地文拉法辛緩釋片)爲其治療。臨牀研究顯示,若欣林能夠全面地緩解抑鬱症患者不同維度症狀,顯著改善常見的殘留症狀,比如焦慮狀態、阻滯或疲勞症狀、快感缺失和認知能力等;其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也有助於患者用藥依從性的提升,更有利於其全病程規範治療。
當前公認的單胺假說認爲,5-羥色胺(5-HT)、去甲腎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三個遞質通道活性降低導致抑鬱症的發生,且三大遞質系統的紊亂會通過影響不同的腦區導致不同的抑鬱症狀表現。大多抗抑鬱藥僅對5-HT和NE兩個遞質有效,但對DA的干預較少,而DA往往與正向情感、動力快感、認知等呈現相關性。臨牀前研究表明,若欣林對於5-HT、NE和DA均具有再攝取抑制作用。
劉薇分析表示,“我們把抑鬱症狀分成負性情緒和正性情緒,患者除了消極、沮喪、哭泣、悲傷等負性情緒的增加,還有快樂、動力等正性情緒的減少,後者就與DA相關。林葉首次治療後出現正性情緒減少,同時還有注意力集中困難等殘留症狀,提示大腦的認知功能受到了影響,若欣林恰好能填補這些未滿足需求。”
據介紹,林葉使用若欣林一段時間後,情緒改善明顯,逐漸開始感受到開心的情緒,並從外界感知到正向反饋,也不再因爲高考失利鬱鬱寡歡、自怨自艾,而是開始採取積極的行動,備戰考研,有信心通過實際行動去改變現狀。
在劉薇教授看來,殘留症狀是阻礙患者恢復正常社會功能的“攔路虎”。抑鬱症患者的症狀表現因人而異、“千人千面”,因此,重視患者多維度症狀的全面緩解,減少殘留症狀對正常學習和生活的負面影響,顯得尤爲重要。
劉薇教授同時呼籲,社會各方重視與關注、對疾病認知的加深、診療理念的進步、創新藥物的出現,正在爲青少年患者的治癒帶來更多希望。“我們期望孩子和家長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朝着我們共同的目標努力——讓孩子真正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