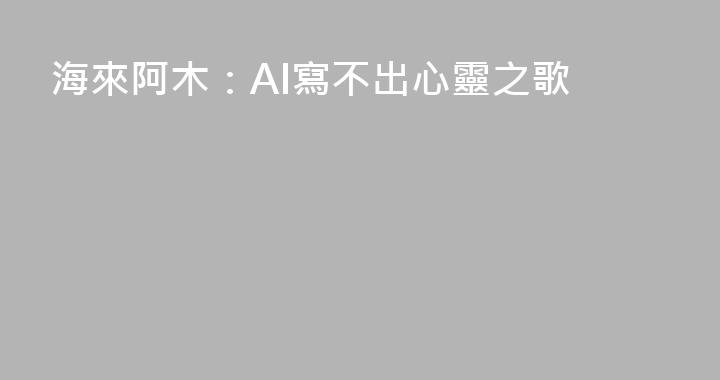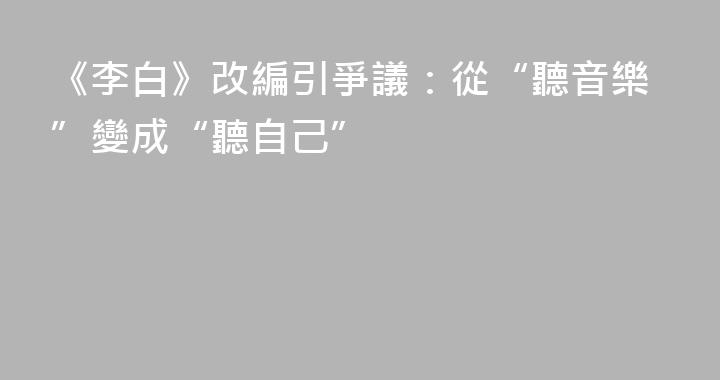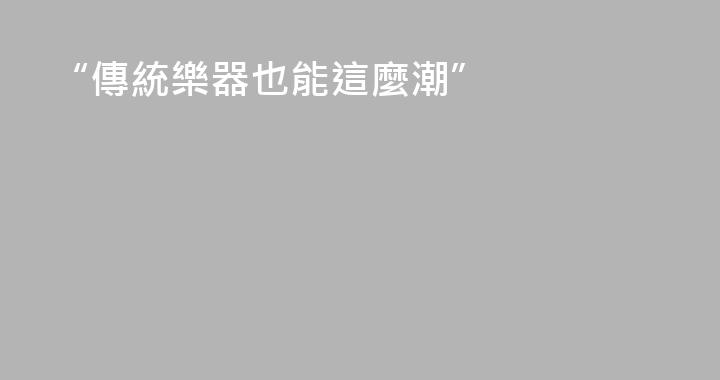觀點提要
爲了適應不同媒介受衆的需求,文學的影視改編往往需要進行類型與價值表述的調整。這種以市場觀衆爲導向的求新求變固然可取,但應立足於對類型敘事背後的世界觀構架、價值觀底色的深入理解與研究。因爲類型敘事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慣例、敘事模式、情節結構和人物關係,真正具有穩定性的類型總是以人類共通的價值理念和普遍的心理感受爲基礎,並與人們當下生活中的困惑和問題息息相關。
《卿卿日常》開播之初,以其女性價值話題與類型顛覆贏得高熱度高口碑的雙重火爆,甚至刷新了平臺熱度值“破萬”的最快紀錄。但在其後半程,類型顛覆中的雜糅混搭帶來難以自洽的價值表述的曖昧與混亂,也帶來熱度的降低與口碑的下滑。
事實上,像《卿卿日常》這樣以女性價值觀的凸顯與劇情的反常規設置爲內容“賣點”,已成近期網劇求新求變的一種方式,比如此前也極具話題度的《夢華錄》《蒼蘭訣》等。這些劇所共同面臨的口碑熱度隨劇情進展而下滑的情況,深層次暴露內容創新背後價值銜接的難題:類型的雜糅與顛覆能否真正解決類型敘事背後潛在價值觀底色與新價值觀之間的有效統一?
從文類角度來看,網絡小說是一種類型化敘事,比如玄幻修仙、種田宅鬥、宮鬥穿越等等。這些類型小說在網絡文學發展過程中逐漸成型,形成較爲固定的敘述模式,擁有相對穩定的讀者羣體。類型敘事不僅僅只是一種講故事的方式的差異,其背後實質上潛藏着特定的觀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並以此形成相應的價值觀“應答”視野,以回應人們對世界的困惑與苦惱。
正如著名電影理論家和影評人路易斯·賈內梯曾指出的那樣,“當運用一個衆所周知的故事形態來創作時,創作者可抓住其主要特色,然後在類型的傳統和個人的創新間、耳熟能詳和原創思維間、一般和特定間創造出無比的張力。神話蘊涵了文明共通的理想和嚮往,而藝術家依循這些熟知的故事創作,成爲縮短已知與未知間距離的精神探索者。這些風格化的傳統和原型故事鼓勵觀衆參與有關當代的基本信念、恐懼和焦慮的儀式。”好萊塢電影類型的權威研究者托馬斯·沙茲也認爲,“製片廠對標準化技巧和故事公式——確立的成規系統的依靠,並不僅是物質方面經濟化的手段,而且還是對觀衆集體價值和信仰的應答的手段。”而這也正是流行文化的類型敘事往往被視爲“世俗神話”的原因。因而,類型敘事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慣例、敘事模式、情節結構和人物關係,真正具有穩定性的類型總是以人類共通的價值理念和普遍的心理感受爲基礎,並與人們當下生活中的困惑和問題息息相關。比如宮鬥文的後宮爭鬥不僅指涉宮廷權謀與險惡的歷史,更映射當下職場“內卷”與焦慮;玄幻升級文則普遍性地蘊含着社會階層躍升過程中“逆襲”的集體夢想。
爲了適應不同媒介受衆的需求,文學的影視改編往往需要進行類型與價值表述的調整:或者爲了更好地擴大受衆以“破圈”,比如《贅婿》試圖從男性讀者向女性觀衆拓展而強行塞入迎合女性新價值觀以滿足受衆的需求;又或者爲了適應時下觀衆審美需要而改變固有類型敘事的模式,比如《卿卿日常》將原小說主體的宮鬥模式修改爲甜寵與經營相雜糅的類型搭配,以避免觀衆的審美疲勞。這種以市場觀衆爲導向的求新求變固然可取,但由於對類型敘事背後的世界觀構架、價值觀底色缺乏深入理解與研究,而急功近利地強求類型的混搭、價值觀的附會與話題的拼湊,則最終導致價值表述的混亂。如果說《贅婿》的網劇改編病在敘事邏輯的內在割裂與快感模式的難以統一,那麼《卿卿日常》的問題在於敘事模式轉換背後的價值衝突的無法調和。
劇集採取了原網絡小說《清穿日常》的人物關係與敘事的主導線索,但將小說中以清朝四爺雍正奪取皇位的歷史背景予以架空,並將後宮女子的權謀鬥爭進行極大顛覆。代之以架空的新川所主導的九川政治聯盟爲背景,通過八川向新川進貢選秀女子爲起點,在政治聯盟格局、少主權力競爭的弱化線索下,以李薇如何從側夫人最終成爲正主夫人爲中心情節。劇集重點呈現以李薇與六少主爲主導的情感故事以及李薇等女子之間的“姐們情誼”與獨立自主爭取個人命運的故事。
從創新的層面上看,《卿卿日常》是宮鬥權謀類型的顛覆、甜寵類型的融入與種田經營類型的拼貼所混合而成的輕鬆喜劇。一方面,劇集顛覆了原本宮鬥權謀類型中,權力的冷冰冰與後宮女子之間的明爭暗鬥,而着力塑造“李薇們”所帶來的溫暖與陽光:她們不僅溫暖了後宮女子之間的關係,化釋了橫亙在親子之間的誤會,也將宮廷權力的冰冷轉化爲世俗家庭的父慈子孝。另一方面,劇集通過對政治聯姻的抗爭、女子經商權力的爭取以及女子之間的互助團結,以種田經營的類型融入來表達一種當代女性的新價值觀:追求愛情的獨立與女性事業的擁有。然而,無論是對宮廷關係的溫暖還是對事業獨立的追求,《卿卿日常》的核心其實是愛情中心的甜寵劇套路:從李薇試圖從被安排的選秀落選、到無奈接受被安排的婚姻而盼丈夫死亡以還鄉、再到元英到來但因爲真愛而接受作爲側夫人的身份、再到最終與六少主終成正果的過程,這種先結婚後相愛的敘述模式,以及其細節呈現的愛情滋長,乃至於處處展現出來的“單純的小美好”,實際上都是甜寵劇固有的敘事模式。也因此,這種甜寵劇中所固有的價值模式——因爲真愛而願意接受現狀,以甜膩的撒糖場面來掩蓋婚姻安排的不合理,更願意接受固有婚配,儘管標榜追求一夫一妻,不納妾的愛情與婚姻的價值觀,實際上是與劇集中試圖去強調的女子追求不依附於男性、擁有獨立事業並藉助互助的姐妹情誼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價值觀構成了衝突,甚至可以說甜寵劇的價值框架消解了這種價值觀。不獨《卿卿日常》如此,根據關漢卿元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改編的《夢華錄》,其根本問題也在於其整體上的“才子佳人”式敘事與現代女性價值觀的衝突。
與《親愛的小孩》《我在他鄉挺好的》《三悅有了新工作》等現實題材女性網劇所具有的情感深度和現實困境的表達不同,近年來以女性爲導向的古裝網劇似乎都走上一種架空的“情感烏托邦”的走向:試圖以女性新價值觀滿足觀衆的“爽感”慾望,又以甜膩的情感實現對女性觀衆“確幸”慾望的滿足。這正是甜寵作爲一種“通約性”敘事框架以雜糅其他類型的甜寵劇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然而,無論古裝網劇如何架空歷史,其構設的敘事時空、權力結構與人物關係仍然是建立在傳統社會的基礎之上。因而,就比現實題材的甜寵劇更突出地暴露出甜寵模式、女性新價值觀與傳統權力關係之間難以自洽的價值衝突:以女性新價值觀所建立起來的“爽感”以及美好甜蜜的“確幸”在一個傳統權力關係的敘述背景中,是無法相容的。這正是包括《夢華錄》《卿卿日常》在內的女性古裝網劇難以避免的口碑走落的命運。在這一意義上,表達後宮權鬥陰冷入木三分的《步步驚心》《甄嬛傳》,呈現後宮女子無奈命運淒涼的《如懿傳》因爲其邏輯與價值的自洽,才真正成爲具有一定深度的女性古裝劇。
(鄭煥釗 作者爲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