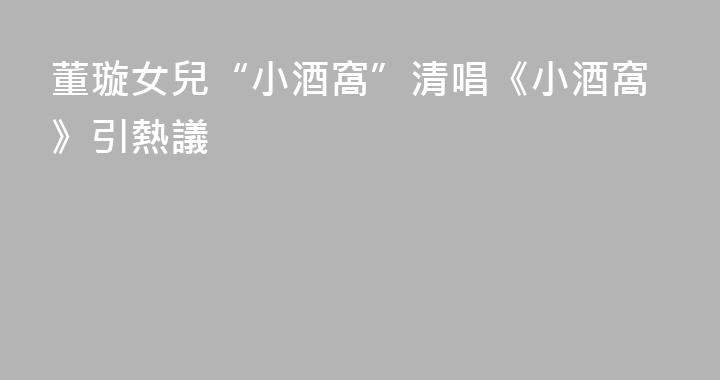■《縣委大院》創作者堅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條:深入生活,紮根人民。
一
央視一套等各大平臺熱播的電視劇《縣委大院》,堪稱一部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精品力作。
說它貫穿始終的是徹底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指其直面光明縣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奮進實踐,真實地、藝術地展現其由落後貧窮、經濟滯後、環境治理不達標、政績數字上報造假、拆遷釘子戶橫設障礙、羣衆上訪不斷、招商困難重重等局面,到在新的縣委班子帶領下知難而上,團結奮戰,勇毅前行,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五位一體”方略,終於出色地踐行了“在國家治理中居於重要地位”的縣一級基層政權所肩負的使命。
該劇既直麪人生、揭示矛盾,因而具有了現實主義的深度、廣度、力度;又開拓未來、展現光明,因而具有了浪漫主義情懷應有的溫度。兩者交融整合,便鑄就了《縣委大院》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藝術品格與美學風貌。
二
正如劇名《縣委大院》所標示,全劇聚焦中國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基石——縣一級基層政權的治縣理政實踐,以光明縣新任縣長梅曉歌爲主視角,向觀衆呈現了急需修復與發展的光明縣,如何從“老大難”現狀中一步步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人說它是一部社會政治劇,這並沒有錯;但我贊同李京盛所言,中國特色的社會政治劇孕育於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而西方的社會政治劇產生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兩者是迥異的。前者的鮮明特色是執政爲民,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爲中心;後者如《紙牌屋》《白宮風雲》等則往往重在表現上層人物的“政治運作”和“權力角逐”,以爭權奪利爲宗旨。嚴格區分這一點,至關緊要。
三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縣委大院》的創作給我們帶來的寶貴啓示。
毋庸諱言,此前把鏡頭主要對準縣一級基層政權的電視劇也不少,但爲何《縣委大院》更有深度、廣度、力度和溫度呢?
這裏面一個重要緣由,便是創作者對標的出發點是什麼。一些創作者是以西方類型片原理和藝術構思框架爲出發點的,而《縣委大院》的創作者是嚴格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出發的,是從生活出發的。不是說,西方類型片理論不能學習借鑑;而是說,西方類型片理論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生活生長出來的,我們只能學習借鑑其中符合中國國情的有用的東西,而萬勿套用西方理論去闡釋和導引中國人的審美創造實踐。
《縣委大院》創作者堅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條:深入生活,紮根人民。創作者把光明縣的改革開放置於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下,把生活當成整體來進行審美把握,不是按西方類型片常見的裁割生活一事貫穿,而是全景式地把執政興縣、城鄉保護、環境治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一攬子盡收眼底,予以審美表現。唯其如此,該劇具有此前同類題材作品罕有的生活厚重感、真實感,既接地氣,又撼人心。
“堅持從生活出發,把生活當成整體把握。”這是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我的導師、已故著名文藝評論家朱寨先生,力排衆議舉薦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時的名言。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觀《縣委大院》,倍覺親切、中肯。
四
《縣委大院》在審美觀照生活上,強調整體性、強調全面辯證地處理好生活化與戲劇化關係的“度”。顯然,它主要不是靠事件的戲劇衝突來吸引觀衆,而是靠事件的“平實組裝”來形象展現中國式現代化在光明縣的歷史進程。與此相關,它在塑造縣委、縣政府班子各具典型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時,也自覺地摒棄了過去曾一度長期制約我們的二元對立、非好即壞、不左就右的單向創作思維模式,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辯證取捨的和諧思維方式。
縣委班子裏,雖人人性格各別、境界有異,但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奮進實踐中,都能做到忙是常事、苦是必然、累是應該、樂是自得。劇中人物從梅曉歌到艾鮮枝,再到呂青山等,大家團結共事,既正視困難又勇於作爲,既忠誠乾淨又擔當重任,既奮發進取又不踩紅線。全劇形象地彰顯了這樣一種新時代新幹部的執政理念,殊爲可貴。正是在這種辯證和諧的創作思維導引下,梅曉歌的藝術形象脫盡了“高大全”氣,雖受命於危難之際,但仍低調上任,以與同行的市委組織部領導對話中引出的“破釜沉舟”“貶官出官”略表情志、潛藏深意。上任後,由縣長而升任縣委書記,對人與事,他力戒主觀判斷輕下結論,尤其不作“非對即錯”的簡單處理。這一形象,在新時代擔當時代重任的新人的藝術畫廊裏,有着一席重要位置和獨特價值。
(仲呈祥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首屆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