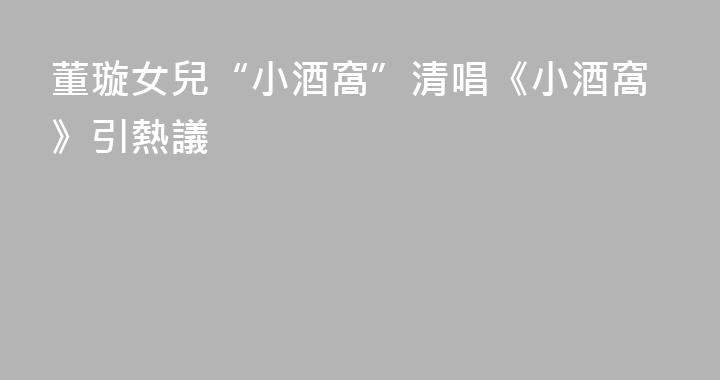滬劇多流傳於上海及周邊地區,雖“偏安一隅”,卻不乏優秀的滬劇影視作品,如《蘆蕩火種》《羅漢錢》《璇子》等。
近年來滬劇除了發揚傳統劇目,更立足當下,創作出一批優秀的富有新時代特色的作品,其中滬劇實景電影《敦煌女兒》令人驚豔,其作爲地方劇種結合影像媒介進行了紮實而創新的藝術探索。
影片以滬劇舞臺劇《敦煌女兒》爲藍本,以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爲原型,真實細膩地展現了以樊錦詩爲代表的幾代敦煌人紮根大漠,爲守護莫高窟而無悔青春、奉獻終身的故事。影片由滕俊傑導演,茅善玉主演,舞臺劇原班人馬共同完成。創作團隊深入甘肅敦煌實景拍攝,將劇場藝術轉化爲影像藝術,化程式爲影像,從而呈現出新的藝術生命,並榮獲第35屆金雞獎最佳戲曲片獎。
《敦煌女兒》在滬劇舞臺上已打磨10年,無論從劇本、唱腔到表演都已很成熟,被翻拍成電影,若僅按傳統舞臺藝術記錄爲主,應很容易完成。但導演的創作欲求不止於此。導演滕俊傑近年來一直深耕於戲曲電影創作,遵循他“尊古不泥古,創新不失宗”的原則,每一部作品都力求有所突破。
70餘年前,費穆導演爲梅蘭芳大師拍攝第一部彩色戲曲電影《生死恨》,兩位藝術家對於戲曲搬上銀幕如何既能保留傳統程式,又符合電影審美有過探討,最後形成“佈景爲實,表演爲虛”的融合,兩位藝術家的偉大合作開啓了程式與影像融合的創舉。在影像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敦煌女兒》更是虛實並舉,將程式、影像與數字科技有機結合,運用電影語言彰顯戲曲的審美優勢,走向戲曲電影歷史與美學的新境界,也是傳統藝術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有力實踐。
虛實互鑑
舞臺寫意與影像寫實融合
戲曲講究“寫意”,電影重在“寫實”,在戲曲電影創作中,兩者一直在磨合、博弈。戲曲三大家之一齊如山曾言,程式需“處處事事都要摩空,最忌像真,尤不許真物上臺”。滬劇是上海本土劇種,儘管以“西裝旗袍”戲的現實風格爲主,程式規範不似京昆那麼繁複,也吸收了文明戲和話劇的表演方式,但角色依然分不同行當,表演以唱、念、做、舞的傳統程式爲基礎。
滬劇《敦煌女兒》的舞臺設計秉承傳統戲曲的簡單寫意風格,運用了三面盒狀結構的門框,色調和線條都較爲簡約,隨着劇情的發展而變換燈光和背景,形成洞窟甚至洞房。電影則是在甘肅敦煌進行實景拍攝,茫茫大漠和皇皇莫高窟帶給觀衆的視覺衝擊和感染力,是舞臺寫意風格所無法承載的。
法國電影符號學家麥茨曾雲:電影首先是空間的藝術,而後纔是時間的藝術。舞臺空間,觀衆與舞臺的距離是固定的,而電影則可以通過景別、蒙太奇、鏡頭運動等表現方式使觀衆擺脫“正廳前排視點”,沉浸在影像空間裏。比如影片開場,剛從北大畢業的樊錦詩坐着馬車穿越沙漠,一路風沙拂面,在舞臺上只能靠演員的唱詞、身段和音效等,以寫意方式激發觀衆的想象力完成敘事;而在銀幕上,大漠孤煙、黃沙漫天,讓觀衆能切實感受敦煌惡劣的氣候環境,直接產生共情。
成功的戲曲電影不僅能充分利用光影,更會讓戲曲程式的寫意在影像的寫實中找到恰當的表達,不是消減程式,而是把程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敦煌女兒》的“三擊掌”,無論在戲曲舞臺上還是在電影中都是重場戲:年輕的樊錦詩初到敦煌,憑着初生牛犢的衝勁兒與當時的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打賭,用“三擊掌”來表達自己紮根敦煌的決心。在舞臺空間,“三擊掌”是“前景一點實,後景層層虛”的表達,樊錦詩與常書鴻以線條椅爲道具,觀衆欣賞集中在唱腔、身段等程式化表演;而在電影中“三擊掌”發生在莫高窟前,後景是現實的洞窟和敦煌特有的蜈蚣梯,比舞臺更富有感染力。同時,爲避免演員唱段延緩整體的節奏,導演把部分唱段改成唸白,以全景爲主,演員調度也呼應舞臺空間的表達,既不消減程式,又符合電影的敘事節奏。然後鏡頭推近至常書鴻的近景,展現他從半信半疑到逐漸被打動的神情變化。最後兩個人的手部特寫形成“三擊掌”段落有力的結尾。本段視聽語言駕馭嫺熟,把舞臺的“虛”和影像的“實”巧妙融合,更細膩、真實地表達人物複雜的情緒,大大提升和豐富了整段的衝突性和藝術感染力。
境生象外
影像的詩意表達
自《周易》起中國傳統美學就探討“意象”與“意境”關係,意象與現實貼近,意境則是作品精神世界的表達,意境產生於意象而又超越於意象。相較於舞臺,敦煌的現實意象,通過鏡頭語言更凸顯出其特別的意蘊。
在敦煌工作3年後,樊錦詩終於和丈夫彭金章團聚並進行了簡單樸素的婚禮。此段表現二人對未來方向的抉擇,是重要的情感段落。舞臺上,演員們通過多段唱腔來表達人物內心的掙扎,情感表達較爲直白;而電影中隱去了部分唱段,增添了許多生活場景的調度,加深人物與環境的聯結,同時用環境的物象來表達角色情感,比直白地唱和念更富有韻味和詩意。
導演運用平行蒙太奇手法表達新婚夫婦彼此的躊躇:樊錦詩邊洗碗邊回憶丈夫爲自己的付出,狠心在請調書上籤了字;彭金章在雨中徘徊許久,回房看到熟睡的妻子依然緊抱着《敦煌七講》,不忍她如此痛苦,便撕掉請調書。最後鏡頭拉開,夫妻二人在前景並肩相抱,望着後景窗外的一輪圓月。整場戲鏡頭語言簡潔流暢,演員細膩的表演通過景別轉換表現得恰到好處,手中的《敦煌七講》、房間內一對紅燭以及窗外細雨、明月等細節,不僅是影像敘事的元素,更是在意象之外體現意境,“境生象外”的影像詩意令觀衆意猶未盡。
影片不僅有詩意的實景表達,更用數字影像把敦煌通過現代的、科技感的方式靈動地表現出來。《敦煌女兒》在莫高窟實景拍攝,離不開對窟內藝術瑰寶的展現,但由於現場環境的特殊性以及文物保護等多方面的限制,爲將具有重要意義的敦煌壁畫靈動又有生機地表現出來,影片運用CG技術讓壁畫裏的人物都“活”了起來,給傳統戲曲帶來嶄新的視覺形態。考慮到滬劇藝術原本的程式結構和審美特性,影片中CG技術的應用主要在黑暗夜晚、荒漠洞窟等具有較高寫意性的時空表達裏。例如,樊錦詩初到敦煌的那晚,她主動申請留在守夜的小屋裏,條件的簡陋、老鼠的肆虐讓這個來自大城市的姑娘內心產生動搖。“鼓起勇氣打開手電把黑夜面紗輕撩起,眼朦朧似見到衆聖千佛來匯齊。一邊,神祕的佛陀漾起那禪定笑容;另一邊,美麗的飛天架起五彩雲霓,一顆心瞬間有靠依。”此處不僅以人物的唱段表現樊錦詩的執着,畫面也疊化出洞窟內鮮豔的壁畫,壁畫上的人物漸漸舞動起來,佛像也立體起來,真的是“衆聖千佛來匯齊”。CG打破虛與實的界限,以數字技術的“虛擬”帶給觀衆影像的“真實”,將世界性的藝術瑰寶活生生地展現給觀衆,觀衆和樊錦詩一起感受到敦煌的強大力量,爲“萬里敦煌道”賦予鮮活的、科技的光華。
在這片光華中,最耀眼的無疑是影片貫穿始終的意象符號——禪定佛陀。
立象盡意
人物有形,而氣韻無盡
禪定佛像是莫高窟第259窟、始塑於北魏的佛像,“這尊坐佛長眉細眼,身披圓領通肩袈裟,衣褶紋理生動流暢。佛像雙腿盤坐,兩手交握,自然地收於腹前,神情莊重,沉靜甜美,彷彿全然進入了一個美妙的世界”。禪定佛陀寶相莊嚴,是影片承擔“起承轉合”和人物成長的敘事符號,也是樊錦詩本人境界的映射,也許更是茅善玉塑造人物時所依照的“心象”之一。
焦菊隱先生曾指出“演員在創作時,要從外到內,再從內到外,先培植出一個心象……沒有心象就沒有形象”。一般說來,人物傳記電影追求外形貼近人物,通過特型化裝使演員儘量靠近人物。茅善玉的外形和樊錦詩不甚相似,舞臺上可以不求現實的真實,而一旦被搬上銀幕,對戲曲演員的考驗非常大。
茅善玉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滬劇的代表性傳承人,多次影視劇拍攝經歷使她對鏡頭前表演並不陌生。她在電影中結合程式和現實兩種表演方式,以唱段和臺詞、表情結合,弱化身段,融合情緒體驗,不求外形復刻,但求神情與氣韻一致。
由於實景拍攝,如何克服惡劣拍攝環境,將樊錦詩真實的生活狀態以影像的方式表現出來,同時又融合戲曲的表演程式,這是茅善玉要解決的重點問題。她在創作舞臺劇期間曾9次帶領主創團隊到敦煌深入生活,與樊錦詩本人也成了忘年交。這對演員來說,是對人物非常重要的“抓型”(鄭君里語,指演員以真人爲模特)的過程,爲其之後完成電影表演打下了非常紮實的基礎。
在塑造少女時代的樊錦詩時,爲體現人物的朝氣和衝勁,茅善玉以戲曲程式的肢體表演爲主,特別是在洞窟前的“三擊掌”一段,年輕的樊錦詩表達紮根敦煌的決心,攀蜈蚣梯、甩髮辮、三擊掌等一連串優美利落的肢體呈現,都融入戲曲刀馬旦的身段步法,符合人物積極明快的性格底色。
在塑造爲人母之後的樊錦詩時,茅善玉則以細膩的現實主義表演風格爲主。當彭金章到敦煌探親,發現樊錦詩忙於工作而把不滿週歲的兒子綁在牀上時,發生了夫妻倆少有的一次爭吵。這場戲也是兩人感情線索的重場戲,導演以樊錦詩簡陋的宿舍爲單一場景,在鏡頭內形成類舞臺的空間,場面調度和舞臺劇同段落相比也較簡潔,因此茅善玉以眼神、表情等爲主,身段、唱腔等程式爲輔。例如她被丈夫責怪時的委屈,看着兒子哭鬧的心疼等,茅善玉都通過眼神表情來表達這些細膩複雜的情感,細節處理完全是現實生活而非戲曲舞臺上的母親所爲。
這樣既符合人物步入中年的沉穩,也提升了該段落內部敘事的衝突性和節奏感,符合電影的審美要求。
演員塑造人物是一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回到實踐的過程,不僅僅是簡單的形象、肢體和行動的模仿,更要塑造人物心理、情感乃至整個精神層面。演員要越過自身的第一自我,從第二自我的深處挖掘此人物且只屬於此人物的精神生活,這樣才能塑造不單薄、有靈魂的角色。樊錦詩身上最難能可貴的是一種質樸高貴、剛柔並濟的氣質。這也許是樊錦詩的本性,更應是日日面對禪定佛陀而達到的澄懷觀道境界。茅善玉最成功之處,便是表達了樊錦詩的這種獨一無二的氣質。
影片開始時,耄耋之年的主人公緩緩步入熟悉的洞窟。畫面是大逆光,茅善玉從光影中走來,洞窟外的陽光映襯着她瘦弱的身影,如同萬丈佛光襯托的禪定佛像。在這片光影中,茅善玉氣定神閒地開唱,回憶堅守莫高窟一路走來的風雨艱辛。大道至簡,此刻演員沒有過多的調度、臺詞和表情,眼神和氣質卻最與樊錦詩相似,不是因爲化裝造型,而是茅善玉表達出的淡定、從容和寧靜的神韻。
當影片進入尾聲時又首尾呼應,鏡頭再一次展現了壯觀的敦煌全景。茅善玉扮演的老年樊錦詩信步走在棧道上俯視着茫茫莫高窟,鏡頭閃回了一連串她在洞窟內外工作的場景。茅善玉撫今追昔,開唱《敦煌女兒》的主題曲。隨後她來到莫高窟九層樓前,轉身背對鏡頭仰望高樓;伴隨着悠揚清澈的風鈴聲,人物緩緩疊化轉身——恰是現實中的樊錦詩。
現實中的樊錦詩面對鏡頭,眺望遠方,如同禪定佛陀展露清雅的笑容,透射出她清淨超凡的氣韻。
這一刻,表演與現實融爲一體,虛虛實實,萬象歸一,影像的瞬間在銀幕上凝固,唯有畫外風鈴聲飄蕩,韻味深長。
著名導演桑弧在拍攝彩色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時,按電影審美,結合實景與繪景,重組戲曲敘事。該片在20世紀50年代以當時的技術展現戲曲影像的魅力,但由於題材和技術的侷限,仍以“歌與舞”的舞臺記錄爲主。在媒介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戲曲藝術是否能形成新時代的創新性審美?電影《敦煌女兒》以現實題材戲曲結合敦煌實景,成功地把敘事節奏、空間調度與程式表演向影像審美轉化,展現戲曲在跨越媒介後更強的藝術感染力,是傳統藝術的創新性審美,也是弘揚民族文化自信的影像實踐。
(沈嘉熠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