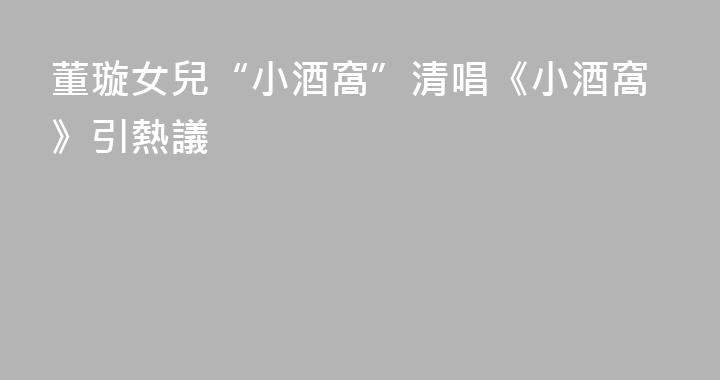核心閱讀
有時候,演員們一天要到3個村子演出,不是爲了趕場,而是要搶時間,怕那些望眼欲穿的村民白白期待。
走到晉西北,必看二人臺。走到晉東南,必聽大鼓書。爲適應觀衆口味,山西省曲藝團培養出自己的編劇和導演,每個人都是一專多能。
他們的節目與時俱進,在市民中也有不錯口碑,城市的口碑又反哺了鄉村的需求。多角度的嘗試,讓他們越來越找得準觀衆的喜好。
田野阡陌間,與草木和嘉禾同時流動着這樣一羣人——他們熟悉鄉間的氣息,也瞭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無論寒冬酷暑,他們千里奔行在路上,克服種種困難,也要把文藝演出送到鄉村去、送到老鄉的家門前。
他們就是山西省曲藝團的演員們。
曲藝與戲曲同源。在戲曲大省山西,道情、蓮花落、鼓書、相聲、小品、快板、數來寶等曲藝活躍在鄉間,與山西衆多戲曲劇種一樣,有着巨大的文化空間和肥沃的生存土壤。山西省曲藝團成立於1959年6月,包含有相聲、小品、快板、二人臺、太原蓮花落、快書、大同數來寶、潞安鼓書等10餘個曲種,在全國性的曲藝比賽中多次獲獎。
山西省曲藝團的“家底”來自上世紀80年代的一輪創業。現任團長王兆麟1984年進入曲藝團。他說:“從那時起,我們經常下基層,自己打行李捲鋪蓋,自己做飯,住旅店。人們愛聽愛看,我們的演出有了市場,打下了羣衆基礎。”
這10年來,他們一方面積極尋求市場,一方面承擔“送戲下鄉”的任務。曲藝在三晉大地的鄉村田野找到了自己的天空。
只要有觀衆的地方,他們就要去演出。只要羊能上去,他們就能走到
有人開玩笑說,曲藝演員下鄉,帶一張嘴就行。確實,對於山西省曲藝團來說,下鄉演出可大可小,可化整爲零,機動性極強,能走到大型團體走不到的山莊窩鋪去。
只要有觀衆的地方,他們就要去演出。只要羊能上去,他們就能走到。
2017年冬,他們到山西臨汾大寧縣儀裏村演出。走在路上,雪越下越大,路越來越難行,大巴車陷在泥裏,所有演員只能下去推車,在陡峭的山路上輾轉3個多小時後,才趕到儀裏村。一進村口,他們的眼睛就溼潤了,數百名鄉親站成兩排,女人手裏捧着大棗、煮雞蛋、山核桃,男人手裏提着熱水,走近了,鄉親們熱情地往演員手裏塞着這些“好喫的”。所有路途上的辛勞瞬間都被融化了。
在鄉下演出,是沒有舞臺的,找到一塊空地,有觀衆,就可以演。他們不需要漂亮的服裝,冬天穿着軍大衣,夏天來不及換衣服,就穿着自己的服裝上場。
“扶貧攻堅曲藝老區行”活動來到呂梁市興縣郭家峁村。這一年,風雪特別大。他們一到達,先幫村民們打掃開一塊場地。村幹部說:“天太冷了,雪又大,你們穿得這麼少,要不少演一點吧!”演員說:“只要村民喜歡,我們就演。你們在臺下一個多小時都不怕冷,我們就更不怕了!”一位93歲的老奶奶坐着輪椅、冒着大雪看演出,一邊看一邊鼓掌。主持人楊帆趕忙將老奶奶請到舞臺側面,讓老人避開大雪。演出結束後,鄉親們又把他們送了很遠很遠。
有時候,演員們一天要到3個村子演出,不是爲了趕場,而是要搶時間,怕那些望眼欲穿的村民白白期待。能爭取多演一點,就多演一點,即便是人少的村莊、高溫中施工的工地,也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身影。
幾個月連續演出的情況很常見,經常是在上午演出的村裏喫碗麪或者燴菜饅頭,緊接着就出發去下一個村。這樣高強度的演出,只能喫住睡都在車上,大巴車就成了他們最溫暖的家。
最近這5年,他們演遍了深山裏的700個村子,行程幾萬公里。哪怕受疫情影響的這三年,他們也走過了200多個村子。今年山西省總工會的“三送三進”慰問中,他們的足跡遍佈11個市、60個縣,爲3萬多工人演出,讓歡笑播灑在城鄉。
在節目上花心思,用曲藝最擅長的方式,弘揚正能量,倡導移風易俗
走得遠,還要讓觀衆覺得節目舒心好看,山西省曲藝團沒少花心思。
到鄉下去,常演的有10多個節目。數來寶《賣土豆》、長子鼓書《小米縣長》、快板歌舞《打響脫貧攻堅戰》、二人臺《南瓜情》……都是用曲藝最擅長的方式,弘揚正能量,諷刺陳規陋習,倡導移風易俗。
相聲《懶漢劉二狗》最受村民歡迎。“劉二狗”是一個不願自己努力、只想依靠政府救濟的懶漢。節目以搞笑逗樂的對白,傳遞了扶貧先扶志的理念。當裹着軍綠色舊棉襖、兩隻手插在袖筒裏、縮着脖子吸溜着鼻涕的“劉二狗”出現在臺上,大笑不止的村民們說:“好,演得好!我們就是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不能像那個懶人劉二狗,就是國家再幫你,自己不努力,那也是白費哇!”
舞臺劇《棗花》既適合鄉村也適合城市,組合起來就是一個舞臺劇,拆開就是幾個小品,演的是呂梁護工棗花走進城市,依靠政府支持、社會關愛和勤勞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此劇由曲藝團自編自導自演,一口氣演進了北京。
舞臺劇《初心之路》真實鮮活地再現了一個個高尚的靈魂。從第一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王荷波,到山西早期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傑出領導人鄧國棟,再到太行英雄左權將軍、解放戰爭中的人民英雄霍桂花……很多觀衆流着淚看完《初心之路》,感慨說:“這是真正的震撼人心和精神洗禮。”
王兆麟和馬曉紅用山西方言朗誦的《再別康橋》雅俗共賞,成了金牌節目。山西方言多而繁雜,晉西北的人愛聽晉北話,晉東南的人愛聽晉東南話,這個節目裏什麼都有,幾乎演遍了全省。他們的數來寶日日更新、鼓書與時俱進;與同路人合作的“好悅來”相聲小劇場,在市民中也有不錯口碑,城市的口碑又反哺了鄉村的需求。多角度的嘗試,讓他們越來越找得準觀衆的喜好。
“網紅”姚崇善,是太原蓮花落傳承人。太原蓮花落起源於清道光年間,用太原方言說唱故事,流行於太原、晉中、呂梁地區,一個人打着竹板即可以說唱。這個90後小夥子從小學晉劇,並得到了晉劇名家的指點,卻在某一天迷上了蓮花落。這一迷,小姚就把已故蓮花落藝術家曹強的段子全學會了,又被團長王兆麟一眼看中,調入山西省曲藝團,專攻曲藝。2020年,小姚不想與喜歡他的鄉親們離得太遠,就開通了網絡演出,並關掉了打賞功能。這一舉動,爲小姚贏得了幾十萬的粉絲,更爲蓮花落贏得了更多的受衆。
他們的故事和素材多來自鄉間,再經過藝術轉化和加工,就有了更加蓬勃的生命
耿麟在山西省曲藝團供職15年。2018年,他參加東方衛視《相聲有新人》節目,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八強,在鄉村也有了幾分名氣。在長治武鄉魏家窯村,找他拍照的鄉親排成了長隊。耿麟卻一如既往、平平淡淡。他明白,光環是暫時的,相聲就是民間藝術,只有植根生活,纔能有蓬勃的生命力。
池銀壽是二人臺演員。二人臺是流行於晉陝蒙冀等地區的戲曲小劇種。60歲的池銀壽從14歲開始唱二人臺,從內蒙古唱到山西,直到在山西省曲藝團紮下根來。他堅守着二人臺的原汁原味,並將鄉親們的方言俚語融進表演。《南瓜情》《土豆開花》《幸福全覆蓋》等節目演下來,村民們見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喜愛的明星。如今,池銀壽最操心的是二人臺的傳承。除了團裏的兩個年輕人,他還有幾十個徒弟在演二人臺。他說,只有這樣,有一天他老了,演不動了,纔能有人把二人臺傳下去。
走到晉西北,必看二人臺。走到晉東南,必聽大鼓書。爲適應觀衆口味,山西省曲藝團培養出自己的編劇和導演:王永剛是編劇,也是相聲演員;王兆麟既是團長,也是導演;張畯是導演,又是主持,也演小品……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專多能。他們的故事和素材多來自鄉間,再經過藝術轉化和加工,就有了更加蓬勃的生命。《懶漢劉二狗》《土豆開花》《棗花》等節目,都是這樣取材並打磨出來的。
只要多日不見面,就有村民給王兆麟打電話:“老王啊,多會兒來我們村哪?”“快了,快了。”曲藝團的演職人員常接到這樣的電話,也都會這樣回答。
田野阡陌和尋常巷陌間,曲藝的芬芳就這樣流動着。 (王 芳 圖片均由山西省曲藝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