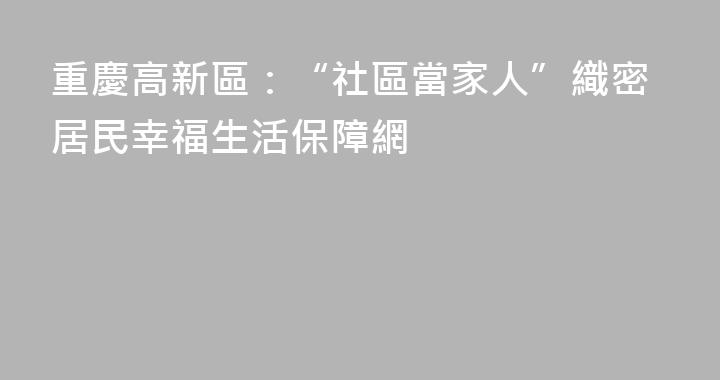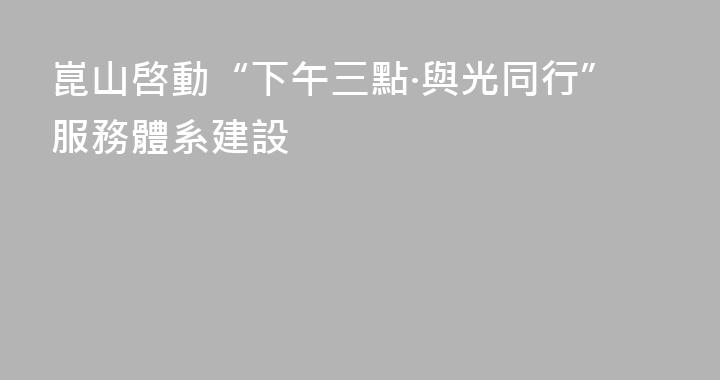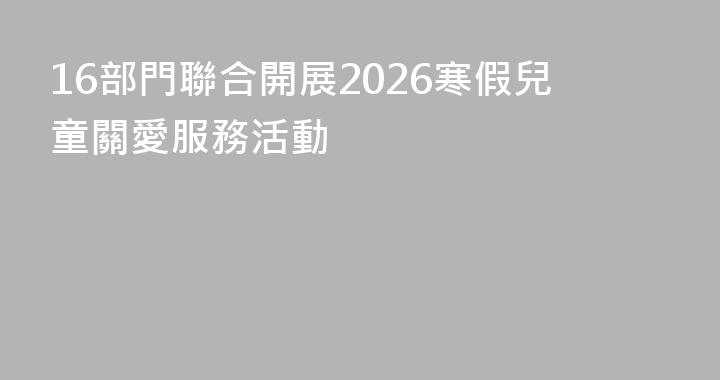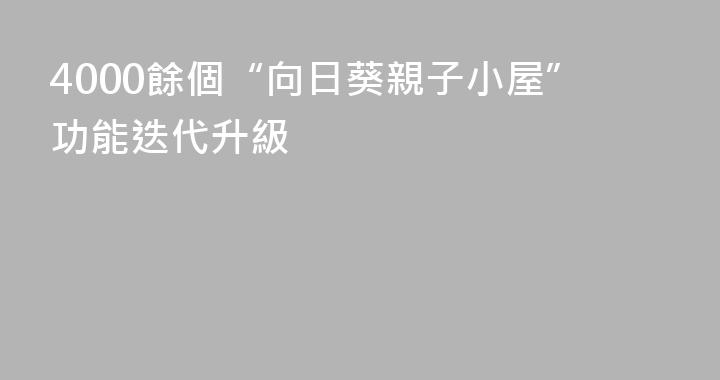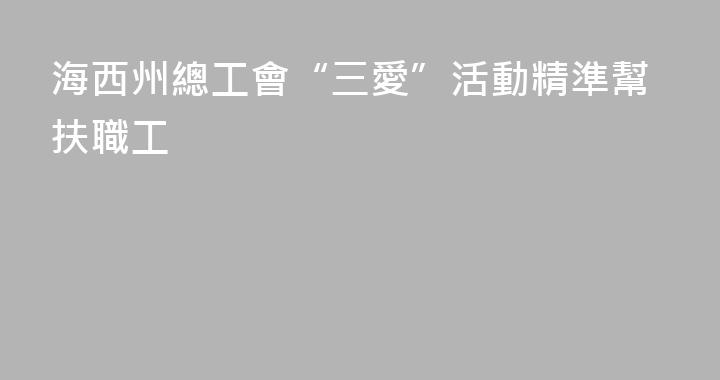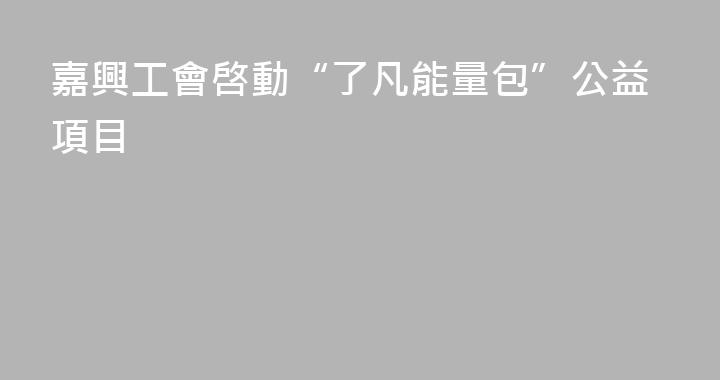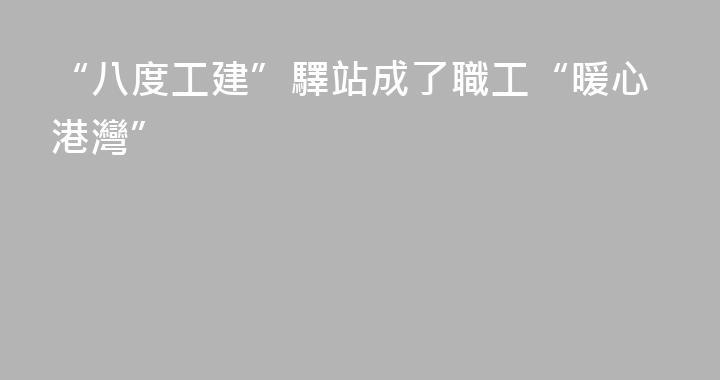圖①:巧家五針松果實。
陶 戀攝
圖②:雲南梧桐花朵。
楊 靜攝
圖③:華蓋木花朵。
孫衛邦攝
圖④:西疇青岡幼果序。
陳智發攝
圖⑤:漾濞槭花果。
陶麗丹攝
圖⑥:研究人員在野外調查同色兜蘭。
蔡 磊攝
圖⑦:滇桐組培苗。
羅桂芬攝
核心閱讀
隨着我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上的持續發力,一個新概念走進大衆視野——“極小種羣野生植物”。這些脆弱的野生植物,極具經濟、科學、生態價值,但種羣和個體數量極少。
近年來,雲南積極推進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目前已有華蓋木、漾濞槭等30多種擺脫了滅絕威脅。
一種植物在野外被發現時,如果只剩下數十株甚至不到10株,是否還具有保護的價值?
對於植物學家來說,答案是肯定的。這些物種背後的保護故事,與“極小種羣”這個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
尋找、保護、引種、繁育、迴歸自然……10多年的艱苦努力下,雲南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初見成效——最初在野外發現僅有6株的野生華蓋木,如今恢復至1.5萬餘株;全世界僅存30餘株野生植株的巧家五針松,通過人工繁育累計獲得近萬株幼苗;野外已滅絕的富民枳,在原產地重建了種羣……截至目前,雲南已有華蓋木、漾濞槭、巧家五針松和雲南藍果樹等30多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擺脫了滅絕威脅。
今年初,雲南3部門印發《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拯救保護規劃(2021—2030年)》,將101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物種列爲保護對象,並提出目標:實現所有名錄物種種羣數量穩定或增長,改善生境質量,確保免於滅絕,最終形成一套基本完善的拯救保護體系。
探索——
珍稀瀕危的“綠色金礦”急需搶救性保護
通直的樹幹,婆娑的枝葉,飽滿的松果透出棕色光澤。
這是巧家五針松,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也是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上世紀90年代首次在野外被發現時,僅存34株野生植株。
2021年8月,巧家五針松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園內實現了首次結實,標誌着這個物種遷地保護的初步成功。爲了這一天,科研人員已足足等待12年。
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不只巧家五針松,遷地保護後木本植物開花結實都需要很長時間——華蓋木30年,漾濞槭8年,西疇青岡13年……植物物種的保護,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辛勞與堅持。
雲南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之一,也是野生物種受威脅嚴重的地區。這裏的珍稀瀕危植物面臨着共同的困境:在自然界裏分佈地域狹窄,受外界因素干擾,種羣及個體數量都極少,已低於最小可存活種羣而隨時瀕臨滅絕。
爲了拯救這些物種,2005年雲南提出了“野生動植物極小種羣保護”的倡議,並於2010年出臺了雲南省極小種羣物種拯救保護規劃綱要和緊急行動計劃。
2012年,原國家林業局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全國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拯救保護工程規劃(2011—2015年)》,將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拯救保護工作推向全國。
“一個物種就是一個基因庫。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是大自然中極爲寶貴的基因資源,猶如潛在的‘綠色金礦’。”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綜合保護重點實驗室主任孫衛邦說,拯救保護極小種羣野生植物,就是保護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生物資源,對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
十多年來,孫衛邦率領團隊一直致力於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概念的推動和發展、系統性研究與搶救性保護行動,先後完成多個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的保護研究。
保護——
每個物種背後都有一個保護計劃
金沙江畔,山巒起伏。
喫過早飯後,老肖提着鐮刀早早地出了門。老肖全名叫肖體進,是元謀縣江邊鄉沙溝箐村的一名護林員。江邊哪條箐、哪個山頭上長着什麼樣的樹,老肖如數家珍。
烈日炎炎,山路難行,沿着乾熱河谷山側的砂石陡坡,老肖仔細地巡護着。山間巖縫中的幾株小樹,每次都會讓老肖駐足留意。樹幹亭亭玉立,枝頭吐出嫩綠的新葉,樹梢上的紫紅色花穗閃着光澤。這,就是被最新版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名錄收錄的雲南梧桐。
由於數量稀少、生境惡劣,雲南梧桐面臨着極其嚴峻的保護形勢。上世紀末,雲南梧桐的野生植株已幾乎絕跡。直到2017年,孫衛邦率領團隊開展野外調查,意外發現了野生雲南梧桐的蹤跡,其中一處便位於江邊鄉小山崖巖縫的薄壤中,發現時僅有十來棵植株存活。
2021年9月,科研機構和地方林草等部門在江邊鄉建立了雲南省第一個雲南梧桐就地保護點,還向村民和護林員們贈送了人工繁育的雲南梧桐幼苗。
現場見證全程的老肖和周邊村民一起,參與到保護雲南梧桐的行動中,巡山時總會多留意這些樹苗的生長,幾乎變成了守護雲南梧桐的“活地圖”。
和雲南梧桐一樣,每一個列在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名錄中的物種背後都有一個保護計劃。孫衛邦介紹,針對不同植物物種的資源特點,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已形成了就地保護、近地保護、遷地保護、種質庫種質資源保存、種羣增強和迴歸等多種保護方式結合的綜合保護體系。
昆明植物園極小種羣野生植物專類園內,壯麗含笑、華蓋木、富民枳、漾濞槭等具有代表性的極小種羣野生植物在此安家。身爲昆明植物園主任的孫衛邦,一有時間就往這個專類園跑。他告訴我們,園內每一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的開花結實,都意味着又有一種植物的滅絕風險正逐漸降低。
從2015年始建至今,昆明植物園遷地保護了86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成爲十分重要的遷地保護基地。近日,昆明植物園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育溫室建成投入使用,將重點收集保育不能在露天進行栽培,原產熱帶、南亞熱帶和需要高溫高溼環境條件的極小種羣野生植物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
雲南省林業和草原科學院研究員楊文忠介紹,10多年來,雲南省實施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拯救保護項目120多個。截至目前,雲南省已建立30個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小區(點)、13個近地和遷地基地(園)、5個物種迴歸實驗基地,共遷地保護極小種羣野生植物61種10萬餘株、迴歸定植16種3萬餘株。
利用——
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利用的鏈條
雲南梧桐樹形優美,樹冠亭亭如蓋,觀賞價值非常高。專家告訴記者,雲南梧桐的果實可爲本土動物提供食物,種子可食用、入藥、榨油;還耐旱耐貧瘠,是乾熱河谷綠化造林的最佳先鋒樹種之一。
可是,單一的保護模式並不足以解決雲南梧桐的瀕危困境。爲了探索新的保護路徑,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羅桂芬對雲南梧桐進行了組織培養技術攻關。將雲南梧桐幼嫩的頂芽或側芽作爲外植體,接種至培養基中,通過誘導、分化、增殖與生根一系列培養,最後進行瓶苗移栽,就得到了雲南梧桐植株。
將高大的樹木放進瓶子裏,聽上去似乎不可思議。此前,羅桂芬在華蓋木的組培上已經實現了成功突破,開啓了組織培養快繁技術在極小種羣喬木中成功應用的先例。
“多一種技術儲備,就意味着多了一分保存物種的希望。”羅桂芬的組織培養實驗室裏,保存着不同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的組培苗。“組培成苗比自然播種容易,對於保存和擴大像雲南梧桐這樣的喬木種羣,意義重大。”羅桂芬說,這也爲將來該物種的引種馴化、保存、園林園藝及其科研價值的發揮利用提供路徑。
可持續利用,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的保護。在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中,有不少像蒜頭果、紅河橙、祿勸花葉重樓、胡黃連、姜狀三七和雲南金花茶等具有藥用或觀賞價值的物種,有巨大的開發利用潛力。
富含“神經酸”的蒜頭果,具有輔助人類神經吸收營養和修復的功效,2012年被列爲《雲南省極小種羣物種拯救保護緊急行動計劃》重點保護對象。雲南省林草科學院油茶研究所通過多年技術攻關,使蒜頭果移栽成活率達85%以上,現年可量化培育蒜頭果苗木200萬株。
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利用的鏈條,實現“在保護中利用,在利用中保護”,蒜頭果如今在廣南實現迴歸種植2.4萬餘畝,成立產業聯合總社,不僅擺脫瀕危狀態,還成爲名副其實的致富果。
未來——
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迎來新發展階段
2022年2月,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科普基地落戶昆明市西華公園,這也成爲全國首家參與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探索和科普展示的城市公園。在這裏,市民可以近距離觀賞到華蓋木、巧家五針松等15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
走出深山,走近百姓,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正逐漸爲人熟知。“與城市公園合作共建保護科普基地,提升公衆參與度,讓極小種羣的科普工作更加常態化、社會化。”孫衛邦說,爲了讓更多的人蔘與到保護中來,科研人員想了很多辦法。
爲了幫助滇桐引種迴歸,2017年,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林草局和江東鄉林業站的幫助下,孫衛邦團隊徵集江東鄉當地志願者,由志願者認領了150株滇桐幼苗,並栽培到自家的承包地中。這種迴歸模式激發了當地民衆對滇桐的關注和保護熱情。
從2005年雲南省率先提出概念至今,拯救保護極小種羣物種正在成爲社會共識,也得到國際植物保護生物領域廣泛關注。當前,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基本理論、保護模式和實踐經驗已被多國應用於其本土植物保護。
在全面評估基礎上,雲南省對前期規劃名錄進行了重大調整,形成《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名錄(2022年版)》,並對保護本省的極小種羣野生植物提出新的十年規劃,雲南省極小種羣野生植物保護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在最新名錄中,共收錄101種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物種,與2010年的老版62種相比,有40種被撤出,同時新增了79種。讓專家們高興的是,華蓋木、巧家五針松、蒜頭果等10餘種物種因拯救保護成效明顯而被調整出了新名單。
據介紹,未來雲南省計劃在滇西北、滇東南等不同的生物地理區內建立“極小種羣野生植物專類園”,開展種質資源調查、收集、保存、繁育等工作,並開展極小種羣野生植物的遷地和近地種羣構建、野生種羣的恢復與重建。
本期統籌:崔楊臻
版式設計: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