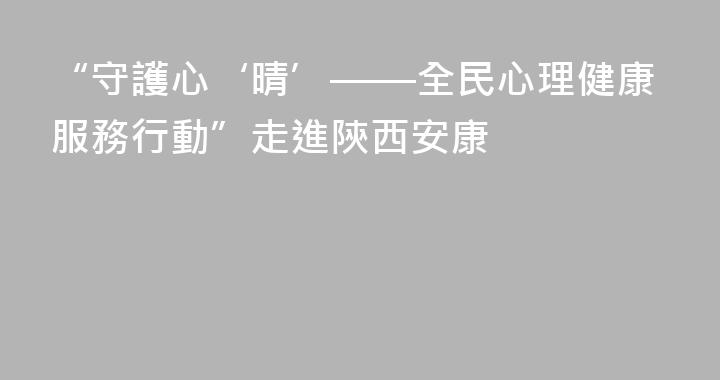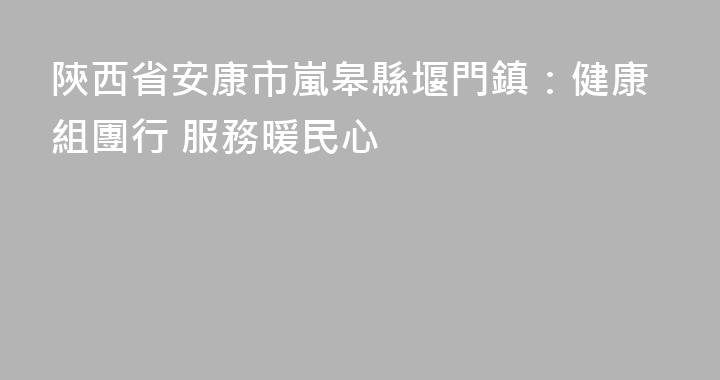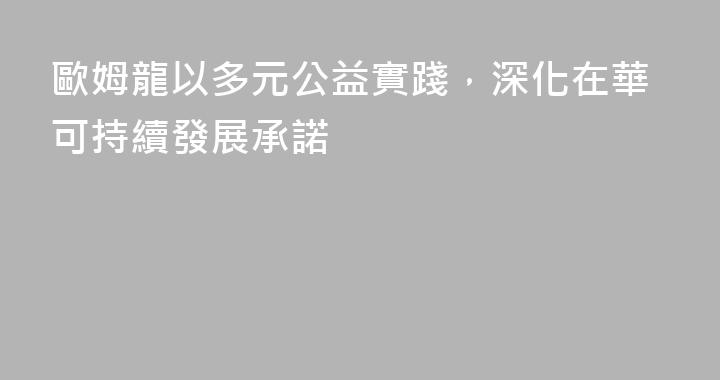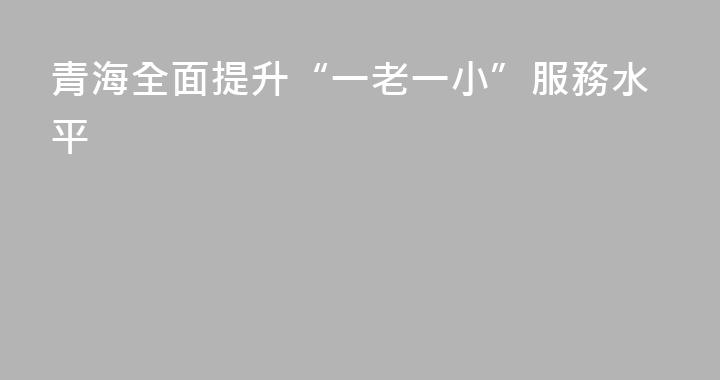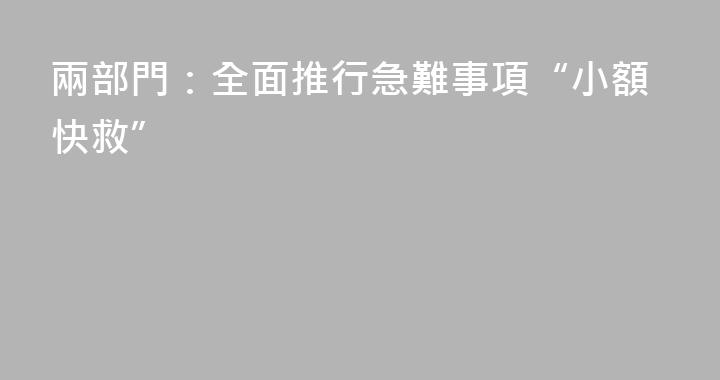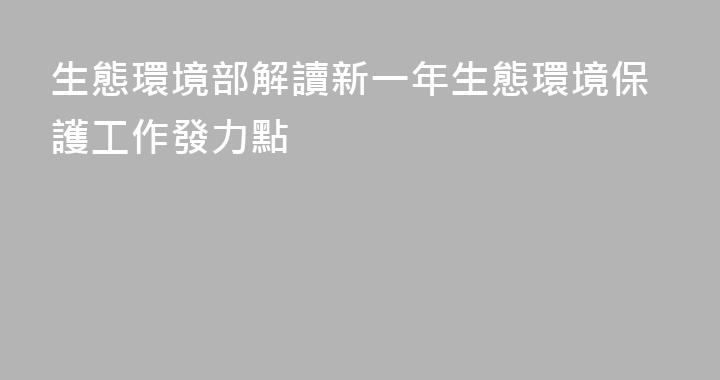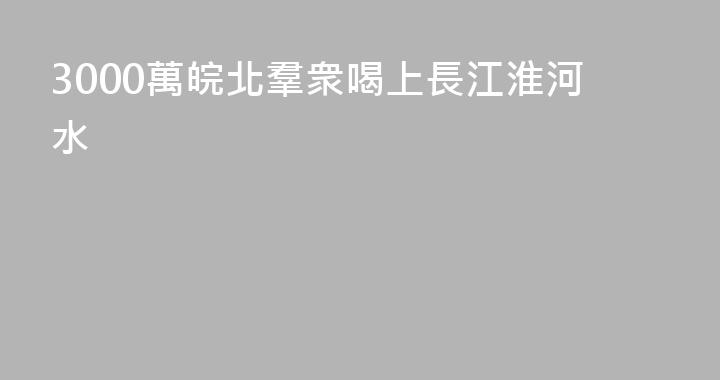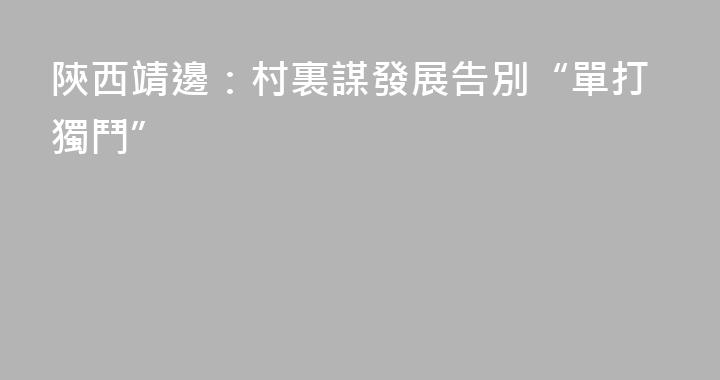自武漢宣佈封城後,黃豪傑及其團隊就在不停地忙碌着。
黃豪傑是武漢市武昌區爲先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爲先社工”)執行主任,該機構主要在武漢市範圍內開展艾滋病防治、性與性別教育和性少數人羣服務等,業務範圍輻射全省。
由於嚴格的封城和管控措施,很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無法及時獲取抗病毒藥物,面臨斷藥危機。這一羣體需要每天服用藥物控制體內的病毒,一旦中途停藥就會增加發病和耐藥風險。自封城後,黃豪傑和機構工作人員就不斷接到求助電話,最多時一天求助量有上百個。
爲應對這一狀況,爲先社工緊急成立了一個應急團隊,幫助服務對象處理斷藥危機,協調湖北省疾控中心及醫院等各方資源,幫助他們爭取藥物。從大年初一開始,機構七名全職工作人員和三名志願者全力開動,處理個案諮詢。除去吃飯和上廁所,所有人幾乎沒有時間休息。
同時,爲先社工還組建了三個志願羣,包括愛心車隊、機動志願者和借藥羣,一百多名志願者協助開展工作。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讓他們的春節假期泡湯,也給機構運營帶來了額外的壓力和財務負擔。而這也是目前武漢市及湖北省範圍內很多一線公益機構共同面臨的困境。
難以應對的工作壓力
受疫情影響,爲先社工原有的線下項目全部停止,只保留了部分線上業務。疫情發生後,幫助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獲取抗病毒藥物成爲機構最緊迫的工作。
據黃豪傑介紹,雖然艾滋病藥物是免費發放的,但並不是到哪裏都可以領取。大部分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藥物都只能在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定時定量地領取。但由於封城,大量感染者不在治療所在地,很多人在過年期間去了其他地方,甚至被困在偏遠鄉村,導致無法順利領藥。
儘管在現代醫療條件下艾滋病已經是一種可防可治的慢性傳染病,但感染者每天都必須服用藥物來控制體內的病毒,一旦中途停藥就會增加發病和耐藥的風險。斷藥危機也讓很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感到恐慌。

鑑於疫情的嚴峻程度和現實困難,湖北省疾控中心出臺了異地領藥、送藥到鎮等措施,中國疾控中心也出臺了相應措施,但由於各地情況不同加之部分感染者自身的特殊處境,仍有大量人羣無法及時領取抗病毒藥物。
“疫情發生後,湖北省疾控中心和中國疾控中心相繼出臺通知,感染者可以去其所在地定點醫院領取藥物,但很多感染者不知道流程,也沒有看到相關信息。”黃豪傑告訴記者,他們和各方一直保持着積極溝通,如協助感染者跟地方定點醫院對接,協助省疾控中心開展工作,同時也向社羣及時傳遞相關政策。
“目前的情況是大家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也給我們增添了很多額外的負擔。” 黃豪傑坦言,單憑機構幾個人的力量無法完成目前的工作。爲此,機構特意組建了三個志願羣,包括愛心車隊、機動志願者和借藥羣,有大約100名志願者協助處理工作。
其中,愛心車隊主要負責在武漢市範圍接送感染者去定點醫院取藥,因爲當地交通已經全部中斷;借藥羣主要鼓勵病友之間互相幫助,提供藥物幫助他人暫時渡過難關;機動志願者羣則幫忙處理郵寄藥物和其他一些機動性工作。
“剛剛封城時,因爲求助信息太多,團隊每個人的工作量都很大,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後來我們建立了一個需求收集機制,大家的工作量才慢慢平均下來,工作也逐漸理順了。”據黃豪傑介紹,截至目前,爲先社工已經爲600多人次提供服務,但他內心裏還是感到一絲遺憾:被困在偏僻鄉村的感染者的用藥問題目前仍無法解決。
財務狀況讓人擔憂
由於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目前中小學都推遲了開學時間,各地企業也再次延遲了復工時間。考慮到疫情防控和安全問題,很多公益組織或暫停線下業務,或將主要工作轉移到線上。而那些處於湖北省內尤其是武漢市內的公益機構面臨的情況更爲嚴重。
暫停線下業務,意味着機構承接的項目無法在預期時間內完成,很多工作計劃也無法正常執行。即使將主要業務轉移到線上,機構也還要支付相應的運營成本,比如人員工資、社保及場地租金等。對於一些小型公益機構,財務上的壓力在該階段更爲突出。
“跟以前相比,機構的財務壓力大了很多。因爲原本計劃內的很多工作無法正常開展,但是人員支出、房租支出都要按時支付,對於我們這樣的小機構來說真的很困難。”黃豪傑告訴記者,雖然目前的工作主要在線上,但也要承擔一定的成本,比如快遞藥品的費用、交通支出及其他必要支出等。
由於機構此前並沒有這筆預算,最初黃豪傑考慮由工作人員、志願者等自行承擔這些額外的費用。幸運的是,爲助力疫情防控,正榮公益基金會開展了針對一線公益機構的小額資助項目,爲先社工提交了申請並得到27000元資助。資金雖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機構的財務壓力。
但對於今後機構的運營,黃豪傑仍比較擔心:“如果目前的形勢再持續一段時間,我很擔心我們的財務能不能支撐下去。”
與他一樣,武漢市江岸區愛特特殊兒童教育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愛特中心)主任胡弘對目前的情況也很擔憂。
據胡弘介紹,愛特中心距離華南海鮮市場比較近,由於中心的主要業務是面向兒童羣體,在疫情爆發初期機構工作人員的警覺性都很高。從1月19日開始放假,該機構暫停了所有工作,到目前仍未恢復正常。

“過年期間很多員工都回老家了,現在無法返回武漢工作,所以我們也無法給孩子們和家長一個準確的復課時間。不過因爲處於疫情重災區,大家的警覺性還是很高的,也能夠理解。”胡弘表示,目前機構有一些工作轉移到了線上,比如通過專家講座、線上指導答疑等給特殊兒童的家長一些專業指導和心理支持。對於家長來說,長期照護特殊兒童尤其是自閉症兒童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其也需要專業老師的指導。
但從線下轉移到線上並不是想象得那麼簡單。
“我們之前開展的業務主要是在線下,從線下轉到線上也有一些問題和困難。因爲我們着重於對線下教師的專業技能培養,對線上業務還沒有開發出合適的模式和方法,也沒有針對性。而特殊教育是很有針對性的,在線下我們可以根據孩子的不同表現適時調整教學方法,面對面教學也更有效果。”胡弘告訴記者。
她談到,對於愛特中心來說,除去房租及人員工資社保等福利性支出,現金流的壓力更爲突出。“復課之後,機構要墊付資金用於特殊兒童的康復訓練,這給機構的流動資金帶來很大壓力。對於外界資助我們其實是有需求的,因爲就目前來看機構面臨的壓力也很大,一些原有的項目可能需要轉型。”
相比而言,爲先社工的情況可能稍微好一些。黃豪傑談到,“如果此次疫情持續時間更久,我們可能就承擔不起了。但比較幸運的是,我們在春節前備案了一個月捐計劃。如果備案通過,我們會加強相應社羣籌款,以緩解目前的財務壓力。”
亟待建立的應急機制
在積極應對“斷藥危機”的同時,黃豪傑和團隊也曾想爲服務對象多做一些事情,比如爲他們提供心理援助。但考慮到機構人員和精力有限,他暫時放棄了這個念頭。“我們現在的策略是優先處理緊要的問題,再根據疫情發展情況考慮其他方面。”
在他看來,機構目前能做的就是從自身專業角度出發,整合多方資源,關注服務對象現階段面臨的實際困難。越是在特殊時期,一線公益機構越應保持理性。“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樣不僅能夠保證服務的專業性也能保證服務質量。”
與爲先社工和愛特中心情況類似,疫情發生後,宜昌市啓智親子公益活動中心也停掉了很多項目,並根據抗擊疫情需要推出了“宜昌天使計劃”。


宜昌市啓智親子公益活動中心從外界爭取到的物資,這些物資都捐贈給了當地醫院和社區
該中心主任張曉瓊表示,“根據機構自身優勢,比如一直以來對老人和兒童等弱勢羣體的關注,我們設計了這一項目,共同抗擊疫情。希望通過該項目減輕兒童、老人年和家庭的心理壓力,爲他們開展心理疏導和疫情宣傳等服務,同時幫助困難羣體渡過難關。”
張曉瓊告訴記者,由於較早發現了疫情的嚴重性,考慮到宜昌本地相應防護物資較爲匱乏,中心在春節前就聯繫了一些省外的基金會和公益機構,積極尋求外界幫助,將他們採購的物資爭取運到宜昌,送到醫院或者社區。在他們的努力爭取下,目前已有幾批物資陸續發放給當地。
同樣,在武漢市武昌區首義路街創益無限志願者服務中心理事長周英看來,由於自身是一家關注社區困境兒童教育的公益機構,面對疫情,其首先考慮的是可以通過線上教育的方式安撫孩子及家長的負面情緒。
“由於我們的項目涉及到疫情嚴重的地區,必須暫停機構服務和志願者參與。不過,在居家隔離後,我們在大年初一就恢復了線上課堂,通過開展線上繪畫、繪本閱讀及手工等項目,安撫孩子們的負面情緒,因爲藝術本身就具有療愈功能。”周英談到。

周英帶領團隊爲社區配送物資
在周英看來,一線公益機構體量雖小,但行動起來更加靈活。“我們跟社區層面聯繫很密切,知道他們有哪些困難和實際需求,因此反應速度要比其他人快很多。當政府部門還未關注到社區層面時,我們就已經注意到社區工作的一些困難了,比如分級診斷、上門服務、居民情緒管理等。利用一些渠道,我們幫助社區在上海、北京等地申請物資,尋求基金會的幫助。”
據記者瞭解,考慮到一線公益機構尤其是受疫情影響較爲嚴重地區小型公益機構的實際困難,目前已有一些基金會開啓了資助計劃:
正榮公益基金會開通共抗疫情綠色通道,面向全國,以小額資助的方式(3萬元以內),支持專業社會組織開展補充性疫情防控;
千禾社區基金會發起“社區互助防疫——千里馬行動基金”,爲積極參與抗災互助的個人或公益組織、志願團體提供小額資金;
銀杏基金會成立“銀杏快速行動基金”並得到敦和基金會20萬支持,爲抗擊疫情的行動者提供及時、靈活、應對實際需求的小額資助......
目前,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在疫情防控一線,但到疫情發展後期該怎麼做、公益組織能從此次疫情中總結出哪些經驗教訓,也是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議題。
記者從採訪中也得知,很多公益組織尤其是一些小型機構之前並沒有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經驗,特別是缺乏應對地震、水災或其他自然災害以外的災害的應急機制和預案。這也導致機構在面臨新的社會問題時出現忙亂或被動的局面。
黃豪傑的話在諸多采訪對象中也頗具代表性:“之前機構沒有應對重大社會事件的應急機制,包括政府層面和民間層面,大家都處於探索階段。目前大家還都忙於應對疫情給工作帶來的新的壓力,沒有時間反思機制建設問題。等疫情結束後,我們可能會對此進行思考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