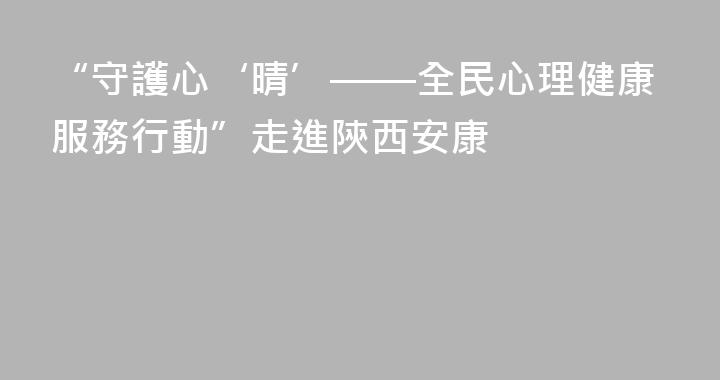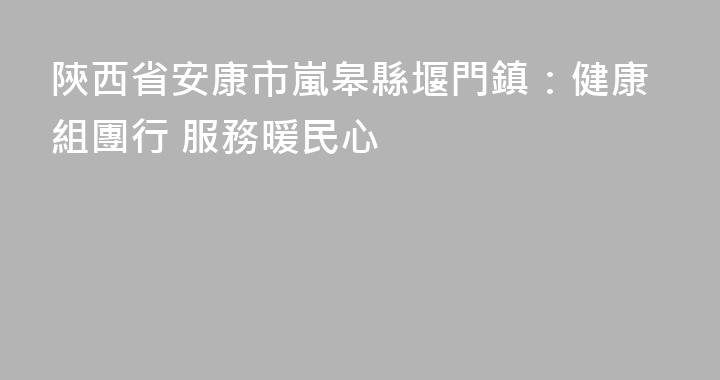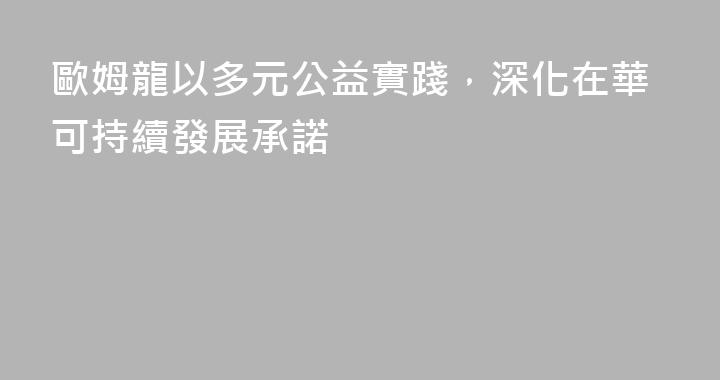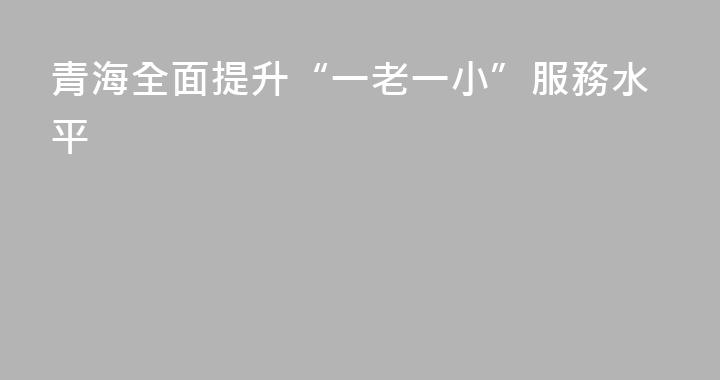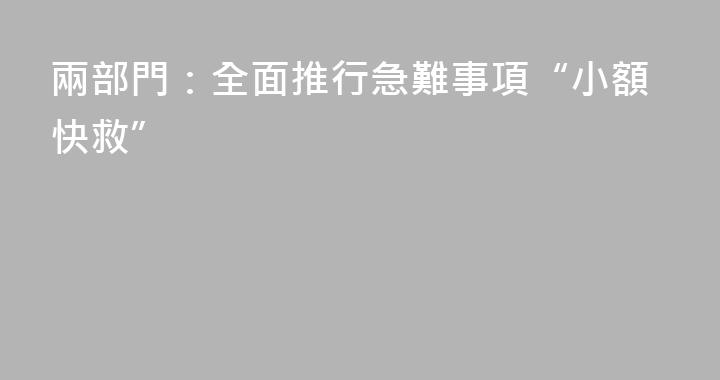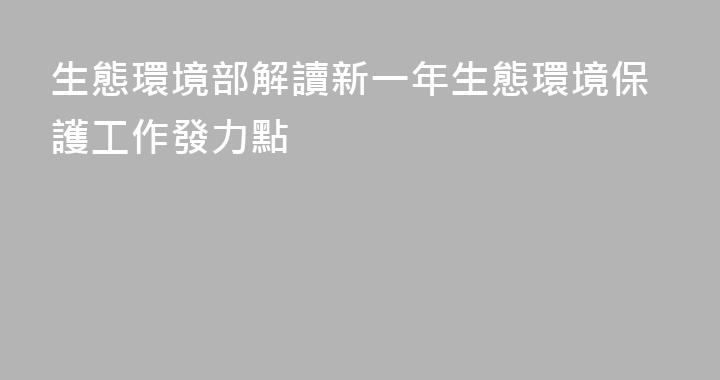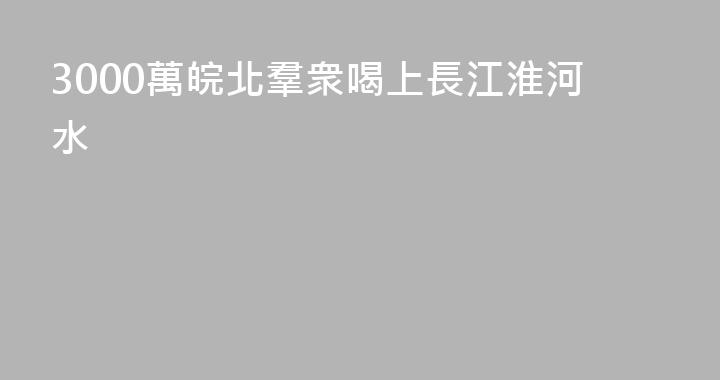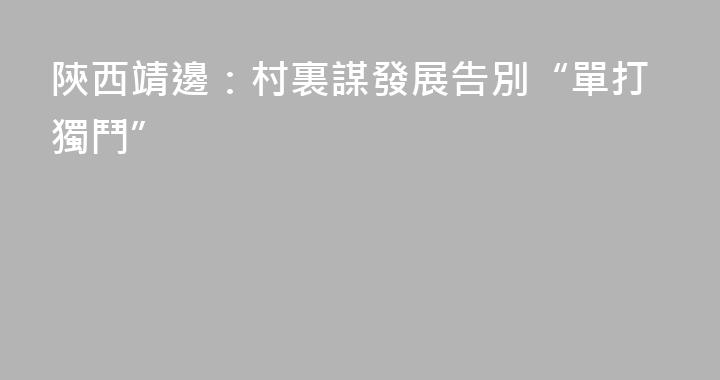“等戰‘疫’結束了,我們要去武大看櫻花,然後吃火鍋。”電話那邊,檀學兵言笑晏晏,在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堅守了20天之後,這個1992年出生的姑娘內心世界不見絲毫陰霾。
作爲北京支援湖北醫療隊的一員,她最初接到的任務是,在武漢支援14天,然而到了超期的時候,沒人問一句爲什麼,因爲他們知道這是一場必須超期才能完成的任務。
而在相隔20多公里的雷神山醫院——一座剛剛新建改造到位的醫院裏,到庫房領設備的湖北省腫瘤醫院護士朱亞,看到所有人都在忙,便默默背起了1人多高的櫃子,一步一步挪到50米遠的卡車旁,等待裝車。那個瘦弱的身影被旁邊的同事拍下來發到網上,許多人瞬間淚目。
如果沒有疫情,護士柯全喜歡下班後穿行在武漢的大街小巷,靜靜感受這座城市的美好,或是下下棋、刷刷手機。但現在,能休息時,他頭一沾枕頭就能睡着,但睡得很淺,夢裏自己還穿梭在病房裏,護理着病人。
一場突如起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節奏,而成長也彷彿在一夜之間。
“上完第一個班,我們‘幹掉’了領導的決定”
檀學兵是北京世紀壇醫院的護士,是正月初二在石家莊的家裏接到出發通知的。大年三十晚上,她在家裏看春晚,看到戰“疫”前線的內容時就問媽媽:“如果醫院讓我去武漢,你同意嗎?”檀學兵說,“當時我媽以爲我開玩笑呢,等到接到通知,才知道是真的,一下子緊張起來,和我爸一起把我送到火車站。”
1月27日(正月初三),北京醫療隊連夜馳援武漢。在這裏,他們學會的第一課是防護——保護好自己,才能救助更多的人,絕不能成爲團隊的短板。
北京世紀壇醫院這次派出13個人參加北京醫療隊,5名醫生、8名護士,其中4個80後、4個90後。年紀比他們大許多的“醫生大叔”,在這裏化身成“唐僧”。一模一樣的事兒,“大叔們”每天都要說上幾次,特別是隊長丁新民。
爲了防止年輕同事第一次上“戰場”緊張,丁新民和護士長把4個90後姑娘排在了一個班,想讓她們互相鼓勵。卻沒想到,這個決定第二天就被姑娘們推翻了。
“第一次進入隔離病房,最開始有點忐忑,但是進去之後,我再也沒有害怕過。”小檀說,當時下了夜班,凌晨4點多,4個姑娘坐在公共汽車改成的班車上,不知誰先起了個頭,就你一言我一語地開了個會。“我們覺得我們能行,做得挺好的,防護也好,不需要特殊照顧。如果我們4個一個班,別的班就要多承擔,多幹活兒。”
商量好了,第二天,她們找到護士長,就把領導的決定給“幹掉”了。
現在她們4個小時一輪班,而花在穿脫防護服和洗澡的時間加起來要兩三個小時。在這裏做好防護,絕不是一個人的事,只要有一個人做不好,就會帶來整個團隊的毀滅。
“就第一個老爺子,很抱歉給他紮了兩針”
有6年護齡的李秀男是個北京男孩,新婚不久。介紹自己時,他說,“叫我大男吧”。李秀男是朝陽醫院的護士,也是一個90後。在醫院裏,男護士是個“稀缺物種”。整個朝陽醫院有1000多名護士,男護士只有70多個,但這已經算多的了。在武漢協和醫院西院的隔離病房裏,很多人沒見過男護士。李秀男沒想到自己還因此享受了“特殊待遇”。“病人都不信我是護士,以爲我是醫生,以爲是醫生親自給他們服務,所以更配合。”
大男對自己的技術很自信,但沒想到,進入隔離病房還是遇到了挑戰。要帶着三層手套給患者消毒、扎針,護目鏡上聚起的霧氣又影響視線,打針的難度成倍增加。他們要經常低頭、側頭,讓霧氣匯成水滴,流到護目鏡內側鏡底,有時要從鏡片的縫隙才能看清楚。 他值的第一個班就是夜班,後半夜給患者採靜脈血。“當時第一針沒紮成,第二針成了。8個病人,一共抽了25管血。就第一個老爺子,很抱歉給他紮了兩針,其他都是一針成功。”
穿着防護服,戴着N95口罩、護目鏡,一會兒就一身大汗。“每組班我都會給醫護人員量一下。進到隔離病房,(醫護人員的)心率大概都是100到110之間。血氧正常人98、100,我們進去是96、97。”大男說,之前在呼吸科,知道病人憋氣難受,也會說,“我們理解你們的狀態,理解你們的心情。但其實還是理解不了。現在我們比正常人的血氧低一些、心率快一些時,就已經很難受了。這些病人長時間缺氧、心率快,肯定更痛苦。”
到了戰“疫”的最前線,生死之間,很多看法都變了,最重要的是對患者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
小檀從上高中的時候開始記日記,但也只是偶爾。現在她每天只要有時間就寫上一點兒。與別人記錄心情感受不同,她寫的更多的是患者。“因爲我覺得他們太不容易了!”
有位37歲的女患者,住進來時是“疑似”,她父親因爲新冠肺炎剛去世。一家人都在隔離狀態,家裏只有一個8歲的孩子。她剛住進來時,非要出去,來來回回就是一句話,“家裏有孩子呢!”後來小檀跟隊友就做她的工作,聯繫社區的人照顧孩子。前幾天,小檀在網上看到有個新冠肺炎患者的家裏,只有一個五六歲的孩子,社區的人隔着門給孩子喊話,送吃的,瞬間就理解了那位女患者當時的感受。眼淚當時就流了下來。
深呼吸,我告訴自己要堅強
最難的不是日常的醫護工作,而是有時要將眼淚流在心裏。
和以往的病人不一樣,這裏的病人更焦慮更恐懼,網上撲天蓋地都是各種關於新冠肺炎的消息,死亡率每天都在變化。而他們即使能活動,也只能在自己的房間裏。因爲隔離治療,家人也不能來看望,因此格外無助。
40多歲的江阿姨是和老公同時確診的。老公的病情更重,住在別的病房。有幾天,江阿姨聯繫不上老公,就拜託當班的護士幫忙看看。“進去一次,她就和我說一次,讓我幫她聯繫。我到現在都記得,她老公在11層叫什麼名字。”後來,小檀去問才知道她老公已經去世幾天了。當時心裏很難受,又不能告訴她實情,就找各種理由,“重症那邊太忙,沒有接通我們電話,後期再給你聯繫;或者說你老公挺好的,在休息,睡着了,可能沒聽到手機聲;或者手機可能沒充上電”。
“但最後江阿姨還是知道了,當時就崩潰了,大哭。我們所有人都去安慰她。她不聽,我們就一點點開導她。讓她想想家裏上高中的孩子,家裏有支撐她的人。”小檀說。
後來,她們每次去別的病房,不管是打水還是其他事情,都想着來看看江阿姨,問她需要什麼。到最後,江阿姨說,“我知道我老公的事了,你不用再安慰我了,我一定會好好活下去的。你放心吧!”
因爲是輕症,江阿姨就要轉到方艙醫院去了。但她說:“我不想離開你們。因爲在這兒挺好的。你們特別關心照顧我,護理我特別到位。”小檀就說,那兒都是輕症,去那兒應該高興,證明快康復了。當時江阿姨哭了,小檀的眼睛也紅了。
還有位80多歲特別可愛的奶奶,和老伴一起感染了。她很關心醫護人員,有時候護士操作,離她近了,或說話近了,她會說,“孩子你離我們遠一點兒。”
一天小檀給她測血壓的時候,她說,“孩子,我給你個東西,你去送給××牀我老伴。”裏面是一卷衛生紙,一個蘋果,一點麪包還有塊香皂,香皂盒上寫着多少牀,還有名字。
小檀當時奇怪,自己不知道有這個病人。去護士站查還是沒查到,一問才知,人已經去世了,東西只能放到家屬代領區。從那時起,小檀就對自己說,“只要我上班,就一定去看看奶奶。”
該給奶奶回話了,小檀平復好情緒走進病房,“奶奶,他很好,讓你不用給他(帶東西),他有吃的。讓你好好的”。奶奶說,“他有什麼吃的啊?吃的都在我這兒呢!”
第二天,小檀帶了兩個橘子去看奶奶,“爺爺讓我把他的桔子給您帶來了。您看他多疼愛您啊!您可得好好的”。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首先要過自己這一關。“我們所有的目的就是讓她好好的活着。如果自己都在悲傷的情緒中出不來,怎麼行?”小檀說,“我會深呼吸。然後對自己說:跟她說,跟她說,一定要跟她說,讓她堅強,你也要堅強。”
在這裏看見愛情最美的樣子
在專門救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戰“疫”最前線,有的不只是消毒水的味道,還有愛的味道。
柯全和喻晨都是90後,一同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工作。原本計劃今年2月2日領結婚證。但是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的節奏。1月29日,在金銀潭醫院的病房裏,柯全看到一位防護服上寫着“喻晨”的人,再看身高、體型,很像自己的女朋友。“你是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喻晨嗎?”“是。”四目相對,瞬間確認了眼神。
驚喜是如此巨大!雖然柯全知道喻晨也來支援金銀潭醫院了,但並不知道在哪個病區。然而,沒有久別重逢的擁抱與情話,因爲要忙着搶救病人,直到分開,他們也沒有說上第二句話。
2月2日這天,柯全特意等着喻晨下班,他們戴着口罩在金銀潭醫院一起走了20分鐘。“在這最危險的地方同走一段路,是種特別的紀念方式,也會是以後一段特殊的回憶。” 柯全說。
之後,他們一起在醫院食堂吃了頓飯,沒有玫瑰與燭光,只是沒有像同事那樣隔得很遠,而是面對着面。第一次破例了,隔着不到1米遠的距離,悄悄摘下口罩,端詳對面那張親切的臉。“好久沒有看到對方不戴口罩的樣子了!”喻晨的臉上還帶着口罩的壓痕,“真心疼,又覺得這一刻很甜蜜!”
柯全說,真希望疫情快點結束,“可以摘掉口罩,自由呼吸、自由生活、自由工作!”
在前線8天了,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護士胡志敏還在慶幸醫院領導終於說服了妻子,沒有讓她來武漢。胡志敏是在大年三十,看到醫院選派醫護人員支援武漢的通知的,當時就想報名,但當時妻子懷孕3個月了,他實在不放心,就想和她商量一下。誰知道還沒等他開口,妻子就說她要去。“我不同意,可她說,要去一塊去,不能撇下她。拗不過,我只能同意了。兩人一起報了名,但最終醫院考慮她的身體,沒有同意。”胡志敏總算鬆了口氣。
“疫情結束後,我就想馬上回家,多陪陪妻子。她一直擔心我在武漢的情況。有時候我覺得挺對不起她和寶寶,讓她們擔心。就希望疫情能早點結束,回去後,我要承包下所有家務。”
在這裏成爲所有人的牽掛
雖然早有準備,但是真正接到通知去新冠肺炎一線支援的時候,剛剛工作一年多的許浩遠還是忍不住有些緊張。作爲武漢協和醫院的產科護士,如果不是因爲疫情,她可能永遠也不會與防護衣、護目鏡發生交集。
接到女兒的電話,爸爸的眼淚當時就掉了下來。後來媽媽說,“你爸這情緒還隱藏得挺好的,一邊拿着紙巾擦眼淚,一邊還能這麼平靜地跟你講話。”
“現在我媽每天都在等我下班。有一次上夜班,凌晨5點多下了班。當時我媽都沒睡在等我。之後,她都會提前問我第二天上什麼班,她就會等着我。等我下了班跟她講完話,她纔會去睡。然後每天都會發一個朋友圈。”許浩遠說。
現在小檀往單位羣裏發東西,不管多晚都有人很快回復。同事、朋友說得最多的是“保護好自己,好好的回來”。小檀每天和媽媽視頻,來來回回也是這句話,“我爸說,我都聽煩了,孩子早聽煩了。感覺我們和武漢成了所有人的牽掛。”
蘋果和尿不溼的故事
雖然有各界的支援,但是物資還是匱乏。
醫療隊的物資相對比較有保障,醫生護士就經常省下一點吃的用的,帶給患者。可能是水果、飲料,甚至一次性的筷子、紙杯。
大男說,剛到前線時,還沒進隔離病房,他們去超市買東西。參加過SARS戰役的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唐子人叮囑他們多買些蘋果。後來,小超市裏的幾十個山東煙臺大蘋果,幾乎都被他們買光了。
第一天進病房,每個患者都收到了一個蘋果。大家當時很高興,有位爺爺戴着儲氧面罩。“他看到我們送來了蘋果,非要摘下面罩送我們出來。要知道一旦脫下面罩就會出現嚴重的呼吸困難,有時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我們趕緊勸阻他。他眼裏含着淚說,謝謝你們,感謝大家支援武漢。”大男說,還有個患者,給他採血時,一開始不太配合,但是給他送完水果,他的態度轉變特別大。
一個蘋果在平常不算什麼,但是在這裏不只是醫護人員的心意,更代表着好的寓意,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早日康復。
有很多第一次都是在這裏發生的,包括平生第一次穿尿不溼。大男小時候都沒穿過尿不溼,沒想到在這裏穿上了。“還挺不適應的,帶了兩次,發現自己能控制住,就不再用了。”他把省下來的尿不溼給病人用。有需要的老人,想買便盆也買不到,他們最需要尿不溼。
來自不同的單位,第一次合作卻親如一家。每天上班,一起搭班的可能有北京天壇醫院的、北京安貞醫院的,都會互相幫助,互相幫着穿隔離服,監督防護做得到不到位。
“雖然現在也叫不出對方的名字,但是隻要穿上這身衣服,我們就有同一個任務,同一個信念。”小檀說。
有很多隱形英難,所有的人都在逆行
“大家都說我們是逆行者,是白衣天使。我覺得所有人都在逆行,包括警察、快遞員,我們住的酒店的工作人員,甚至後方的醫院領導,還有媒體。”小檀說,“各行各業都在‘逆日常、行公益、共抗疫’。”
“有很多隱形英雄,他們也很辛苦。我們治療病人,他們要保證我們的休息、安全,但是他們的安全、他們的休息呢?”小檀說。
北京醫療隊住的酒店,每天有班車接送他們去醫院。“只要我們從酒店出來,班車就在那裏等着。”所謂的班車其實是一輛公共汽車,臨時徵召爲班車,駕駛員也是臨時徵召來的。每天要穿隔離服。他們是1人值24小時。“我都不知道他們吃飯、上廁所要怎麼辦?”小檀說。
每次下班都必須洗澡,淋浴噴頭有限不可能同時洗,大家下班的時間也不一樣,要分批洗。光是脫防護服,就最少要半小時。每次司機師傅都會等他們。武漢夜裏相當溼冷,因爲要通風,不能開暖風,不能關窗。司機就要在寒風中一直等着,每天都是這樣。
也有患者不理解的時候,他們甚至遇到過一些極端的病人,更不用說無處不在的病毒感染風險。“儘管有風險有辛苦,但是真的是無怨無悔。就像人家說的,不計生死,不論報酬。我們所有人都是這種感覺。”小檀說。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最重要的回憶了,很珍貴。可能以後我也會和我的子孫後代說,嗯,看你奶奶,看你姥姥(當年還去過前線)。”她大笑着說,青春飛揚。
大男說,“人生中有這麼一段經歷就不枉從事這個行業!”
2月13日,北京支援湖北隊收治的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了,其中一名是武漢的醫護人員。唐子人特別高興,因爲這是他們的戰友,他還寫下了一句話:“無畏生死赴疆場,風雨同舟迎彩虹。”
一切都在逐步到位,越來越多的人在馳援武漢、馳援湖北。2月17日,支援雷神山醫院的朱亞也結束了“後勤”支援,調回護理崗位,開始護理感染病人。
“透過窗子的那一縷陽光正在給我們加油鼓勁,等一切都過去了,武漢的櫻花一定會開得很美!”“靜待花開!”大男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2020年02月19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