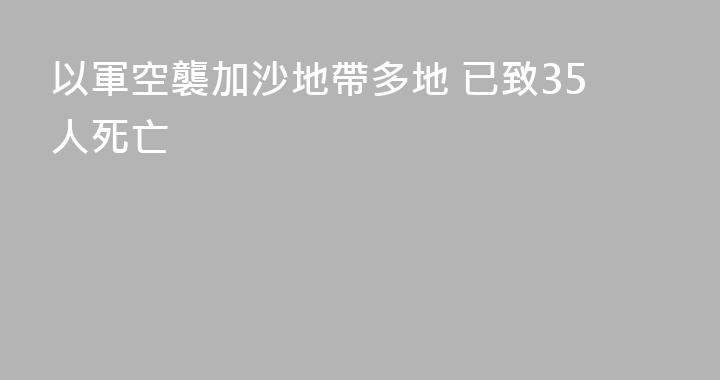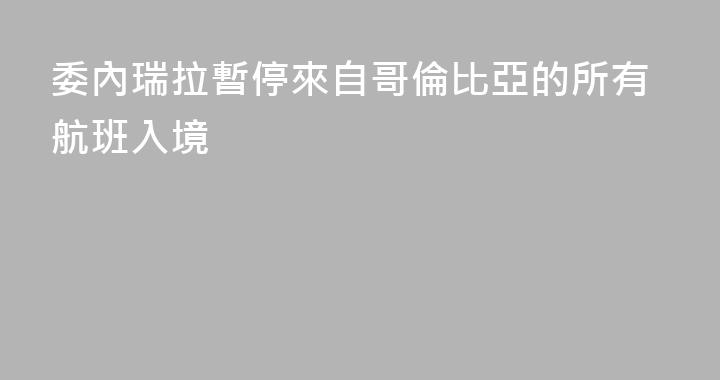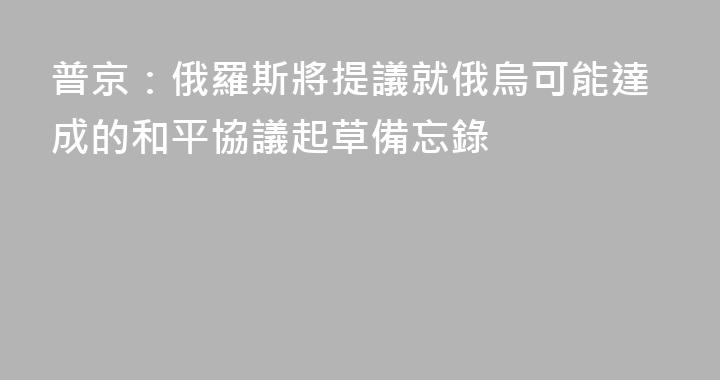美國《紐約時報》5月15日文章,原題:我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 前不久,我在威廉姆斯學院與一個名叫大衛·維格納爾的大四學生聊起了當今年輕人的困境。他說:“我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人。”以美國頂尖高校的錄取率爲例,1959年全美約半數學子只需要申請一所學校即可,而如今學生們卻得申請20—30所學校,只期望其中一到兩所能拋出橄欖枝。過去20年間,全美67所名校的申請人數增長了兩倍,每年平均將近200萬學生投出簡歷,但錄取名額卻並未隨之變化。在哈佛大學近期的招生工作中,約5.4萬名學生提交了申請,僅有1950人被錄取,逾5.2萬人被拒之門外。
不少學生都認爲,他們是“被拒絕最多的一代人”。有人說,他們原以爲考入頂尖名校就意味着殘酷競爭的終結,卻不想一場“飢餓遊戲”纔剛剛開始。很多學生社團門檻就很高,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航海家諮詢”商業社團每學期能收到800到1000份申請,但最終入圍的只有六七個人。這種選拔機制十分矛盾,你只有先成爲這個領域的專家,才能獲得准入資格。除了社團,學生們還得爭奪熱門課程、專業的有限名額。
實習機會的競爭同樣異常激烈。以高盛爲例,該公司通常會提供2700個實習崗位,卻能收到31.5萬份實習申請。一名學生投了40份夏季實習申請,被拒了39次。還有人表示,他們每年要填寫150到250份實習申請,纔有把握能得到幾個實習機會。
就業市場往往更嚴峻。數百萬人將成堆的簡歷投放到互聯網上後,沒人知道它們會被什麼樣的算法機制過濾。有的年輕人申請了400份工作,無一例外全部遭拒。
其實早在中學時期,教育體制就已經告訴過他們“成績不行”“腦子不聰明”就“當不了贏家”——這纔是這個社會最爲殘忍的拒絕。我曾問過一些學生,這樣的環境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個性。一名女生告訴我,她感覺自己披上了一層鎧甲,變得更爲強硬;一名國際生則認爲,她的美國同學各個“長袖善舞”。我將之稱爲“美國小姐綜合徵”,因爲他們總能綻放出如同“美國小姐”一樣的迷人微笑,再給出精心編排、滴水不漏的答案。還有學生告訴我,這種“拒絕文化”會倒逼年輕人學會“早做規劃”與“果斷決策”,譬如必須在12歲前就專注於某項體育運動或樂器,這樣才能在18歲的“人生首秀”讓人眼前一亮。(作者大衛·布魯克斯,劉皓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