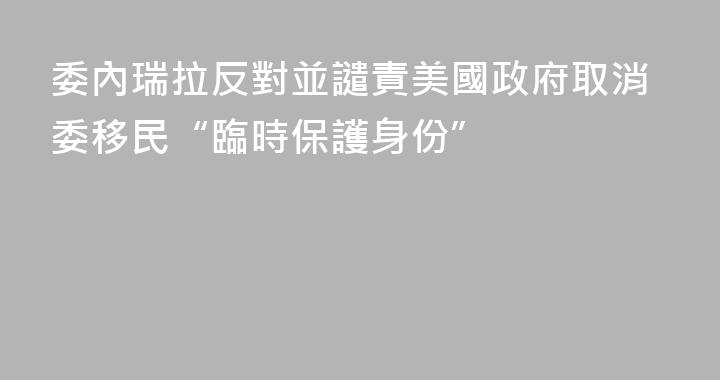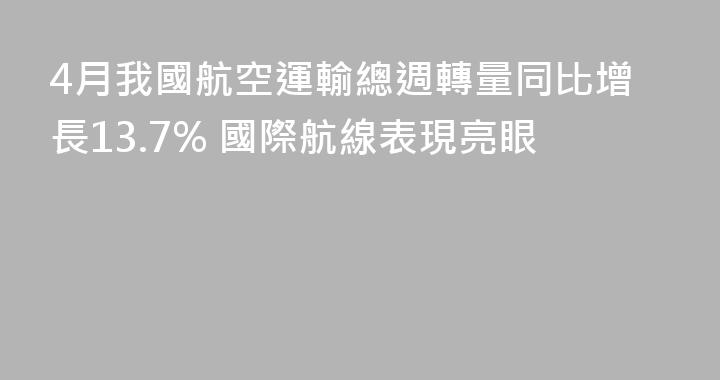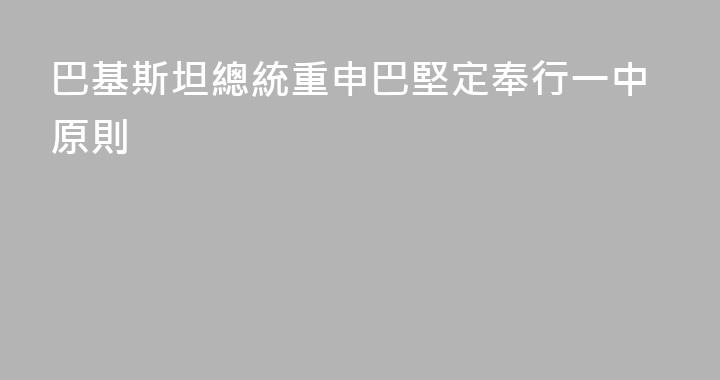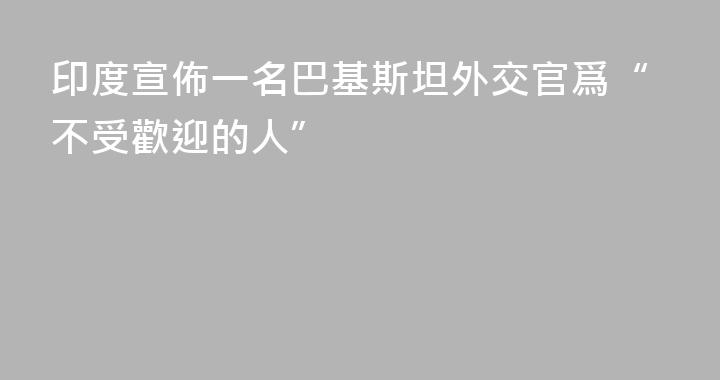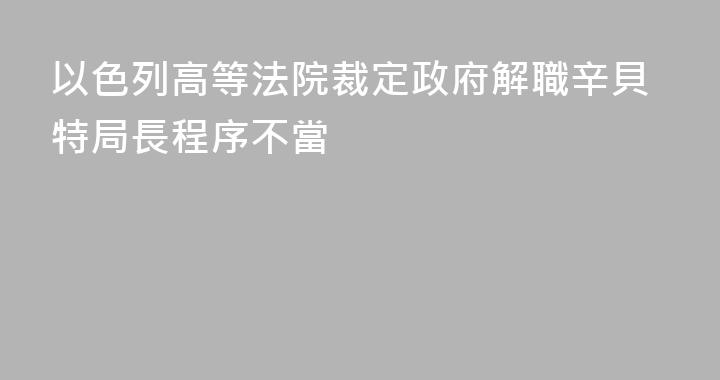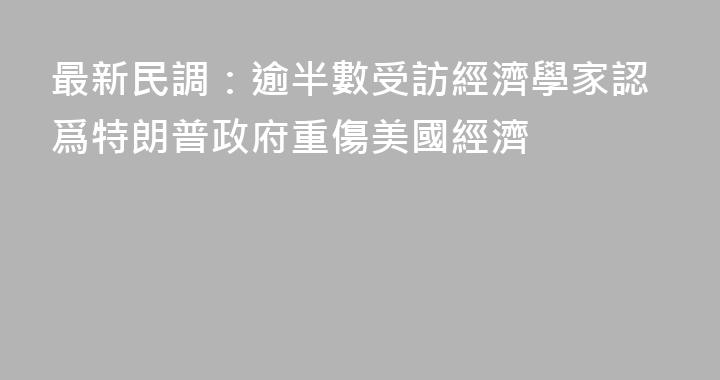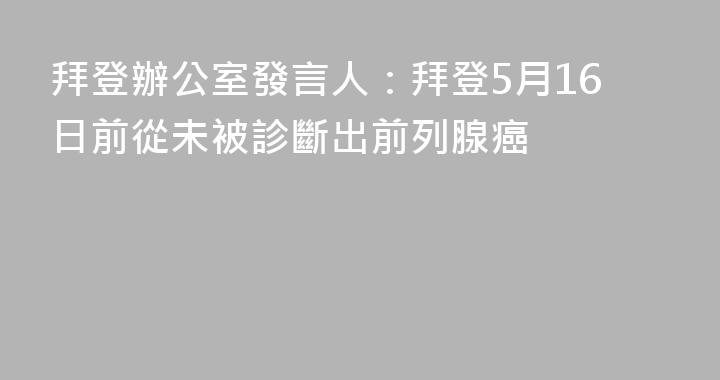【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楊沙沙】編者的話:日本媒體近日報道稱,美國與英國、中國就下調關稅達成協議後,日本政府內部出現了焦慮的聲音。20世紀80年代,日美在貿易領域激烈交鋒,陰影至今揮之不去。從多個領域“日本第一”到“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仍在承受這中間的巨大落差。本期“日美貿易衝突啓示”訪談錄的受訪者是旅日華人經濟評論家莫邦富,他已在日本生活工作40年,經歷了日本經濟的高光時刻及低谷期。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莫邦富認爲,經濟停滯不前讓日本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他表示,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做了兩件大事,核心都是打造日本的軟實力。這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國借鑑。
“中國製造”幫日本化解經濟衝擊波
環球時報:過去40年,您經歷了日本經濟的巔峯時刻以及“失去的三十年”。能否以您的視角,還原一下處在經濟巔峯時的日本社會是怎樣的?
莫邦富:1985年我來到日本。日本當時有一個“千日元老公”的說法,妻子給丈夫一天的零花錢是1000日元,當時買一個盒飯500日元,再喝杯咖啡、抽包煙基本上就花完了。
有日本中產家庭曾給我看過他們的日常開銷:30萬日元月收入扣掉稅以後只有24萬,大頭要交房租或還房貸,還有水電費等雜七雜八費用。如果妻子不工作,每月能剩下的錢也就七八萬日元,存銀行3萬,剩下5萬是夫妻雙方的零花錢,可以說一般的中產家庭也不是很寬裕。
1985年日本被迫簽署“廣場協議”後,日元急劇升值,日本人紛紛到海外投資。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達到最高峯。當年,我到美國夏威夷,當地人告訴我,夏威夷可以做高爾夫球場的山谷,很多都被日本人買下來了。很多靠近海邊的酒店,也被日本人買了下來。
環球時報:日本泡沫經濟崩潰時,整個社會是什麼樣?
莫邦富:當時最直觀的感受是,房價一下子掉下來了。此前東京低於5000萬日元的房子非常少,1992年以後,市面上待售的5000萬日元以下的公寓開始多了起來。
另外一點感受是,日本百元商店逐漸興起。中國義烏產的商品,大量擺放在日本百元店的貨架上。買套餐具,如果是日本國產的,起碼要花5萬日元,但在百元商店,花5000日元就能搞定。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人的生活質量並沒有下降多少,我認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化解掉很大一部分經濟衝擊波。
“失去的三十年”,日沒忘打造軟實力
環球時報:據您觀察,“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在哪些領域加強了建設?
莫邦富: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把以日餐爲代表的美食文化推向全球;第二件,學好萊塢,以索尼爲代表的企業將影視文化發揚光大。兩件事的核心目的都是打造日本的軟實力。
現在日本人似乎在西方國家很受歡迎,但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在一些國家被稱爲“經濟動物”,意思是他們只知道賺錢。日本農民協會簡稱“農協”,經常有人罵日本人就是個“農協”,類似稱其是“鄉巴佬”。
日本人改變形象的手段之一,就是發展美食經濟。日元被迫升值後,進口商品變得便宜,西班牙火腿、法國和意大利的紅酒充斥市場,日本美食行業認真向法餐學習,餐飲行業慢慢成長,並逐漸開闢國際市場。
1979年,日本索尼公司研發出“隨身聽”,爲傳播日本文化提供了強大的現代工具。例如,大家熟悉的日本歌曲《北國之春》,就傳遍整個亞洲。這就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我在介紹這首歌的時候,經常說這是日本的“農民工之歌”,講述的是主人公背井離鄉到城裏去打工,思念家鄉的老母親和老父親。想想看,我們有沒有這樣一首歌,像《北國之春》這樣傳唱海外?假如我們每年有10部像電影《哪吒2》或遊戲《黑神話:悟空》這樣的文化產品面世,就會將中國的形象提到一個新高度,中國的軟實力也可以大大增強。
環球時報:8年前,您在採訪中提及,日本很多年輕人不想出國留學,日本人的學習意願大大衰退。日本年輕人現在還是這個狀態嗎?
莫邦富:“失去的三十年”意味着什麼?當時剛畢業的大學生,現在已經50多歲,臨近退休了。30年中,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下降。很多日本企業的業績讓員工產生一個非常悲觀的觀點——我努不努力,成績都沒去年好,那我乾脆放棄掙扎,開始躺平。30年過去,後果很可怕。不僅這一代人不努力,還給後面年輕人留下了“不需要努力”的印象。
和日本七八十歲的人聊天時,我能感受到他們身上旺盛的能量,到現在這些老人還想着能不能發明一種新產品把局面扭轉過來,因爲這一代人有成功經驗。但是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沒有成功經驗,只有失敗經驗,接連的打擊摧垮了年輕一代,最後整個社會都出現了躺平現象。
前面我提到索尼“隨身聽”,但如今,我們身邊有什麼產品是日本的?我的電腦是日本科技巨頭NEC生產的,但NEC已被中國聯想收購,我的手機是美國蘋果的,裝的是韓國聊天軟件LINE……曾經的第二經濟大國日本,在互聯網經濟時代,幾乎什麼都沒留下。
“中國是繼續發展的世界第二”
環球時報:對於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結果,日本社會有何評價?
莫邦富:總要有人站出來與霸權主義做鬥爭。從中美日內瓦會談來看,中國取得了不錯的成果。當美國發現壓不住對方的時候,就會選擇妥協。
1990年,我在東京街頭聽廣播說,“中國的GDP正在追趕東京都的GDP”。聽到這個消息,我在街頭差點“暈”過去,那時一個東京都就能把中國的經濟實力覆蓋掉,當時真的感覺,中國再怎麼努力,也很難追趕上日本。
20年後的2010年,當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爲全球第二時,日本一個知名經濟團體的負責人跟我交流,他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日本的世界第二和中國的世界第二是不一樣的。日本的第二是我們做到頂級之後的第二,而中國的第二是會繼續發展的第二。”他的話也讓我明白,爲什麼一直以來,美國對中國戒心會這麼大。
環球時報:一直以來您都非常關注中企出海。在您看來,中國企業現在開拓海外市場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莫邦富:20世紀90年代末,我開始關注中國企業出海。義烏小商品的流動軌跡讓我十分震驚。我曾在迪拜碼頭看到堆積如山的義烏商品。當地人告訴我,這些商品很快會被裝上許多更小的船,穿過運河,往沙漠更深處轉運,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上。我在義烏看到一個賣牙籤的老太太,她一盒牙籤的利潤只有5釐,不足一分錢。但就是這樣的牙籤,她一天能掙1500美元。
如果一盒牙籤能賺5分錢,義烏人會說這不是好生意。爲什麼?你能賺5分錢,大家都會蜂擁而上搶做生意,但你只能賺5釐,誰都不敢隨便做。一些中國企業把一個黃金價的產品做成白菜價,靠着這5釐錢積累起來的資本,一點點發展壯大。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已經到了必須改換新賽道的時候,中國企業要做更多有知識產權、有原創特點的新產品,才能把生意長久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