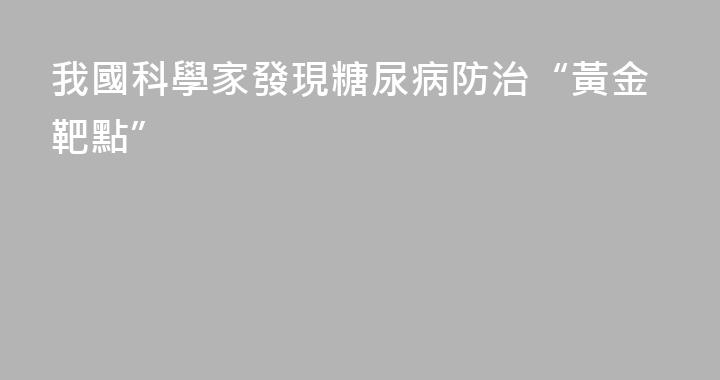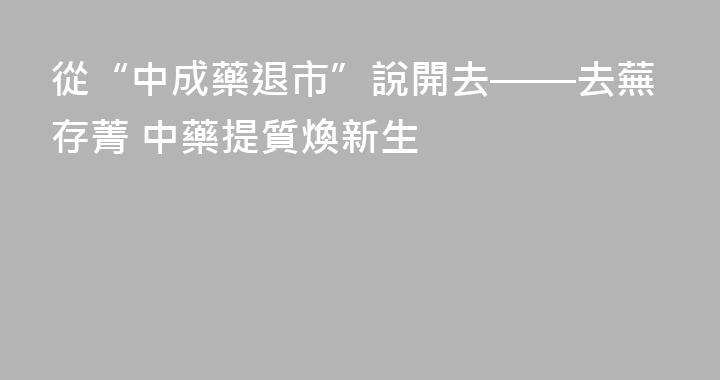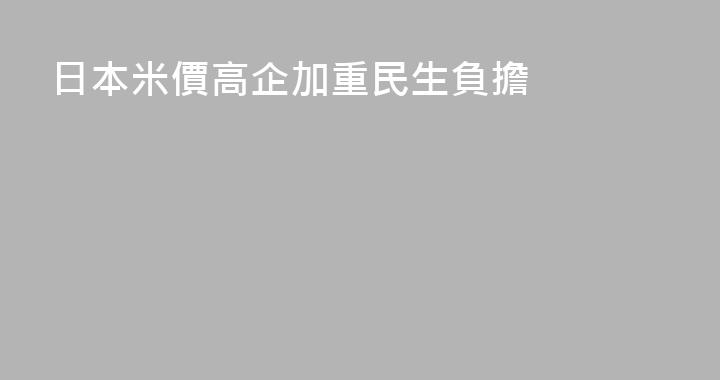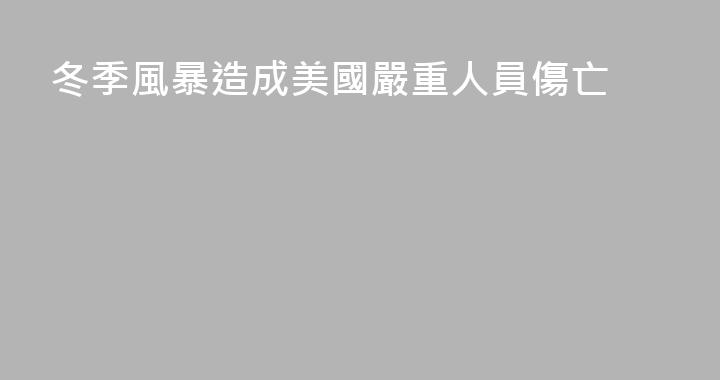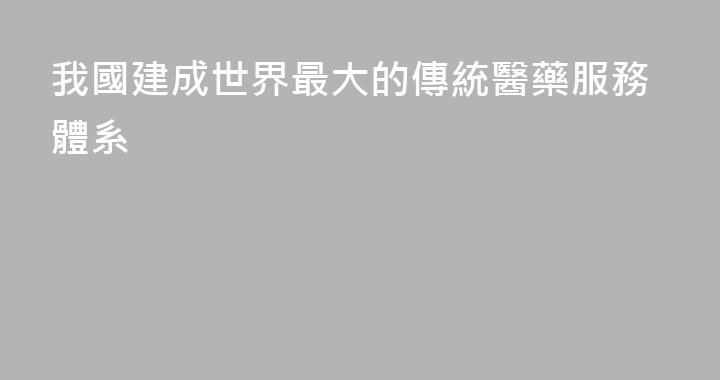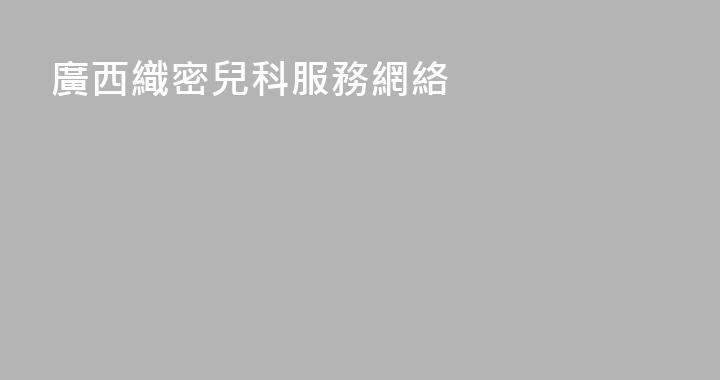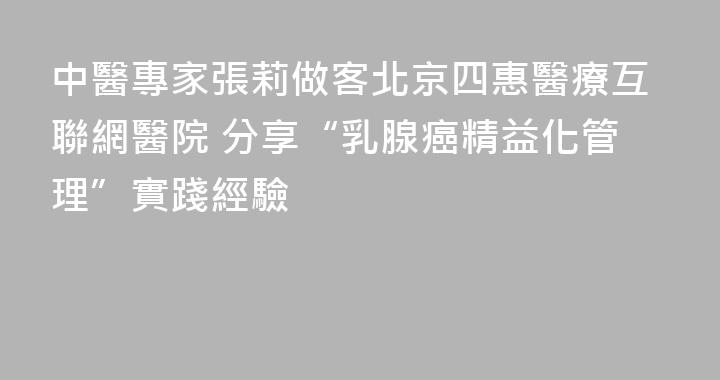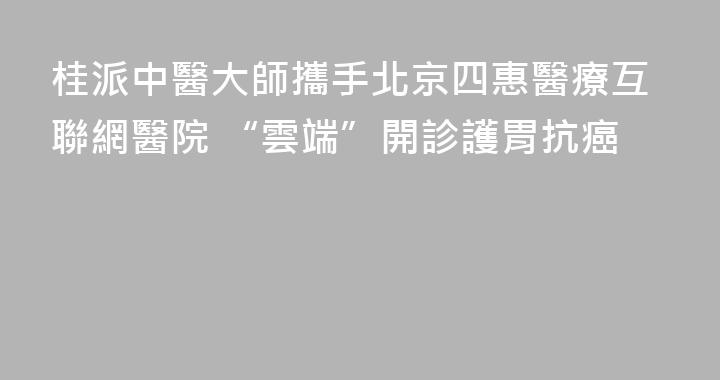將青少年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 “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鬱症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開學前一週的週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對父母說:“能不能帶我看一下心理醫生。”
心情低落,長時間發呆,無原因流淚……她已經和這些症狀交手了數月。當時,何琳得了急性胃炎。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痛苦,讓她終於決定求救。
經檢查,何琳確診了抑鬱症。
“我沒什麼感覺。爸媽有點驚訝,他們覺得我平時挺活潑的。”何琳回憶道。
前段時間,教育部在答覆政協《關於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鬱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時指出,要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沙莎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總體來說國內兒童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爲1%—2%,青少年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爲2%—8%。爲提升兒童青少年抑鬱症檢出率,將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是覆蓋面最廣、可操作性較強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當了十幾年精神科醫生,沙莎接診過太多患抑鬱症的孩子,瞭解他們的無能爲力、不由自主。“他們需要醫生,需要專業人士,保護他們,爲他們發聲。”
小別扭還是心理問題?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學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牀心理學博士徐凱文做過一些對中學生的心理評估。“我們不僅做測試,還一對一做訪談。我們發現,現在青少年抑鬱症發病率比例確實不低。”他說。
一個被經常報道的數字,是《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中給出的——2020年我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爲24.6%。
不過,抑鬱情緒並不等同於抑鬱症。沙莎說,抑鬱症的確診,需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有精神科醫生執照的專科醫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精神疾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此前發佈的《202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指出,因爲新冠肺炎疫情,孩子們在心理上又額外承受了更多壓力。
從接診情況來看,沙莎也切實感到了疫情的影響。
隔離,居家學習,網絡的過分使用,日夜顛倒……這些擾亂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節奏。成年人可能無法感同身受疫情對孩子心理的衝擊。外部環境的劇烈衝擊或隔離,可能讓孩子體會到更多的擔憂和恐懼。而青少年處在生理和心理雙重生長髮育階段,思維以及心理髮展的不均衡,可能會導致孩子無法準確表述自己的內在體驗,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或行爲問題,嚴重的還會陷入某種偏激狀態,很難自主走出。
“疫情對青少年抑鬱症的作用因素,還需要全社會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沙莎說。
抑鬱症目前還是依據現象學診斷。徐凱文介紹,抑鬱症有一些常見症狀,如情緒低落、興趣減退、快感缺乏、行動遲緩、語速變慢、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等……若每天大部分時間處於這種狀態,且持續兩週以上,就需要引起注意。
媒體人張進曾在書中這樣描述他患抑鬱症時的感受——腦袋像灌了鉛,昏昏沉沉;胸口火燒火燎地難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猶豫畏縮。
患有抑鬱症的青少年,同樣有類似症狀。沙莎說,不過他們還有一個顯著區別於成年人的症狀特點——煩躁。
“如果你問抑鬱症患兒爲什麼會自殘自傷,很多人會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很煩。”沙莎說。
那團叫人煩躁的、捉不住擺不脫的東西,壓在孩子心頭,流竄在他們體內。有時劃傷自己,他們才覺得能釋放一些,能好受一點。
有些孩子會出現軀體上的症狀,比如腹痛、頭痛。抑鬱症常見的表現是失眠、食慾減退,但有些青少年則表現爲暴食、嗜睡等反向軀體症狀。
他們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記憶力也可能會下降。“有的孩子會感覺不到自己的情緒,感覺不到自己和環境的區別,覺得麻木和不真實。”沙莎說。
青少年在抑鬱中,還可能合併焦慮症狀,容易感到緊張、害怕。
“特點多而且雜亂,合併症也很多。”沙莎介紹。所以,當一切初露端倪時,很難被察覺,也可能被誤讀。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間。她一個人待在房間裏上網課,其實並沒有聽進去,只是發呆、神遊。她不出門,不想動,父母也只是說一句,你怎麼變懶了?
孩子的變化,容易被當成叛逆期到了,被誤解成逃避學習的小花招。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標準——看孩子的社會功能是否遭到損害。更簡單來說,就是看他們是否還能正常完成學業,堅持上學。
厭學,是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普遍出現的症狀。
徐凱文說:“幾乎每天都有家長找到我,說孩子有一段時間不上學了,能不能給孩子做一下心理諮詢。”
不過,能將孩子厭學和心理問題關聯上的家長,已算是難得。對抑鬱症沒有認知的父母,面對不願上學的孩子,可能會變本加厲地斥責、批評,反而雪上加霜。
有問題的孩子背後,多是有問題的家庭
何琳並不知道自己發病的誘因是什麼。事實上,對於抑鬱症的病因,目前科學上並無定論。只能說,生物、心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都與之有關。
從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無法快樂起來的境地。
發呆時,一些過去的畫面在她腦海裏重演。那已經是她上小學時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沒做完作業,爸爸氣到踹東西、摔盆。乒乒乓乓,聲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無法和脾氣急躁的父親單獨相處。每次只要媽媽一出差,她就會發燒。
開始接受心理諮詢後,何琳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那個時候,她就已經受到了傷害。
從業二十多年的陳清是何琳的心理諮詢師。
他反覆向科技日報記者強調,要解決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必須連同父母的問題一起解決。
“難點在於,很多父母不願意承認自己有問題。”陳清說。求助他的很多家庭,親子關係已經處於崩潰邊緣。孩子和父母的溝通幾乎中斷,甚至互爲仇敵。
陳清見過太多焦慮的父母。情緒是會傳染的,孩子會承接來自父母的情緒並放大它。對成年人來說尚可忍受的焦慮,到了孩子這裏,可能會壓垮他。
陳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樹。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葉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風暴雨,可能被打落幾片樹葉,但等風停雨歇,它照樣能茁壯成長。但如果這棵樹本來就根基不穩,病病殃殃,一場雨,一陣風,就可能颳倒它。
根基,是從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態,與幼年成長階段家庭的照顧和關愛有較大關係。
“孩子對父母的情緒其實是很敏感的,他們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愛不愛他。如果家長對孩子常常是強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熱諷,長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會喪失安全感。”陳清說,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出來的心理之樹,更有可能被挫折壓垮。
徐凱文同樣表示,孩子抑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親子衝突。
親子衝突,其實源於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家長和孩子成長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經驗來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孩子,無異於“刻舟求劍”。
徐凱文講了一個讓他唏噓的案例。
孩子自殺未遂,父母求助於徐凱文。一開始,徐凱文沒找到什麼明顯問題。父母看起來非常關心孩子,爲了照顧他,還提前退休,專心陪伴。
但這孩子總覺得絕望,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
進一步瞭解後,孩子終於跟徐凱文提起一個細節——我這麼大了,爸媽進我的房間前,都不會先敲門。
在徐凱文的鼓勵下,孩子嘗試跟父母提出了“敲門”的要求,結果斷然遭到拒絕。大家一起當面溝通時,父母依然無法理解這一訴求:“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進自家房間怎麼還要敲門?在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爸媽進我房間,也從來不敲門啊。”
徐凱文明白了,這麼小的事情,孩子都無法掌控,所以他覺得人生不是自己的,乾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對孩子已經是過度控制了。”徐凱文說。
過分關注或者過分忽視,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鬱症患兒家長的教養問題。
過分關注,是孩子出了一點點問題,有一點點脫離掌控,父母就十分緊張,擔心孩子誤入歧途或出危險。過分忽視,則是對孩子的疾病體驗不以爲然,甚至覺得病是裝出來的。他們說孩子“嬌氣”“不勇敢”,說“別的孩子都沒事,怎麼就你有事”“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怎麼不像你這樣脆弱?”
除了父母不恰當的教養方式,抑鬱症陽性家族史、個人先天性格氣質、學業壓力、朋輩競爭、暴露在不適合自己年齡段的負面信息下或是長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鬱症發病的影響因素。
徐凱文特別解釋了學業壓力。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我們一直把成績當成評價一個孩子的唯一標準。彷彿一個學生自尊的全部支撐,就是成績。”徐凱文說,當成績成爲唯一標準,孩子就會不斷遭遇挫敗。“他們會覺得,一旦我成績不好,我就沒有價值了,我就什麼都不行,就躺平了、癱倒了,當垃圾了。”
國家已經提出了“雙減”政策,減輕孩子過多過重不必要的學習負擔,從心理諮詢師的角度來看,徐凱文直言這是“德政”。“我們要學會換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壓力。哪怕一個成年人,如果他長期睡眠時間、遊戲和休閒時間得不到保證,長期處在過高的期待下,照樣會出問題,更何況是孩子?”
從篩查到治療,家校醫攜手,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
將青少年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鬱症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量表篩查是比較常規的方式。要選擇規範的、經過信度效度檢驗的適用於青少年人羣的量表。爲了保證重要信息不會遺漏,我們也會讓家長參與到調查中來。”沙莎說,抑鬱症量表會涉及多個維度的測量,如情緒、軀體、睡眠情況等相關因素,也會問到自殺的意念與行爲。“從健康管理的角度,我們需要把已經有自殺想法的孩子標記出來,防範風險。但我們也要思考,怎麼在篩查時,讓這些問題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來。”
家校溝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議,做青少年抑鬱症篩查,儘量讓家長“知情同意”。學校告知家長篩查的內容和意義,如果家長有質疑和顧慮,學校可以聯合專業機構答疑解惑,在告知階段消除一些誤解。
“對篩查結果的應用,要注意保護青少年隱私。”徐凱文提醒,心理健康狀態測評結果的知情範圍,應該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師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學和精神衛生學知識,給孩子恰當程度的關心。“特別要明確的是,不要因爲篩查結果對孩子產生歧視和偏見。否則,以後大家不會如實填寫量表了,篩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凱文強調。
篩查,是篩查孩子患有抑鬱症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帶孩子就診。
別把抑鬱症看成絕症。它需要被重視,但也不要被它嚇倒。根據整體的數據,一半以上的抑鬱症患者是可以被治癒的。
沙莎說,對青少年心理問題,應進行的是綜合治療;要用藥,也要開展心理療愈;治療孩子,也要把家庭納入,對家長進行宣教和輔導。“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家庭、學校、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組成聯盟,從用藥情況到心理治療情況再到日常生活情況,全方位地跟蹤關注患兒,並針對患兒的康復情況和康復策略進行密切溝通。”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與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國的精神科醫生和有經驗的心理諮詢師數量都不足。
家長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孩子配合治療。
如果孩子需要用藥,要儘量做到足量足療程治療。
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藥物的作用並非立竿見影,有時副作用會先於治療作用來到。家庭要成爲孩子的後盾和支撐,幫孩子理解自己的處境和治療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藥的依從性。
“家長還要對自己的教養方式進行評估,看看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沙莎說,如果是過度控制,那就放鬆一點;如果是過度忽視,那就更關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帶着愛去支持,也帶着愛去限制。要讓愛在家庭中流動起來。”
當孩子病情穩定後,就可以復課復學。“學校要信任我們精神科醫生的診斷。”當醫生爲孩子開出復學證明,就意味着經過審慎評估後,孩子已經可以重返校園。沙莎說,學校不必過分焦慮與擔憂,與家長保持溝通,給予患兒持續有效的關注即可。
此前在做心理治療時,陳清爲何琳做了家庭關係修復。全家人一塊兒接受了心理諮詢,父親爲曾經的暴脾氣向何琳道了歉。
“我給生病後爸爸媽媽的表現打9.9分。”何琳說,爸爸的改變尤爲明顯,他脾氣收斂了許多,給了自己更多關心。1年多來,何琳能感到,父母在儘量讓她開心,也在盡力瞭解她。
現在,何琳身上的抑鬱症症狀已經消失,她重新擁有了快樂的能力。
“我們不要把抑鬱症看得那麼重。”何琳想對跟曾經的她一樣處境的同齡人說,“用平常心對待,這些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的。”
何琳喜歡跳舞,喜歡書法和畫畫,還想抽空學一門樂器。在最近的朋友圈裏,她爲閨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業,討論番劇,也發自己的照片和短視頻。她展示着屬於她這個年紀的鮮活的青春,還有無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