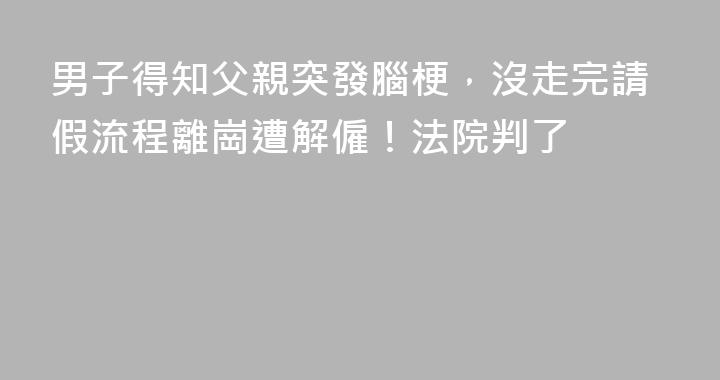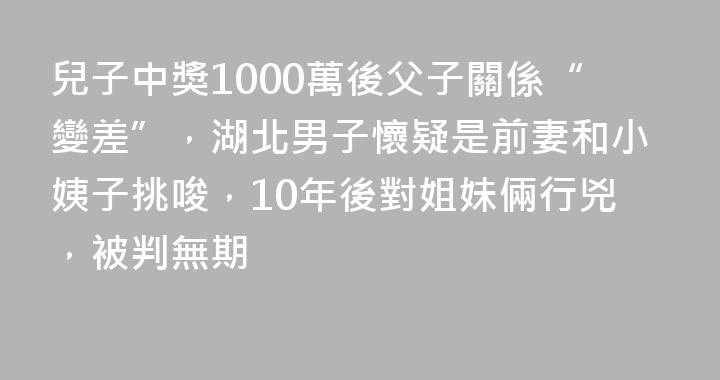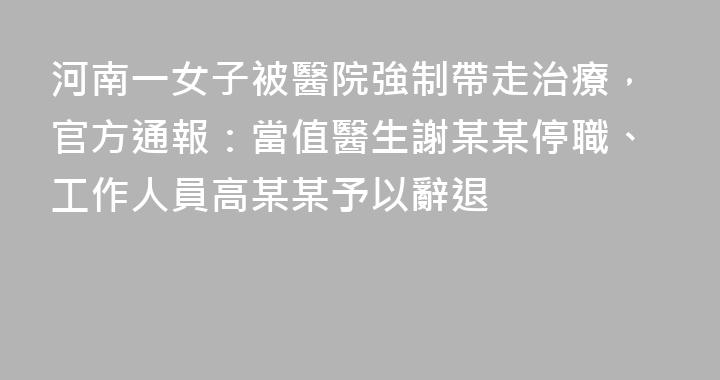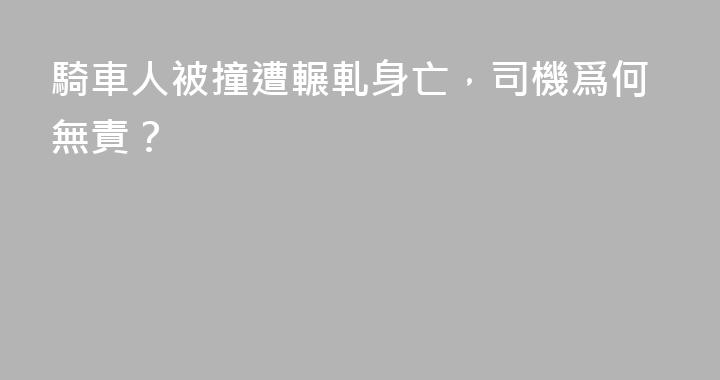自今年2月開學後
福州市第二總醫院神經精神病防治院
臨牀心理科的厭學門診人數就不斷攀升
其中不少是高三學生
有的“厭學”了
有的大腿青一塊紫一塊
許多家長都在問:
“怎麼好好的孩子,突然就這樣了?”
“你以爲孩子突然垮了,其實早有蛛絲馬跡。”臨牀心理科精神科主治醫師、中級心理治療師鄒曄峯介紹,下月就是高考了,不僅孩子需要學會解壓,家長也要做出改變。
17歲高三男生突然“厭學”
小曾(化名)是高三男生,瘦瘦高高的個子,走進診室時,手裏拎着一瓶蘇打水,爺爺小心翼翼地跟在後面。
“今天是自己想來的,還是家人讓你來的?”醫生問。
“我自己想來的。”他的聲音很小,輕輕坐下後,幾次欲言又止,“他們說我厭學了。”
“他們”——是老師、家長、同學,甚至他自己。
經過心理醫生的深入交流發現,小曾並不厭學。上學期,小曾請了長假,在家休息了幾個月,內心還挺渴望早日回到校園。但回校之後,看着同學們說笑,而他像被“透明罩子”困住。白天強撐笑臉,夜裏輾轉難眠。他想堅持,但每分每秒都像折磨。
家人說他只是“狀態沒調回來”;老師說“堅持一下就好了”;他也試着這樣安慰自己。可他覺得堅持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泥潭中掙扎。
不是“不想學” 而是“心太累”
“重返校園不能融入人際圈、暫時沒找到學習的狀態,注意力不集中,伴有明顯的焦慮情緒,睡眠受到影響,進而影響白天的精力,我們考慮小曾是不能適應環境引發的焦慮抑鬱狀態。”鄒曄峯介紹,小曾的情況是“心理衝突”的自然反應,是身心在喊“我真的快撐不住了”。
醫生們首先幫助他消除自責的情緒。其次,去探討他多痛苦就意味着有多麼想要改變。再次,進一步澄清付出的努力未必能夠獲得預期的成果,即便結果不理想,我們依舊需要努力調整。最後,再賦予其希望,與其討論具體緩解焦慮情緒、改善人際、適應校園生活的技巧。小曾的情緒有所平緩,相信自己在家人的幫助下能夠恢復正常。
據醫院門診數據,2025年開學初臨牀心理科接診的青少年中,超過六成爲因學業相關焦慮、情緒障礙、睡眠問題前來就診。他們有的表現爲“厭學”,有的可能是“自殘”“焦慮”。而他們的共性是——“外人看來好像沒問題,可他們自己很痛苦。”
高三男生小南(化名),指尖滿是咬痕。就診時,他已經連續三週,每天只睡三小時。父母說小南凌晨驚醒後,會默默躲進衛生間繼續刷題,但成績仍一落千丈。就診前一晚,他甚至在做英語完形填空時突然呼吸急促,手指開始抽搐。
心理評估結果顯示:小南已陷入高度焦慮狀態。
小南說起,開學初班主任說了一句動員的話:“每一道錯題,都是高考考場上刺向你們的刀。”從那天起,他開始在錯題本上寫“血債血償”,每天用紅筆圈錯題,漸漸地——錯一題,他掐自己大腿產生瘀青,以此“逼自己集中注意力”。
好在,小南及時就醫。經過八週的系統干預——包括藥物治療、個體心理支持和團體治療,他的焦慮評分從78降到了32。
需要改變的,還有家長們
“厭學和焦慮並非突然出現,
而且背後原因不止一種。”
鄒曄峯介紹,幾類因素需要引起重視
認知超載:刷題刷到腦殼“宕機”。有初中生一天練習卷子超50頁,結果導致大腦前額葉疲勞、專注力失調、記憶力驟降。
情感赤字:家人愛我,但不懂我。 “情感雙盲”的家庭越來越多:孩子不會表達脆弱,父母看不到孩子眼裏的信號。
社交孤島:沉迷網絡≠有朋友。很多孩子線上社交6小時+,現實中卻失語、人羣恐懼症。
意義危機:我們常說“爲未來而學”“爲高考而拼”,可在孩子眼裏,這些話是空洞的,沒有清晰價值認同,就很難有持續的內驅力。
“所以,家長們要學會懂孩子。”鄒曄峯也提醒家長們,你以爲的“孩子突然垮了”,其實早就有了蛛絲馬跡;你以爲的“他們只是怕喫苦”,其實是他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層的心理內戰;你以爲的“堅持一下就好”,可能正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要做的,不是批評、催促、拉扯,而是用心聽、用愛撐、用專業助,是先理解,再陪伴,再行動。”他表示,當你真正懂了,孩子也會慢慢找回那個,曾經熱愛學習的自己。
下個月就迎來高考了
鄒曄峯建議
家長們不妨從以下方面開始改變
接納孩子的不完美,允許他們停下來喘口氣;
重新建立親子溝通的“情感賬戶”,讓家變成避風港,而不是戰場;
當孩子出現持續睡眠問題、食慾下降、情緒反覆、逃學念頭,尋求專業支持:及時就醫干預比任何道理都更重要;
重建對“學習”這件事的定義:學習不是爲了分數,而是爲了認識世界和自己。
記者 陳丹 通訊員 林佳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