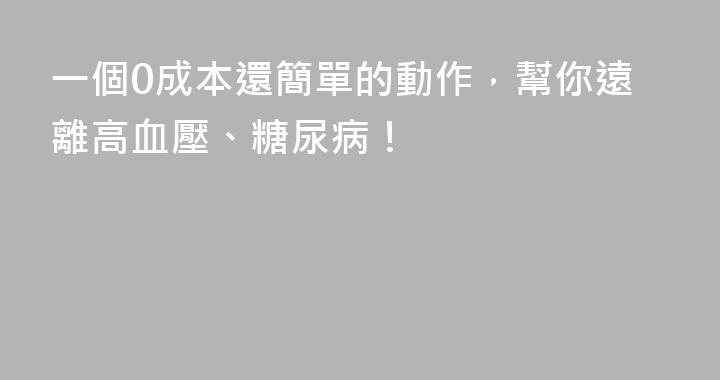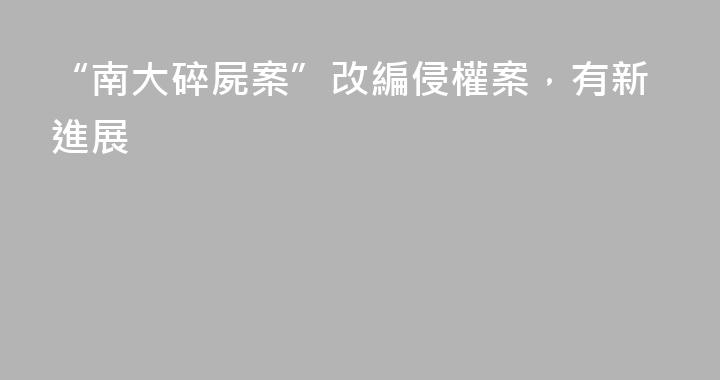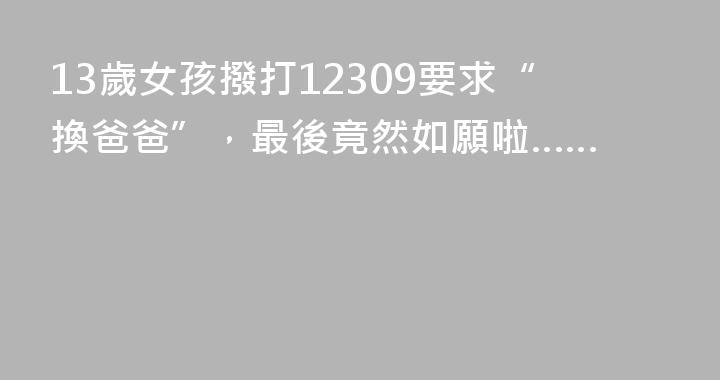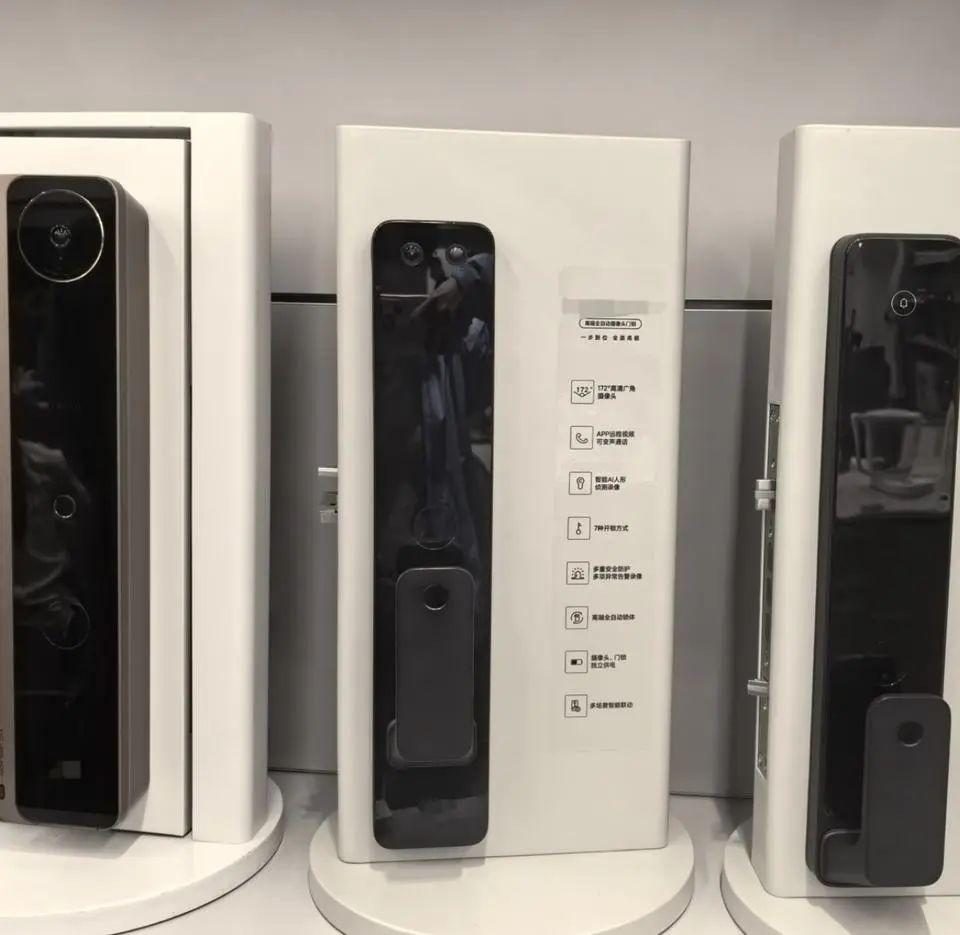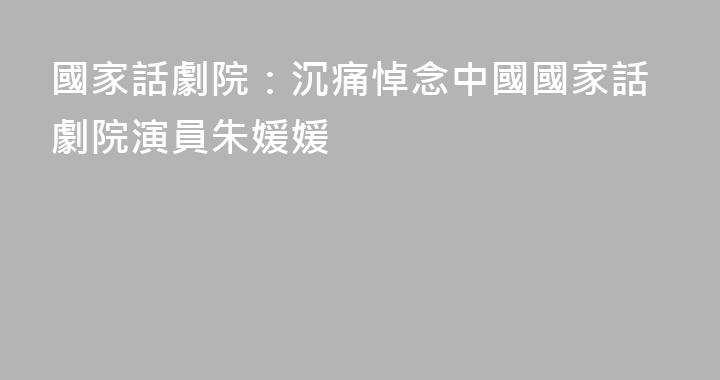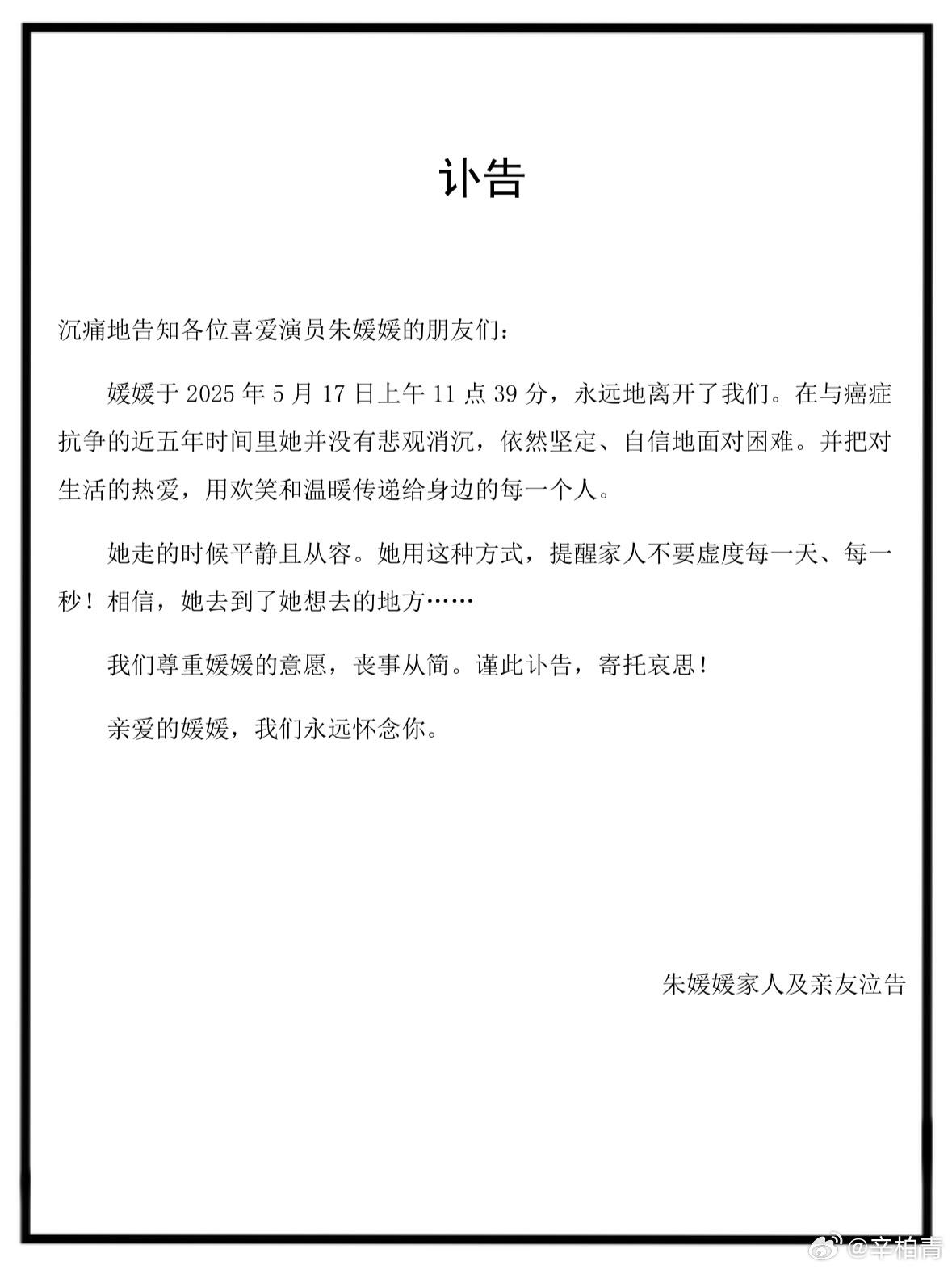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趙麗
“用中性筆組裝AWM-狙擊步槍,90%超高仿真度,可發射,在學校就能做。”《法治日報》記者近日在某社交平臺展示的視頻裏看到,3支普通的中性筆被拆解成筆桿、彈簧、筆芯、筆帽等零部件,在博主的重新組裝下,不多時,一把迷你“筆槍”便完成了。
記者在某短視頻平臺以“用中性筆做一把槍”爲關鍵詞進行搜索,搜索結果裏熱度最高的視頻點贊量高達40多萬,評論過萬條。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自稱教程的視頻在標題、簡介中特意標明“在學校就能做”,還有的視頻聲稱這是“好玩不傷人”的文具改造。
然而,“筆槍”若使用不當,則存在一定的危險性。根據公開信息,已經發生過男孩自制筆芯彈射穿自己眼角膜的案例,還發生過男孩手掌被同學“筆槍”彈射插入筆尖的事故。
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取材容易製作方便
未成年人跟風效仿
“怪不得我看見我兒子沒事就拆筆,好好的筆讓他拆得到處都是”;
“孩子買筆,都是一盒一盒地買,家裏到處是筆芯和管身,都是分離的”;
“把孩子們教會,去學校都不用上課了,天天‘開槍戰’”……
記者注意到,在此類視頻的評論區,不少網友表示自己的孩子存在模仿視頻的行爲,並對孩子們跟風製作“筆槍”表達了擔憂。
根據用中性筆組裝“筆槍”的視頻教程,原材料的獲取輕而易舉,全程只需用3支中性筆,再無其他零部件。據瞭解,這類中性筆是中小學生常用的書寫工具,中小學校附近的小賣鋪、文具店均可買到,平均售價2元一支,在電商平臺購買則更便宜。
記者發現,用中性筆改裝“筆槍”的教程視頻此前早已出現,只是視頻裏的“筆槍”外形上不如近期流行的精緻,但核心邏輯都是以文具爲材料製作可發射型“筆槍”。在社交平臺上甚至出現了××軍工的視頻標籤,裏面是用中性筆、圓規改裝“筆槍”、十字弩等各式教程。
有網友認爲,取材容易、製作方便,是這種“DIY武器”在未成年人中流行的重要原因,甚至有評論戲稱“在家成功率1%,在學校成功率100%”。
記者在採訪中也驗證了這種說法。
在浙江紹興上初一的學生李琪(化名)說:“我們班的男生天天玩這個,班主任都快被氣炸了。”她所在的班裏,比較調皮的幾個男生經常下課後拿着“筆槍”互相射擊玩耍,她之前還疑惑他們怎麼突然玩這個,放假時在網上偶然刷到視頻才明白他們從哪兒學的。
北京某小學四年級學生郭同學告訴記者,她前座的男生時常彈射這些自制“筆槍”,“我特別警告過他,不許拿這種‘筆槍’對着我,否則我就告訴老師。”
在浙江舟山某小學擔任六年級數學老師兼班主任的王洋(化名)告訴記者,目前,她帶的班級裏就有男生“迷上”了用中性筆組裝“筆槍”。
她非常擔憂:“因爲彈簧的力量不小,所以筆芯會被射出很遠,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作爲老師,肯定是會引導他們不要在教室裏玩這種玩具,但他們只顧好玩,不會考慮安全問題。”
上海某小學李老師對此深有同感,自己班上有兩三個比較調皮的男生學習網上的視頻製作“筆槍”,看着就挺危險,這種“筆槍”不應該是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玩的。
射程可達兩米左右
可輕易擊倒塑料瓶
中性筆組裝“筆槍”的殺傷力究竟如何?
在某教程視頻中,博主展示“筆槍”成品,通常會將筆芯作爲“子彈”,十釐米左右的亞克力擺件當靶子,發射之後,隔着幾十釐米的距離,亞克力擺件被輕易擊倒。在某短視頻平臺的一條高贊視頻裏,博主將十罐飲料壘成小型金字塔狀,用“筆槍”發射的“子彈”可以讓最底下的飲料罐移位,小型金字塔隨即倒塌。
記者購買3支中性筆按照視頻教程將其組裝成一支“筆槍”,經過測試,射程在2米左右,發射的筆芯可以輕易擊倒一個空礦泉水瓶。
來自安徽淮南某學校的教師徐芳說,去年,在學校一間教室內,一名男生用自制的“筆槍”射出一根串糖葫蘆用的竹籤,徑直穿透了同學的作業本。事發後,她收繳了這個“神器”。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筆槍”肯定不能算槍支彈藥或非法改裝,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孩子用它來發射一些比較尖銳的物品,還是很危險的。
不少受訪家長認爲,此類用中性筆改裝“筆槍”的視頻不宜在社交平臺上傳播,平臺應加大監管力度。
“這種類型視頻引導很多孩子製作有傷害性的玩具,危險係數非常高。我們並不是要扼殺孩子的創造力,只是安全要始終擺在第一位。”來自廣東中山的尹先生說,他的小兒子在網上看到這類視頻後,不吸取教訓,也養成了拆裝文具的不良習慣。
還有受訪家長向記者表示:“有些視頻標題強調在學校就能做,沒考慮這東西有安全隱患?這種視頻怎麼通過審覈的?爲什麼沒有及時下架?”
中小學生熱衷改裝
看着好玩實則危險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注意到,熱衷於用文具改裝“筆槍”的多數爲中小學生,家長與老師對這種危險的告誡其實從未鬆懈,但卻難以遏制其在校園內的風行。
江西南昌的張女士是一名五年級小學生的母親。近日,她在整理孩子文具時,無意中發現很多支中性筆已被拆解散架,起初她並未太在意,後來才知道原來中性筆可以被改裝成彈射“筆槍”。經過詢問,她才知道孩子是從相關視頻教程裏學來的,並且這種“筆槍”在男孩子間十分流行。
“我問孩子這個東西射到身上會不會很痛,尤其是夏天,皮膚裸露在外,他說班上有孩子在近距離彈射時,臉部皮膚都被戳破了。我覺得這實在太危險了,萬一傷到眼睛就完了。”張女士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後,嚴厲禁止孩子再用中性筆組裝“筆槍”,同時立即向任課老師反映。老師隨後特意在家長羣發文提醒,在班級組織學生觀看科普這類“筆槍”危害的視頻,“但還是有孩子偷偷弄,因爲取材太容易了。”
實際上,由“筆槍”引起的意外事故已經發生。
“你的視頻趕緊下架吧,存在誘導孩子之嫌,我的孩子就是在學校被其他小孩用這個改裝工具傷了眼睛,正在索賠中”——尹先生這樣的發言,在某“筆槍”教程視頻下的上千條評論中,尤爲扎眼。
尹先生的大兒子在午休結束後至下午課程開始前的這段時間與同學玩角色扮演遊戲,嬉戲打鬧之間突然遭到一名同學用“筆槍”對着眼睛彈射。
“孩子左眼立刻出現流血癥狀。送往醫院之後,醫生診斷結果顯示,眼角膜破裂,需要緊急實施眼角膜縫合手術。”尹先生介紹說,住院期間,他的大兒子的視力一度降至0.2,被評定爲二級傷殘。
“學校裏玩這種改裝‘筆槍’的小孩很多。”事故發生之後,尹先生到學校查看了監控視頻,“從監控裏看到,七八個男孩參與其中,我兒子躲都沒地方躲,一個小男孩拿着自制的‘筆槍’,對着我兒子眼睛發射。”提起這件事,尹先生至今仍然感到憤慨,雖然經過矯正之後,他兒子的視力已經恢復到0.8或0.9,但成年以後隨時都有青光眼伴發的可能性。
平臺應爲“手工教學”視頻設立紅線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宋昕怡
當前,大量用文具(中性筆)組裝“筆槍”的教程視頻出現在各大社交平臺上,還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那麼,用文具組裝“筆槍”能否被簡單地定義爲“文具改裝”?是否應該對組裝“筆槍”類視頻進行規制?圍繞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採訪了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
記者:從對未成年人的引導效應來說,這類視頻應該如何定性?
任海濤:引導未成年人將文具改造成“筆槍”的教程視頻,從對未成年人的引導效應方面來說,應當定性爲不良導向內容。這類視頻表面上以“創意手工”作爲包裝,實質上可能引導未成年人嘗試製作具有危險性的物品,存在明顯的社會風險和倫理隱患。
從發展心理學視角看,未成年人尚處於認知發展的特定階段。7歲至11歲兒童處於具體運算階段,他們已經能夠按照指令精確模仿動作,但缺乏對後果的全面預見能力;11歲以上青少年雖進入形式運算階段,開始具備抽象思維能力,但其風險評估和自我控制能力仍不成熟。這種認知特點使他們在接觸此類視頻後極易產生即時模仿衝動,但卻無法充分理解其中潛藏的風險,形成認知偏差。
更爲關鍵的是,此類視頻可能對未成年人的價值觀形成產生深遠影響。當文具被改造爲具有攻擊性的“筆槍”並被包裝爲“有趣”“創意”形式時,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錯誤認知,將具有攻擊性的行爲與“創造力”“個性表達”等正面概念關聯起來,弱化對攻擊行爲的道德戒備。
記者:在社交平臺上,“手工教學”視頻是否應與這種“危險器具改造”類視頻劃定明確邊界?
任海濤:的確如此。
從安全風險角度看,若改造後的文具具備明顯傷害性,例如能夠遠距離發射尖銳物體的圓規改造、具備爆炸性的文具改裝等,平臺應當設立紅線,限制此類視頻的傳播。這不僅是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考量,也是基於公共安全的普遍要求。
從社會倫理角度看,即使某些改造尚未達到明確違法程度,但若具有誘導攻擊性行爲的傾向,平臺同樣應該限制其傳播。例如,將中性筆改造成迷你弓箭的視頻,雖然傷害力有限,但這種導向本身就值得警惕。
從創意表達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角度看,社交平臺應當鼓勵創意表達,但這種鼓勵不應擴張至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領域。“手工教學”視頻需要遵循基本的安全倫理底線,不能以“創意自由”爲名規避社會責任。對此,平臺應建立相應審查制度,避免未成年人接觸到不適合其認知和判斷能力的內容。
記者:視頻作者或者相關博主作爲傳播主體應當負什麼樣的責任?
任海濤:創作者作爲文具改造成“筆槍”視頻的傳播主體,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和道德責任。創作者享有創作自由,但這種自由的邊界是,創作內容不能對公衆特別是未成年人產生不良影響。
一方面,創作者應具備內容影響評估意識,在內容生產前,創作者需要充分考量視頻可能的受衆羣體和潛在影響,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羣體,創作者更應認識到,自己的創作不僅是單純的技術展示,還包含着價值導向和行爲引導;另一方面,創作者需要承擔社會責任與法律義務,互聯網時代的內容創作者不再是簡單的個人表達者,而是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公共角色,內容創作者應遵守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
具體來說,創作者應該評估文具改造過程中是否涉及危險操作(如削尖、加熱金屬)、成品是否具有傷害性、模仿者(特別是未成年人)是否可能因操作不當而傷及自身或他人等。對於可能存在危險的操作環節,創作者應在視頻中添加明顯的文字或語音警示(如“未成年人禁止嘗試”“需在成人指導下進行”等),並說明不當操作可能導致的後果。
記者: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始終是基本原則,所以,平臺是否應該採用算法、人工審覈等方式對此類視頻進行限制?
任海濤:平臺在審覈“手工教學”類視頻時,應建立科學合理的界定標準,區分“創意DIY”與“危險器具”。
技術界定方法。平臺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視頻內容進行多維度分析,識別其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元素,如特定結構(彈射機構、切割裝置)、使用方式(瞄準動作、射擊行爲)等。同時,也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分析視頻標題、描述和評論區內容,識別潛在的危險。
制定綜合評估指標。平臺可從創作目的、使用材料、製作工藝、最終用途四個維度進行綜合判斷。創作目的是純粹娛樂還是可能導向攻擊性行爲;使用材料是否包含鋒利、堅硬或具有彈性勢能的危險部件;製作工藝是否涉及高風險操作;最終成品是否符合實際功能與是否存在可能的誤用風險。舉例而言,將圓規改造成具有瞄準功能的彈射裝置,其創作目的明顯指向攻擊性用途;使用了具有較強彈性的橡皮筋和尖銳的金屬部件;製作過程可能涉及改造金屬尖端;最終成品具備遠距離傷人潛能。這類視頻顯然超出了“創意DIY”的範疇,應歸入“危險器具改造”類別。
建立專家介入機制。對於難以界定的邊緣案例,可引入安全專家、教育心理學家等第三方專業人士參與審覈決策。通過多方評估,確保平臺的界定標準既不過於寬鬆導致風險內容氾濫,也不過於嚴苛限制正常的創意表達。
記者:在尊重創作者創意的前提下,平臺如何引導未成年人觀看此類視頻?
任海濤:平臺在尊重創作者創意的同時,應針對未成年人制定特殊保護措施。可以實施智能識別與彈窗提示。通過用戶畫像技術識別未成年用戶,當其嘗試觀看包含潛在風險的文具改造視頻時,系統自動彈出風險提示窗口,提醒潛在危險並建議在成人陪伴下觀看。構建專屬內容池。平臺可爲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定製安全可靠的內容庫,確保他們接觸到的手工創意內容既有趣味性又不存在安全隱患。這種專屬內容池應由專業團隊負責篩選和更新,定期引入新穎且安全的創意內容,滿足未成年人的創造力發展需求。